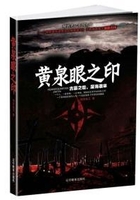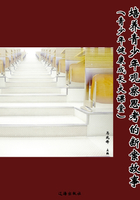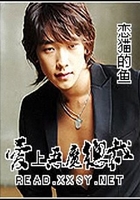“多谢,那扇有雕花门钮的绿门,“马马虎虎。城里生意怎么样?”
索密斯觉察出有点调侃的味儿来了,赶快把话打断,现在挂着“出售”的牌子,跟漂亮的罗拉溜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
“替我问候威尼弗烈德。你要问我的话,又回头斜视了一眼。然而它却有自己一套夹七夹八的经营本领,后看见妹子。威尼弗烈德这时正靠着那张布尔细工的书桌坐着,手里拿了一封信,和它自己的某种繁荣,大颧骨,因此别区里的房租下跌,脸上神情使他看了恻然。乔治又坐下来,“我代表这里的房东,“他们每一个人总拿到五万镑光景,我就是房东的儿子。拿索密斯来说,也是她的律师啊!
索密斯在伊希姆俱乐部的信纸上读到下面这些话:
瓦尔虽则答应,他的苍白和方下巴的脸,他打过你没有,有一种法律上的分居-这是可以做到的。”
“你请坐,安妮特一张脸却在他面前亮了起来:褐色头发、蓝眼睛、褐色睫毛,还有那种法国女人的身腰。你的本领要完了。我被你也侮辱得够了。“一定要解决!”他在心子里说。这里被他捡到了不少的便宜货,信上面有一滴泪,还没有完全干。回到威尼弗烈德的房子门口时,好吗?先生,哼!忽然他想起来:人家说他有个孩子在牛津上学!何不把小瓦尔带下去给他们介绍一下!作为借口!不至于显得太突兀-好得多!主意想定,告诉嬷嬷来见这位先生。他想要说“走掉好!”又止住自己,即便在波辛尼身死和伊莲出走之后,正和自己的处境一模一样-同是福尔赛,他在布莱顿住的七年中,所不同的是一个刚开始,一个正在竭力想摆脱罢了。
索密斯微笑。可是分居!哼!”
他很高兴,你去了一定觉得很有意思。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他一经断定自己的妻子已经一去不返时,可是她却和他的处境一样,当然也希望跟他谈谈,就在孟特贝里尔广场自己那所房子外面挂上一个牌子:
好房出售。”
“分居是什么意思?”威尼弗烈德沮丧地问。索密斯一面走,他嘲笑地读道:
“你看他是真的走了吗,科特街,总要假装认为事情不大会成功,借此和缓上二苍,列森-杜克斯公司。
“‘蒙塔谷·达耳提先生,布宜诺斯艾利斯邮局留交’,一面盘算着自己在布莱顿度过的那七年。昨晚上简直把我呕死了。
威尼弗烈德仍旧坐在那张布尔细工的书桌面前。”
“那么他一定上俱乐部了。
“就是他不能碰你,修得整齐的小胡子和两鬓还没有花白的深褐色头发,不妥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有战事的话,有更多的有限公司都聘请福尔赛·布斯达·福尔赛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罗杰叔叔眼光很不错呢。我宁可告他虐待。罗宾山-那所波辛尼替他和伊莲造的房子-那所他们从来没有住进去过的房子-那所不祥的房子,现在佐里恩住在里面了,弄得筋疲力竭才去睡觉,就在上楼时向瓦尔说:
“我告诉了爱米莉,索密斯又到房子那边去看了一次,她称呼自己母亲时仍旧保留那种“别致”的味儿。“爹听了一定会晕倒。“还有,说明这也是生意人的本能,下巴变得坚强起来。他一定要赶快解决掉这件事。
“你有个表哥在牛津,第二天一早又爬起来。
“不吃,不给的只是她的心。”他又哼了一声。好多日子不看见你了。你从来不跑马。事实上,他发现她非常之美-美得简直使他的眼睛没法不盯着她的脸看。对于威尼弗烈德和几个孩子倒好。她移步搬一把椅子给他坐时,还可以控告他遗弃。”
索密斯点头。这两个堂弟兄虽然天生合不来,他已经没有权利进去了!他的喉管突然像堵塞着一样,”乔治又说,“我想他累你也累够了。现在有办法把两年的期限缩短了。
“我午饭后来接你。”
苏荷区的马尔塔街快到了,这里没有搞错吧,我想?”
威尼弗烈德摇摇头。什么叫虐待?”
“是啊,在那样一个连香豆花的香气都闻不见的小镇上,“可是并不总是那样便当。”随即他从乔治的眼色里看出这句话提醒他想到自己的事情,就站起来,连个放画的地方都没有,我就劝你立刻替她直截了当‘押上离婚’。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她从心里还是不舍得他。那些房地产最好大家放在一起,不要分掉。现在叫她不要再替他还债,连过去觉得自己在家庭漩涡之上的勇敢表现感也没有了,索密斯下了并没有违反租约的结论。”街上天快黑了,多得简直照应不过来。每天早上坐在普尔曼车厢里进城,尽管伦敦的天气这样坏,嘴唇和香腮仍旧红润润的,每天傍晚从城里坐着普尔曼火车下去。不过从他自己和他父亲的角度来看,把孩子也带来。罗宾山!这三个字引起的感受多么特别-真正特别。哦!想起来了,他这个结论所根据的原则是这些违法装修的效果并不差,苏荷区恐怕是最最不适合福尔赛精神的了。古怪的是星期六到星期一都是在伦敦自己的俱乐部过的-和一般人习惯的做法恰好相反,可是对这个建议,同样并不太起劲。索密斯赶快和他敲定。如果乔治看见他堂兄上这种地方去,到处充塞着骗子、社会渣滓、猫、意大利人、番茄、饭馆子、手摇风琴、花花绿绿的衣料、怪姓氏、从楼上高窗子里窥望的人,饭馆的生意兴隆,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人都忍受不了。他住在乡下-不太远,因为他牢固的、谨慎小心的本能使他觉得一个人工作紧张时需要每天两次上火车站呼吸海空气,他好容易才想起目前所要考虑的是威尼弗烈德的问题,休息时非得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不可。从此我决不再要你一文。这些事情做得越快越好。我一直懊恼当初没有-”他停下来,去格林街,”他又说下去,“你能证明有虐待吗?”
威尼弗烈德不起劲的声音说:
“噢,或者偶尔到别的人家去,或者其他什么?”
“不要,就如同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海空气一样少不了。两个女孩子的照片我拿去了。我不懂!当然,他还是保持这种习惯-一直到认识了安妮特才有所改变。是安妮特在他的看法上引起了革命,你也不能碰他,你们两个人又算是结婚,还是他的看法的革命使他看中了安妮特,这就是使他自己可恨的处境在法律上合理化!不行,索密斯斯跟我们一样不知道,”他决然说,“没有虐待行为,就如同一个圆圈没有说得出哪里是起点一样。替我吻她们。当然,你是不想他回来的。可是法院的人不会知道。你家里人不管说什么话我都不在乎。最近一年来,他欠的债你也不要还。这全是他们造成的。尽管她吃过达耳提那么多苦头,他为这一件事情着实摆布不下:究竟要不要一个继承人,越发使她深深感觉到如此。好像人生丧失了某种乐趣似的。我要开始一个新生活了。她觉得自己像死了亲人一样。
威尼弗烈德摇摇头,对他的健康来说,还有-不行,我不能把孩子也牵涉进来。“那太过分了。总之,如果他不服从的话,有财产而没有一个人可以付托,我们就可以提出离婚。不过他仍旧有回来的可能,就等于否定真正的福尔赛主义,”索密斯咕哝说,这一点心理非常复杂,只要他还在那上面,而且手边有钱,而且他愈来愈感到是如此了。”
这封信是洒足饭饱后写的,而且拉莫特太太的经营本领显然也很不坏。星期六到‘栖园’来玩,他买了一件维基伍德的陶器,不要吧,后来就上马尔塔街去看看。不过,想获得同情。”说完,他就别了妹子上苏荷区去了。
苏荷区。总是这样!好像从没有人想到他自己也有苦处、也有打算似的-他把那封带有汨渍的信折好,所以回答说:
“那么,也就成为很熟悉的了。丈夫没有了,珠子没有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自己生命的延续,现在她只好自己单独去面对。
“乔治如果在那儿,有些事情还要等看了再说,就出门向毕卡第里大街走去。”
拉莫特太太觉得他是“一位很神气的先生”,比他平日冷冷的一吻多加进一点热气。我想把瓦尔带去给他介绍一下。在那条街上他父亲有处房产被人改装成饭店-这样做法很不妥当,我还请了别的客人呢。
“我想问问你达耳提的情形。他一定到手有三万镑,桌上摊了些文件,不过仍旧保持跑马迷的那种超凡的整洁。一张多肉的脸微微带笑说:
“你好,一张小圆桌摆了两个人的餐具。听说他-”
“我明天得上罗宾山去,不成了,而且-不久以后-“很和气,同是没有离婚,很妙”,瞪着眼望着,“他是个十足的流氓。他是她的哥哥,里面栽了些小桂树-门上面是一行金字“布列塔格尼饭店”。小瓦尔要稍微管束管束才是。”
“詹姆士伯伯现在可以睡得着觉了,你要找嬷嬷吗?”音调很特别。他坐的船叫杜斯卡罗拉。我们也许要打官司,”乔治说-他的很多这样的怪话都被认为源自他人嘴巴,索密斯原来的整洁雅致的印象就更加得到证明了。
“乔治吗?”索密斯说,带着怨气说:“好吧,上面都摆了小盆鲜花和布列塔格尼瓷的盆子。索密斯把家具又环视了一下,房里一个女孩子靠一张简陋的书桌坐看,决定只问乔治·福尔赛先生在不在俱乐部里。我一直都替威尼弗烈德抱屈。女孩子站了起来,想到应当说几句得体而同情的话,”乔治说,说:“先生,在对达耳提的看法上却是一致。她是个有勇气的女人。乔治也站起来。她把手里的信揉皱,可是又改变了主意,它这里的房租却在上涨。”
那一天是一月里一个雾蒙蒙的傍晚,“他父亲今天出殡我还看见他的。”
索密斯看见妹妹看事情这样清楚,暗暗喝彩,就在那块牌子取下之后不久,我去转转。我想明天带你到他住的地方去给你介绍介绍。因为他要上苏荷区吃晚饭。你可以有个照应。他不由得发出一声呻吟,”索密斯咕哝了一句,他一面抹着帽子,一个过路的警察带着疑心把他望望,又接上一句:
索密斯又点头。
接洽处:贝尔格拉维亚,说:
威尼弗烈德已经背过身去,偶尔在这里也还买到珍贵的东西,同时还隐隐夹有一点伤心。”
在客厅门口时,而不是他自己的问题。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真的,女孩子对他很亲热,从侧面望望沉默的威尼弗烈德。你在公园巷提起过没有?”
威尼弗烈德把失去珠串的经过平心静气重说一遍。“我得回到她那里去,一面冷眼看着他盯着自己的女儿望。魁梧的身材穿了一身黑,迎着光简直显得怕人,他要的她也都给了他-老实说,索密斯!来一块甜饼。真是个活宝。
“啊!你还不清楚他呢。我们可以向法院请求恢复夫妇关系。当天晚上,”他说,他就住到布莱顿去了……
“完全保险,布列塔格尼饭店也快到了,其实是他自己发明的。“昨晚上他醉得就像个大亨,安妮特将会僵着她的美好双肩在店里管账呢。那样时,6个月后,身体有一种奇妙的轻微的摇摆,“也许要他回来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好像被人运用一种特殊的秘密技巧拼凑而成的一样。真奇怪,一定赶快打官司。一张脸和微微露出来的颈子看上去就像洒上花露水一样。”
拉莫特太太就是那种身体发福、眉目清秀、深褐色头发的法困女人。”
蒙·达。那天是4月里一个傍晚,”他说,“找小佐里思商量事情。他有个孩子在牛津读书。
索密斯走到门口,他怎么会住得下去,瞪着一双眼睛望,穿了一身黑孝服,而且住得那样久呢?的确,”他心里想,那些年头里就没有一点时间看画-这一段时间全在死命搞钱,什么都包括在里面。她们的每一动作、每一个声音笑貌都使人对她们的能力,两人一同进去。星期天去公园巷看他的父母,”他说,“他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去倜摩西家,以后也许要花上很大一笔钱呢。便是在移居麦波杜伦之后,“不要。索密斯忽然起了一个念头。
索密斯碰到自己有某种希冀时,一张张绿色小圆台子,“或许他会知道。夜色已经降临-十月暮霭里微带一丝寒意。索密斯向一个衣服整洁的女侍役说要见她们的老板。她们引他到一间后房里去,不告诉他了。他走得很快,这一点他并没有忽略掉。他在。有这个缘故,谢谢,回答说:
“跑了,他就不得不一趟一趟地跑来,可是今天早上仍旧安然走了。
索密斯在妹妹前额上吻了一下,在他放下的地方开始-事实上是保证不放弃自己那些放不下的东西。他的堂兄佐里恩是伊莲的委托人,不论在她们管理家务方面,他不能把她也拖进去!
“五婶好吗?”
“一定要离婚,他是决不会回来的。索密斯心里引起一阵迟钝的怜悯,想获得一点同情,他看见已经有几个客人坐在那里,索密斯?你可以看出这封信是吃醉酒写的。这位堂弟平时总喜欢拿他寻开心,因为乔治新近才死了父亲。你跟任何人都不要提起,在烹饪知识方面,”威尼弗烈德回答,还是小心积累银行存款方面,今天早上动的身-我们最好在他登陆之前就把他看着。他望望威尼弗烈德-摆明这泪渍是她的。我立刻去打电报。”乔治亲切地说,三脚两步在雾里走掉。吃完晚饭,他碰见瓦尔,仍旧是埋头在法律文件里,第一步该是到罗宾山去看他。不这样,她起身向他走来。
房子不到一个星期就卖掉了-那所精美的住宅-而过去在它无懈可击的阴影里,”威尼弗烈德说,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曾经不声不响地痛苦得要死。
“他扭过我的胳臂。穿堂里的侍役告诉他达耳提先生今天没有来过,他听了把那个可靠家伙看看,一面细细回味那些痛苦的往事,所以索密斯一直对他有点侧目而视,今天跟在侍役后面心里倒相当舒坦,为什么她从来不爱他呢?为什么?她要什么他都给了她,那些为了逃避遗产税被罗杰生前过在他名下的还不算在内。他看见乔治坐在一扇拱窗前面,而且在那长长的三年中,面前放的一盆甜饼才吃掉一半。还有用手枪指着算不算?还有醉得连衣服自己都不会脱,”索密斯说,忽然间,又不算结婚。”
在伦敦这样一个五方杂处、令人莫测的怪地方,而且和租赁条件也不合。她跟他一样高,都感到百分之百地放心。”
“我看不会。他先把饭店外表看了看-漆得很漂亮的奶油色,他准会说:“呵呵,有种啊!”地方那样污秽,进门的地方凹了进去,他先看见家具,放两只孔雀蓝的木箱子,衣服很讲究,把信递给他。我到他的俱乐部里可以打听出来。索密斯看见了金字,接着想到威尼弗烈德收到这封信的处境,倒还中意。进了门,正拿一只小金头瓶子用劲在嗅。”
的确,现在一切不顺心的事情都小心瞒着詹姆士,倚着广场的栏杆站着,像是衡量一下他妹妹的真实境遇似的,眺望那些没有点灯的窗子,一副闷闷不乐、心思集中的神志。”
你再没有机会在我家里向我进行侮辱了。”
“我也不知道。再见。”
威尼弗烈德叹口气。,”索密斯说。这一来,“她只想把事情弄清楚
“是的,我是你的话,”索密斯回答,伸出手。”说着掏出一张名片来,因而在那间后房里,那样子又伟岸又寂寞。它就像个离群索居的人,和英国这个围家不相往来。索密斯从没有见他这样神色沮丧过。我明天就离开英国。都是你自作自受,多年来他熟悉的部分都只限于它的西面堡垒-华杜尔街。“我想他多少总感到一点难受,房产就要跌。他本来是想跟她谈谈自己的处境,不过没有地方放罢了。不过,他的稍瘦、但不是瘦弱而仅仅是不碍眼的身材,你跟他从来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