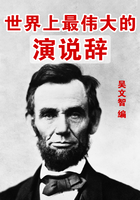“您没有权利这样说……我……不单纯……这……”蒲尔道夫司基激动地、吐字不清地说道。
“您没有任何权利做这样的假设。”列别杰夫的外甥又以教训人的口吻帮腔道。
“这太气人了,”依鲍里特尖声说道,“这种假设是气人的、错误的、与事无关的。”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公爵急忙赔罪,“请各位原谅。这是因为我想,我们不如把心里想说的话完全摊开来说好,但是随你们便,悉听尊便。我当时对切巴罗夫说,因为我不在彼得堡,但是我可以立刻委托一位朋友全权处理这件事,后来我也把这个情况通知了您,蒲尔道夫司基先生。我要直截了当地对你们说,各位,我觉得这事其中有诈,因为切巴罗夫在捣鬼……喔,各位,请勿见怪!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千万不要见怪!”公爵看到蒲尔道夫司基脸有愠色,在他的朋友中也出现了骚动和抗议,便害怕地叫起来,“我说这事其中有诈,这跟你们本人无关,也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时候你们中的任何一位我都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连你们的尊姓大名我都不知道。我说这话是冲切巴罗夫一个人说的,只是泛泛而论,因为……你们倘若知道自从我接受遗产以来受了多大的骗,你们也许就不会怪我了!”
“公爵,您太天真了。”列别杰夫的外甥嘲弄地说。
“更何况您是公爵,又是百万富翁!尽管您的心肠也许的确很善良、很单纯,但是您终究逃脱不了一条普遍的规律。”依鲍里特庄严宣告。
“可能是这样,很可能是这样,各位,”公爵急忙说道,“虽然我不懂你们说的是什么普遍规律,不过还是让我说下去吧,然而,请各位不要见怪。我起誓,我毫无侮辱各位的意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各位:我竟不能说句真心话,一说真心话,你们就要生气!但是,第一,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世上竟存在‘帕夫利谢夫的公子’,而且还处在这样可怕的境况之中,就像切巴罗夫向我说明的那样,帕夫利谢夫是我的恩人和我父亲的朋友。(唉,开历尔先生,您在您的大作里干吗对家父写了这么多不真实的情况呢?他既没有挥霍连队的公款,也没有苛责下属……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您怎么抬得起手来写这种无中生有的事呢?)至于您写的关于帕夫利谢夫的话,更叫人完全无法容忍了:您居然称这位最高尚的人是贪淫好色的花花太岁,而且说得那么大胆,那么肯定,好像言之凿凿,千真万确似的,其实这是一位世上少有的最洁身自好的人!他甚至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与科学界的许多可敬的人有通信关系,而且花很多钱资助科学研究。至于说他心肠好,做过许多好事,噢,当然,您写得很对,我当时几乎是白痴,什么也不懂(虽然俄语我还是会说的,也听得懂),但是我还是能够对我现在想得起来的一切,做出自己的评价……”
“对不起,”依鲍里特尖声叫道,“这是不是太多愁善感了?我们不是小孩。您说要开门见山,言归正传,九点多了,请记住这点。”
“好吧,好吧,各位,”公爵立刻表示同意,“在最初的不信任之后,我终于认为我也可能弄错,也许帕夫利谢夫的确有个儿子也说不定。但是使我感到十分吃惊的是,这儿子居然会这么轻易地,我是想说,居然会这么公开地把自己的出生秘密和盘托出,主要是,竟至于不惜玷污自己生母的名声。因为切巴罗夫还在当时就曾用公开这一秘密吓唬过我……”
“真蠢!”列别杰夫的外甥叫道。
“您没有权利……没有权利!”蒲尔道夫司基叫起来。
“儿子不能对老子的放荡行为负责,而母亲是无罪的。”依鲍里特热烈地尖叫道。
“那就似乎更应该体谅她呀……”公爵怯怯地说。
“公爵,您不只是天真,恐怕是天真得过了头。”列别杰夫的外甥冷笑道。
“您有什么权利!”依鲍里特用听来极不自然的声音尖叫道。
“我没有任何权利,我没有任何权利!”公爵急忙打断道,“我承认,你们在这点上是对的,不过,这是情不自禁,而且我当时就对自己说,我的个人好恶决不应该影响事情的发展,因为即使出于感念帕夫利谢夫对我的恩情,我已经认为自己理应满足蒲尔道夫司基的要求,那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即不管我尊敬布尔多夫斯先生与否,我都应该给予满足。我所以开头说这样的话,各位,那是因为我看到做儿子的居然这样公开地揭露自己母亲的秘密,总觉得有悖常理……一句话,主要是因为我深信切巴罗夫一定是骗子,一定是他怂恿布尔多尔斯基先生设置骗局来进行这样的讹诈。”
“简直岂有此理!”他的客人发出一片喧哗,有几个人甚至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各位!所以我才认定,这位不幸的蒲尔道夫司基先生一定是个单纯的、无依无靠的人,容易上骗子们的当,因此我更应该帮助他,就像帮助‘帕夫利谢夫的公子’一样,第一,反其道而行之,使切巴罗夫的阴谋不能得逞,第二,用我的忠实和友情开导他,第三,我决定给他一万卢布,也就是按我的算法,帕夫利谢夫在我身上可能花掉的钱……”
“怎么,才一万!”依鲍里特叫起来。
“好了,公爵,您的算术也太不高明了,或者说,您的算术也太高明了,虽然装出一副傻头傻脑的模样!”列别杰夫的外甥叫起来。
“一万卢布我不同意。”蒲尔道夫司基说。
“安季普!您就同意了吧!”那位拳师趴在依鲍里特的椅背上,探过头去,用快速而又清晰的低语提醒他道,“您就同意了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我说梅什金先生,”依鲍里特尖叫道,“您要明白,我们不是傻瓜,更不是浑蛋,您的所有的客人们和这些女士们,大概就是这么想我们的,瞧,这些女士们正在十分愤怒地冲我们冷笑,特别是这位上流社会的先生(他指了指叶夫根尼·柏夫洛维奇),对于这位先生,当然,我还无缘相识,但是也多少听说了点……”
“对不起,对不起,各位,你们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公爵激动地对他们说道,“第一,开历尔先生,您在您的大作里对我的财产估算得非常不准确,我根本没有得到几百万,也许只有您假定我拥有的财产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第二,我在瑞士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在我身上花掉数以万计的卢布:施涅台尔每年才收到六百卢布,而且总共也只是最初的三年,帕夫利谢夫从来没有到巴黎请过漂亮的家庭女教师,这又是诽谤。我看,花在我身上的钱还远远不到一万卢布,但是我却拿出了一万卢布,你们自己也看到,我还要还债,因此我无论如何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蒲尔道夫司基先生了,虽然我非常爱他,也爱莫能助。所以爱莫能助,还因为出于一种礼貌感,我是还他的债,而不是给他的施舍。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但是我希望今后能用我的友谊来补偿这一切,用积极关心不幸的蒲尔道夫司基先生的命运这一办法来补偿。他肯定上了人家的当,因为倘若不是人家骗他上当,他自己决不会出此下策,比如今天在开历尔先生的这篇大作里公然诋毁自己的母亲……各位,你们到底怎么啦,怎么又冒起火来了呢!这样下去,我们永远无法互相了解的。你们看,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现在亲眼看到并且深信我的猜测是对的。”公爵着急地想说服他们,想平息他们心头的焦躁,但是他没有发现,他反而使他们的情绪更加激昂了。
“怎么?您深信什么?”大家几乎暴怒地对他群起而攻之。
“非常抱歉,第一,我已经亲眼看清了蒲尔道夫司基先生的为人,我现在已经亲眼看到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一个涉世未深的人,但是大家都在欺骗他!他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因此我才应该体谅他;第二,我曾经把这事委托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去办,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了,因为我在来彼得堡的路上,后来又在彼得堡病了三天,可是现在,也就是一小时前,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突然通知我,切巴罗夫意欲何为他已经全部弄清楚了,并且有真凭实据,至于切巴罗夫的为人,恰如我所推想的那样。各位,许多人都认为我是白痴,这,我是知道的,由于我名声在外,说我会把钱随随便便地送给别人,因此切巴罗夫以为我很容易上当,而他指望加以利用的也正是我对帕夫利谢夫的感情。但是现在主要是,请听我说完嘛,各位,请听我说完嘛,主要是,现在忽然弄清楚了,原来蒲尔道夫司基先生根本就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公子!这事是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刚才告诉我的,而且他向我保证,他已经弄到了确凿可靠的证据。好了,各位对此有何高见,要知道,在发生这一场轩然大波之后,简直使人没法相信!听着:证据确凿!不过,我还是不信,奉告各位,我自己也不信,我还在怀疑,因为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还没有来得及把一切详情细节原原本本告诉我,但是,至于说切巴罗夫是个骗子,对此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了!他把你们所有的人都骗了,既骗了不幸的蒲尔道夫司基先生,又骗了你们这些为朋友仗义执言的所有先生,(因为他显然需要支持,这点我是明白的!)他非但骗了你们所有的人,而且把你们所有的人都裹挟进了这件诈骗行为,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坑蒙拐骗。”
“怎么是坑蒙拐骗!……怎么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公子?……这怎么可能呢!……”发出一片感叹和大呼小叫。蒲尔道夫司基那群人处在一种难以形容的骚乱中。
“这自然是坑蒙拐骗!如果布尔多斯基先生其实并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公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蒲尔道夫司基提出的要求,就是一种彰明较著的诈骗行为,(当然,这是假定说他知道事实真相的话!)但现在的问题是人家骗了他,所以我才坚持必须替他说句公道话,因此我才说他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太单纯了,不能没有人替他出来说话。否则,就这件事本身来说,他也就成了骗子了。要知道,我自己早就深信不疑,他对个中内情的确一无所知!到瑞士去以前,我自己的情况也与他相仿,说起话来也咿咿唔唔,前言不对后语,想说又说不出来……这我明白。请恕我直言,因为我自己的情况也庶几近之,所以我非常同情他!最后,尽管现在已经没有了‘帕夫利谢夫的公子’,这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我仍旧不改初衷,情愿奉还一万卢布,作为对帕夫利谢夫的纪念。要知道,我在遇到蒲尔道夫司基先生这件事以前,就曾想拿出一万卢布来资助办学,作为对帕夫利谢夫的纪念,但是现在资助办学或者给蒲尔道夫司基先生,反正都一样,因为蒲尔道夫司基先生即使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公子’,也跟他的公子差不多:因为他本人上了人家的大当,他自己曾经当真以为自己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现在,请各位先听听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的情况说明,我们就此结束此事,请各位别生气,也别激动,请各位先坐下!加夫里拉·阿尔利达翁诺维奇马上就会给我们说明一切,我承认,我也非常想知道全部内情。蒲尔道夫司基先生,他说他甚至亲自到普斯科夫去找过你妈,她根本没有像你们在文章中写的那样,卧病在床,奄奄一息……请坐,各位,请坐!”
公爵先坐了下来,又让座位上一个个跳起来的蒲尔道夫司基先生的那一群人也一一就座。在最后这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内,他说话很激动,声音很大,说得跟连珠炮似的,很不耐烦,有点冲动,嗓门也比所有的人都高,喊得也比所有的人都响,以致后来他对现在脱口而出的有些话和假设深感后悔。如果不是别人刺痛了他,使他忍无可忍,他是不会允许自己这么露骨,这么匆忙地公然说出自己的某些猜测和过于开诚布公的话的。但是他刚一坐下,一阵炽烈的后悔就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除了他公然假定蒲尔道夫司基也患有他自己在瑞士治疗的那种病,因而“得罪”了蒲尔道夫司基以外,此外,他又做出了提供一万卢布的决定,但不是资助办学的许诺,照他看来,这样做既失礼,又不慎重,好像是给别人施舍似的,而且还当着众人的面公然说出来。“应当等一等,等到明天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再提出来嘛,”公爵立刻想道,“现在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了!我真是白痴,地地道道的白痴!”他暗自认定,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和非常痛心。
在此以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一直置身事外,一言不发,这时便应公爵之请,走上前来,站在公爵身旁,镇静而又口齿清晰地开始做公爵委托他办的那件事的调查报告。本来大家在议论纷纷,霎时间便鸦雀无声。大家都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洗耳恭听,特别是蒲尔道夫司基的那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