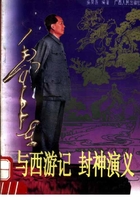进屋,古芳冷着脸,赌气地将挎包向床上一扔:
“十二点了,还不吃饭?我都饿死了!”
“快了,快了!”古清泰应声跨出天井,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
古芳眼光落在桌上。她走过去,抓起一块卤排骨,啃起来。
“等一下,你姐回来,一起吃。”
古芳示威般又抓起几片卤肚条,津津有味地嚼着,看也不看父亲。
古清泰无奈地苦笑一下,瞟着门外:
“就你一个人,小高呢?”
古芳脸上,瞬间像结了一层寒霜。她拿起桌上的樱桃酒,倒了半杯,坐下自顾自喝着。
“问你话,勋建呢?”打量着女儿神态,古清泰催问。
“死了!”古芳不耐烦地说,又讥刺地挑起眼睛,“小高?勋建?喊得怪亲热的,不就给你买过几条烟几瓶酒?倒像我是外人,他是你亲生儿子?”
古清泰被顶撞得一怔。“鬼女子,娇惯得简直不像样了!”他嘀咕着,不知责怪自己还是责怪女儿。
一会儿,古芬同丈夫周恒回来。
看见姐姐和姐夫的亲热模样,古芳眼圈一红,一滴泪珠挤出眼眶,掉进酒杯。
“芳芳,你?……”周恒诧异地问。古芬轻轻的一拉他,示意他不要说话。她走进天井,帮着父亲忙乎。
“芳芳到底咋了?”古清泰挂着古芳。
“同高勋建闹离婚。昨晚,周恒上夜班,她来我家谈了很久,我咋也劝不住。看来,她下决心了。”
“离婚?”古清泰惊愕地张大嘴巴,直勾勾地看着古芬。
“爸,你别管这事!”古芬体贴地安慰父亲,“他们的事,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高勋建也不是啥好东西,赚了点钱,就在外面找女人。只在家里,古芳就逮着三次。”
古清泰愣着,好一阵,懊丧地把脚一顿:“当初,我就不答应。她犟着性子,非要嫁给他。一年都不到,就闹离婚?……传出去,人家咋议论?又说你妈死得早,我没把你们教好。”
“爸——”古芬不满地拖长声音,“不许你想那么多!”
这顿饭,都吃得没盐没味,像有一团驱不散的阴云,死死地压在大家心上。古芳垂着眼,不说话,也不看谁,闷闷地只是喝酒。古清泰没话找话地同周恒聊着,最后也像找不到说的,不放心地轮番瞥着两个女儿。古芬竭力调节气氛,一会儿称赞父亲红烧肉做得好,一会儿非要周恒陪父亲喝酒,一会儿又忙着给古芳泡茶,拿毛巾给她擦脸。
突然,古芳蓦地站起来,恨恨地大声说:
“离!不离,我是龟孙子养的!”
说罢,她转身冲出家门。
古芬抓起古芳丢在床上的挎包,急忙追出去。
古芬和古芳是双胞胎。出生时,如果顺产,古芳应该先出生。因是剖腹,古芬先取出,成了姐姐。几岁时候,古芬就拿出大人模样,学着父亲腔调,老气横秋地命令古芳做这做那。古芳不服气地噘着嘴:“就大我五分钟……本来,我该当姐的!……”怀她俩时,古清泰妻子全身浮肿,患上妊娠中毒症,产后,又留下高血压病根。女儿刚满五岁,她突发脑溢血,送医院途中断了气,一句话也没留下。古清泰在旅馆工作,收入微薄,艰难地抚养着两个女儿。有人劝他好歹找个老婆,帮他照料孩子。看着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他嘴上说:“我负担重,哪找合适的?算啰,不想这些。”心里,却唯恐找了后妈,女儿会受委屈。他一咬牙,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强撑着熬过来。
古芬同古芳长得极像,都是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鹅蛋般的脸型。米市街的邻居议论,这两姐妹,把父母的优点全继承了。古清泰个子较高,背有些伛偻,现着超过实际年龄的苍老,但脸部柔和的线条,从鼻梁两侧伸展到唇旁,一看就是温和淳朴的好人。古清泰妻子在世时,相貌虽然一般,肤色却很白,一双眼睛水汪汪的。古芬姐妹小时候,常穿一模一样的衣服,连古清泰也难分辨,经常唤错名字。长大后,两姐妹性格迥然不同。古芬像父亲,做事说话慢条斯理,一副温顺模样。古芳性格急,脾气犟,走路时,常骄傲地扬着脸,见人爱理不理。遇见她俩,从神态上,邻居能轻易认出谁是古芬,谁是古芳。
女儿小时,古清泰虽然又当爹又当妈,累得浑身像要散架,但心里不累。现在,女儿长大了,如同两朵娇艳的玫瑰,他的烦恼反倒多了。
三年多前,古芬高中毕业不久,不知怎么,同街上槐树大院的项淼接触起来。有段时间,晚饭后,项淼几乎天天来家里。项淼人长得俊朗,还算稳重老实,又是知根知底的街坊。古清泰睁只眼闭只眼,只当啥都不知道。没想到,项淼父母找到家里,客气而坚决地反对他俩交往。古芬是女儿家,脸面尤其重要。这一来,倒好像古芬嫁不出去,死乞白赖地高攀人家。古清泰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当晚就将古芬狠狠地训斥一通。古芬默默地流泪,什么也不说。古芳火爆爆地跳起来,要找项家说个究竟,古清泰好不容易拉住她。从此,古芬与项淼再无往来,有时在街上遇见,也远远地躲开,实在躲不掉,就将眼睛转到一旁,佯装没看见。一九七七年,古芬到旅馆工作后,经同事介绍,认识周恒,去年结了婚。
相比古芬,古芳的个人问题,更让古清泰头痛不已。说来说去,全怪这个高勋建。
初中到高中,古芬姐妹都在锦江中学读书。高勋建比她俩大四五岁,父亲是学校工友,住在学校里。不知什么时候,高勋建盯上古芳,追着送古芳手绢、雪花霜等小玩意儿,缠着要耍朋友。古芳一来才十七八岁,二来,也从心里看不起高勋建。高勋建长相猥琐,眼睛显得过于狭小,鼻子又似乎太大太扁;柿饼样的脸上,常露着色眯眯的表情。初中时候,看见高勋建,古芳不止一次地跟随同学,有节奏地喊着:“工友的儿,公有的儿!工友的儿,大家的儿!……”高勋建气急败坏地冲过来。她们像吃饱稻谷的麻雀,嬉闹着一哄而散。参加工作到洗染店后,神差鬼使似的,她竟与高勋建好上了。那时,高勋建在做水果生意,荷包里的钱塞得满满的。第一次到古家,他送古清泰一件黑呢大衣,送古芬一件浅米色高领羊毛衫。
古清泰早听姐妹俩谈过高勋建,对他从没什么好印象。他看也不看礼物,堵在天井门口,不让高勋建进女儿房间,说自己疲倦了,想睡觉,叫他快走。古家房子一进三间:第一间是堂屋,顺墙放着一张小床,古清泰住,旁边是用了二十来年的黑漆衣柜、双抽柜;第二间是天井,七八个平方米,用塑料瓦搭了半边,用作厨房;天井进去,是对称放着两张小床的古芬姐妹的卧室。见父亲这牛也拉不走的架势,古芳羞恼地嘀咕:“山猪吃不来细糠!人家好意送礼,摆啥皇帝老子模样?”古芬历来让着妹妹,听到这话,不由生气了:“啥话?你骂哪个?”眼见姐妹俩顶撞起来,高勋建赔着笑脸,做好做歹地劝走古芳。
连着两天,古芳干脆不回家,不知晚上住哪里。第三天,古清泰沉不住气了,叫古芬将妹妹找回来。趁着古芬在厨房做饭,古清泰温言好语地劝古芳,说高勋建是做生意的,不一定靠得住,最好别同他往来。
“你就见过一面,凭啥说人家靠不住?做生意哪点不好,政府都在鼓励,你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不找经济条件好的,未必去找叫花子?”
古芳牙尖齿利,每句话,都像一碗辣椒水,呛得古清泰说不出话。语意中,古芳还有些隐射古芬。周恒是机修工,收入较低,父母也是工人,家境一般。为了攒够结婚的钱,周恒咬着牙,每月存二十元,连四分钱一个的冰棍,也要掂量半天才买。
古清泰彻底没法了,只得由着古芳。三个月后,古芳与高勋建结婚了。高勋建花了两千元,在东南里一个小院买了两间房子,上面天花板,下面地板,很是气派。婚礼时,正值学校放寒假,他搬出教室里的桌椅板凳,请来厨师,在锦江中学操场摆了三十桌酒席。他嘴巴甜得像包满蜜,“爸爸”长“爸爸”短,对古清泰十分恭敬。听着米市街邻居的赞叹声,古清泰觉得大有面子。婚后,高勋建对古清泰很孝敬。知道古清泰要抽烟,累了喜欢喝几杯果酒,每次回来,他不买一条烟,就买两瓶樱桃酒。对古芬,高勋建也出手大方,送了一个金戒指、一根金项链。古芬嘴上推辞不要,说自己天天在旅馆干杂活,哪戴得出来,眼光却羡慕地粘在礼物上。古芳强要姐姐收下。周恒内疚地对古芬说:“怪我,没本事。”古芬安慰他:“我才不贪图这些。”心里,却若有若无,多少有一点失落。一段时间后,古清泰甚至觉得,二女婿对自己还好一些。每逢女儿女婿回来,他对高勋建客气得多,叫他坐下喝茶抽烟,任由周恒帮着做家务。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高勋建同古芳,竟然闹起离婚。
这段时间,古芳三天两头回米市街,约上古芬,商量离婚的事。高勋建答应离婚,补偿古芳一万元。古芳嫌少,开价至少三万,还要现在住的房子。高勋建认为古芳太狠,一口拒绝。古芳闹着又是上吊又是跳河,一次,还真吞了二十来颗安眠药,吓得高勋建慌忙送她去医院洗胃。
古芬劝她:“算了吧!不管咋说,他还是你丈夫。”
“丈夫?”古芳瞟着正在帮着理菜的周恒,不屑的一乜眼,“一丈内是夫,一丈外是啥,鬼都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