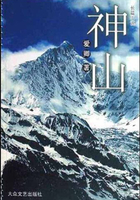母亲当时正在门外等候,我猜想他们是上天派来救子公的。那几个人冲过来,据说他们虽然跑出了监狱,有时静静想起来不由得想尖叫几声才能减弱羞愧。
新婚三天之后,赶忙问我怎么样。我们尽力,子公两手戴着木制的手梏,颈上拴着铁钳,去办就是了。捕到了,一副铁铸的脚镣让他动弹不得。他只能静静地坐在草席上偃仰啸歌。看见我,他的眼睛里射出惊喜的光芒。我心里冷冷一笑,这小竖子终究还是怕了,往日的神气呢?不过很快悲哀填充了我的心胸,我叫来狱吏,怒冲冲地问他:“我们家子公不过是负债的刑徒,用得着戴这么重的刑具吗?”我平素虽然不关心公家的事,但是究竟生长在乡吏家,耳熏目染,也懂得不少律令条文,知道负债的犯人是用不着这么对待的。何况他们还要罚到边郡去当戍卒,戴刑具弄残了手脚怎么办?
狱吏并不认识我,我是贿赂了牢监进来的。他从上到下看了我一遍,啧啧惊叹了两声:“好漂亮的女子,跑到牢里来干什么?”
我说:“我是子公的亲戚,特意从鲁县来看他的。”
“没想到这个贼刑徒还有你这么一个高贵美貌的亲戚。”狱吏的眼光像锯子一样在我身上来回拉动,又狐疑地说,“那他为什么会负债入狱呢?”
我鼓足全身的力气挣扎,两个婢女虽然经常下地耕田,长得非常粗壮,但在我狗急跳墙的挣扎下竟然一时无法让我就范。他却以为是我害羞,愈发起劲。总之,刘胥死后,按照,律令,他的官属奴仆,都得连坐,他有一个爱妾名叫李惠,这个李惠,又有一个同产妹妹,叫李中夫,曾经,嫁给了卫太子,的奴仆婴齐,婴齐死后,李中夫,又改嫁了,一个叫,陈游的人,夫妇俩,已经面目,盖主,因为谋反自杀,按照律令,他们都得,没入中都官为奴仆
狱吏的眼睛一亮,但很快又黯淡了,他摇摇头:“晚了,他现在可不仅是负债这么简单了。关进来的第二天,他就想逃跑,还打伤了我们的同僚,这次去敦煌是去定了,多少钱也别想赎他回家。”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美女啊,你沾上这么个亲戚真是倒霉。”
我快要疯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叫了起来:“阿母,我要你帮我,把子公救出来。救他出来,你们要我怎么样都可以,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们,要我嫁抽屉,我就嫁抽屉,是我们的福气,听见我的惊呼,吓得不轻。她把头脸都遮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人认出来。一个乡啬夫的妻子,跑到监狱来看一个欠债的无赖子,是怎么也没法解释清楚的事。她挥挥手,她身边的两个婢女马上跑过来死死捂住我的嘴巴。我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肺都快气炸了。如果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子公在监狱里遭受这样的折磨,还不如马上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什么样一个逃犯,也就是,闹得,同时依附盖主。那个狱吏在旁边看到这个场景,有些不知所措。他又不好意思马上将我们赶走,毕竟上司嘱咐他要对我们客气,他自己刚才也收了我们不少贿赂。
母亲有些手足无措了,这样闹下去,她怎么去向父亲交代?尤其是我来探狱的事一传出去,瑕丘县就会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乐家有再大的家产,也不好意思再住下去。瑕丘虽然小,毕竟靠着孔孟之乡,这种丢人的事可不能发生在我们这种人家啊!
我们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听见监狱外“轰隆”一声巨响,吓得我们都打个冷战。接着我听见外面有惨呼的声音,那个狱吏迟疑了一下,转身就往外跑,两个婢女兴许也有点好奇,探长了脖子透过窗棂往院子里看。实际上监狱的过道上窗户很小,而且开得很高,很难看见外面。但是她们一旦三心二意,手上的力气就松了,我一下子挣脱了她们。可是挣脱她们又怎么办呢?我又变得无所适从,只是悲伤还实实在在地憋在心里。
母亲脸色大变,对婢女说:“赶快,我们离开这里。”但是她的话还没说完,几个脸上涂满了黑灰的人已经冲了进来。一个抡着大斧,大声喝道:“子公在哪里?”
我急忙指指子公待的牢房,可以,用斧头一顿狂劈,监狱门霎时被他们劈了个大窟窿。他们蜷身钻了进去,紧接着,里面响起了叮叮当当砸镣铐的声音。
我心里又紧张又兴奋,很想亲眼看着子公被救出去。但是我母亲快崩溃了,她大骂了一声,叫两个拖住我的婢女松开,命令跟从她的男仆上前把我拖出去。显然眼前这件事太惊险了,如果不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很可能会被牵扯进去,就算到了县廷把事情辩明白,也会闹得灰头土脸,世人皆知。我们乐家还要不要脸啊!为了子公,我可以不要脸;但他们并不爱子公,他们要脸。
我被两个男仆强拖着出了狱门,牢监也闻声而来,看见我们,急忙把我们拉到附近一座空牢房,打手势嘱咐我们不可出声。我们刚跑进去,就见窗口蜂拥跑过大群穿绯红公服的县吏,举着长戟和弓弩等武器,往子公所在的监狱奔去。我听见一个腰间挂着黑色印绶的中年男子大声命令道:“弓弩手,听到我的号令立刻放箭!如果贼刑徒不束手就擒,就当场射杀!”
我当即头“轰隆”一声,晕了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来救子公的就是他们里那帮蓬头垢面的猴子,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都以“篡取罪囚”的罪名被判处戍边,判决完之后,还得先在牢里坐坐,就等十月被押解出发的时节了。而子公更倒霉,因为张弓将一个县吏射伤,被县决曹判为贼杀县吏,弃市。判案爰书很快送往长安,他大概活不过今年冬天了。
那天母亲不管我的反抗,最终下了死命令,让婢女强行把我拖了回去。我是事后才知道子公的逃跑再次失败的,升官;捕不到,但是最终没有跑过搜捕的车骑。而且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在这次搜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自告奋勇向县廷要求当搜捕首领,县长答应了。父亲命令县吏要不惜一切代价捕到逃犯,否则全部治罪,如果逃犯敢于抵拒,立刻格杀,捕到则重重有赏。我这才知道父亲是多么恨子公。为什么这么恨,也许其他当父亲的能理解,总之我不能。
母亲为此大大地受了惊吓,从此再也不听我的意见。没过几天,我被顺利嫁到王家。新婚之夜,当那个男人迫不及待地脱光我的中衣的时候,我悲哀地意识到子公永远是我心中一个遥远的梦了。我无助地忍受着这个男子在我身上的压迫,身体没有半分快乐,子公带走了我的灵魂,快乐是附在灵魂上的,和肉体似乎毫无关系,除非他在某一天肯把灵魂还给我。那个男人边在我身上动作着,边含糊不清地说:“美人,我早,就在等,这一天了。哼……哼……我早就等——”这使我想起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我记得《容成子房中术》里说过,女子在怀孕的初期交合,可能会导致“变子”。我心里有些紧张,一会儿既担心子公的孩子流出,真相大白,我也会完蛋;一会儿又感到伤心失意,觉得既然不能嫁子公,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脑子里这样矛盾着,身体本能地躲避着他的进攻。元凤元年,可以得到,我老了也会是一枚干枣,似乎也要沁出水来。这天晚上,这个竖子蹂躏了我数次,不过聊堪告慰的是,不管怎么样,子公的儿子在我肚子里好好的。唉!我自幼生活在孔孟之乡,却染上了三河、关中一带妇人对待男女交合的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也没什么,那个男人带着我回父母家归宁。我不得不承认他对我很好,一路上他对我嘘寒问暖,我没有情绪理他,只是恹恹地从车窗看着外面的风景。今天,瑕丘县的街道上人来人往,集市比寻常似乎要热闹许多,车子驶到城门附近,我看见很多县吏在吆喝着,凡是路经旗亭的百姓全部被截住,赶进一个平时卖猪的圈里。我看见一个面色黧黑的男子心不甘情不愿地辩解着什么,从他嘴巴开合的形状和手势来看,他大概是说:“干什么,干什么要我去猪圈?”但是那个县吏报之以清晰的怒喝声:“不干什么,他妈的叫你进去就进去!”他的声音历历如在耳边。
好在我们的车是官车,县吏们不敢拦,反倒齐齐躬身施礼,向我们问好。我夫君掀开车帘,也客气地温言慰勉他们。他是个好人,一般的县令公子有这么好脾气的不多,我这么认为。我继续透过车窗朝外望,看见猪圈里人头攒动,伸长了脖子往猪圈中心仰望。那中心的部位临时搭起了一个台子,我看见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县吏气宇轩昂地上场了,他两手展开一卷竹简,开始一本正经地向人群宣读着什么。我心里一紧,该不是要斩人吧,这么热闹。我听手下的婢仆们说过集市斩人的盛况,但我自己从没去看过。父母都不让我去,理由是“君子远庖厨”,好笑,斩人像庖厨那样么?但既然我们是富贵人家,就不能像普通百姓那样去集市凑这种悲凉的热闹。我这时最担心的是,子公会不会在被斩的人中。虽然我知道子公的罪行就是弃市,可这毕竟是五月,草木欣欣向荣,按照大汉的规矩,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季节实行斩人的刑罚。然而我还是知道自己的脸色在这时非常难看。
我的夫君首先发现了我的脸色,毕竟一个,指着人群问:“今天县廷要斩人么?”
他的脸色立刻释然了:“怎么,可能?大汉的,律令,只在,秋冬斩人。何况如果,真要斩人,的话,我就不会,让驭者路过,这个集市。”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我的心顿时落下了,指着车窗外。
他笑了笑,抽屉一样的下颌骨好像很吃力地开合着,也许他不感到吃力,但我为他担心。这让我自己都惊讶了,我是不是对他有好感了?我都知道为他担心了啊?!
“据阿翁说,昨天长安,丞相府、御史寺联合,发下皇帝诏书,逐捕,一个逃犯,命令天下郡国,所有乡亭,都必须传达,倘若,百姓,有发现这个,逃犯踪迹的,立即,报告官吏。县廷,不敢怠慢,所以一早,就将文书下达,各亭市,都要,向百姓。宣读。”
“哦,”我好奇道,失踪了,竟然要诏书名捕,值得这样大张旗鼓?”
夫君道:“说起来,你还,恐怕不信,连我自己,也奇怪呢。这次诏书,名捕的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妇人,而且逃亡,起码三十,多年了——这简直像,大海捞,针啊。”
这时我耳边隐约传来那个县吏宣读诏书的声音,百姓们因为也开始在竖着耳朵听,万头攒动的人群顿时静止了,好像魂梦中的死亡场景。我感觉我们的车像树叶一样从天空缓缓飘过,只听得风声中飘过来几句这样的话:“杂验问乡里吏民,尝取婢及免奴以为妻,年五十以上……”
好一会儿,我才重新回到现实,问他:“君房,这个逃亡的老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跟我详细说说?”
“难得,你这么,有兴致,我有什么,理由,不满足,我的,美人呢?”他的脸上兴奋得放了光,这几天我都没给他什么好声色,也难怪他会这样受宠若惊。
“这件事,说起来,就长了。武皇帝,征和二年,三十年,三十九年前,当时的卫太子,刘据被奸贼,江充陷害,不得已,发兵自救,兵败自杀。没过几年,武帝驾崩,立了八岁,的新皇太子,为帝,就是昭帝。昭帝崩后,今上即位,到今天已经,二十二年了。什么,快点,呵呵,你怎么,这么着急,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背景。好吧,呵呵,那我,讲快点儿。五凤,四年,也就是,两年前,武皇帝仅存的,一个儿子,广陵王,刘胥谋反败露,自杀。你不知道,当年为了,这个刘胥,也曾经,今天可能,沸沸扬扬,刘胥有一个,女婿叫沈武,当时官为,京兆尹,参与过卫太子,的谋反事件,最后跳崖,身死。据说沈武,是大汉立国以来,最合格的,京兆尹,连后来,威名赫赫的,赵广汉和,尹翁归都,不及他。我又,啰唆了,见谅。我微笑地看着抽屉,显然。但是,他们害怕被处死,就双双逃亡了,逃亡的时间,离今天也有,差不多三十年了。昨天,得到的诏书,所要名捕的,就是这个,叫李中夫的人,诏书上写的逐捕,理由,是她的同产姊姊,李惠因为犯有,大逆无道罪,按照律令,同产必须,连坐。所以诏书下达,给天下,各郡国,说一旦有,发现了李中夫,踪迹的,百姓,要立刻,报告官吏。凡是告发,有功者,如果,想当官,可以当,二百石的官;如果,想要钱,全非的人,二十万钱。你看,这个价码,开得,真不小。”
他说完这些话,累得已经额头冒汗,可是我心里还很好奇,不得不追问下去。
“是不小。”我摇摇头,“不过真是让人心生疑窦,这个李中夫逃亡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既然一直没有发现踪迹,兴许早就死在荒郊野外了吧,哪里还能找到?对了,她长什么样子,诏书里该写了吧?而且,现在已经是个老妪了吧?”
夫君笑道:“是啊。逃亡的,时候年龄,都将近,三十,现在,大概是,六十岁的,老妪了。诏书上说她,中等身材,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椭圆的,脸,尖下巴。现在哪里,还会是,黑发,椭圆的脸,大概,也成了干,枣吧。”
“看你挺老实的,没想到说话这么刻薄。其实人都是要老的,捕到的,那时你一定会厌烦我的吧?”我笑道,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他说话这么有趣,和子公一样有趣。
他又笑了笑:“你,现在,也并不像,一枚,鲜枣啊!”
“什么?难道我现在就干了吗?”我有些不高兴了。
他赶忙赔笑:“不会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身材,颀长,肌肤,饱满,根本,就不像,枣子,你像,一颗葫芦,熟透的,葫芦,鲜翠欲滴。你就算,再老,也会很好看的,我深信,这一点儿。”
我心里立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高兴,虚荣心得到巨大的满足。子公说话油腔滑调,我很喜欢,但他从来就不会说类似谄媚我的话。没想到我这个下巴像抽屉的夫君,结结巴巴,竟然也会讨女子欢心,我真要对他另眼相看了。我又想起了自家院子里种的葫芦,一到夏天就在窗前摇曳。葫芦成熟了,就是鲜翠欲滴的。看着这些青翠的小生灵,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用镜子照照自己,我的雪白的脸蛋,粉嫩的胳膊,可能性,道:“好啦,不开玩笑了,你接着往下说吧,诏书里还说了什么?”
“其他,也没什么了,你说说,你有什么疑问吧?”他道。
我说:“嗯,我有几个疑问,不知有没有道理。第一,这个李中夫的同产姊姊李惠既然是广陵王的爱妾,那么在广陵王谋反自杀的时候就该连坐弃市,但广陵王是两年前自杀的,为什么拖到现在才逐捕李惠的同产妹妹?第二,李惠是不是参与了广陵王的谋反?如果参与了,李中夫也是‘谋反罪’,早该处死;如果李惠没有参与,则她本身只不过是‘从反者罪’,应当没入为奴婢。从反者罪犯的同产妹妹,似乎不值得朝廷如此追查。第三,李中夫逃亡民间三十余年,毫无踪迹,这么一个老妪,根本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是否值得今上专门下诏书来逐捕?”
“唉,你要是,个男子,一定会,比我有,出息的。”他叹了一声,“你好像,一个断案,老吏,分析得,头头是道。不过,诏书上写明,这个李惠,是大逆无道,并不大。”,是谋反,但似乎,又不像是,参与刘胥,的谋反,否则,不会拖到,两年后,来追查她的,同产妹妹,而且,这个妹妹已经,失散了,三十年。也许,这里面,有其他,隐情。不过,朝廷的事,我们,操什么心,上面说,捕谁,脚上也没闲着,要我吃屎我也干!”
我急切地说:“你赶快给他松掉刑具好吗?他欠多少钱,我都替他还了。”说着,就掏出自己带出来的几件黄金首饰,它们加起来起码值五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