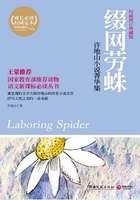一
一早到机场,从锦都飞到杭州,再到莫干山路“之江饭店”。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鲁丽实在有些疲倦。老同学见面的兴奋和激动,已如潮浪渐次退去。她想抓紧时间小憩。下午3点,同学联谊会正式召开。
她启动中央空调,清爽的冷气,顿时从风口缓缓吹出。倒在松软的席梦思床上,她的双腿连踢几下,高跟皮鞋立刻飞远。她懒懒地侧过身,想尽快入睡。可是,一合上眼睛,失望就像幽灵缠着她:他呢,怎么没来?……
两个多月前,李明红来电话,说留在杭州的几个同学,正在筹备同学联谊会,8月中旬相约杭州。毕业后,李明红分在重庆,同鲁丽偶有联系。
“想想,1982年大学毕业,一晃,15年过去了,大多数人都没见过。你一定要参加,一定!”李明红叮咛。
“会去多少人?”鲁丽试探着问。
“基本都参加。”李明红背出一大串同学。其中,有那个令她一听就心跳异常的名字。
“我尽量去。”她表面平静,内心却翻江倒海。
在浙江医科大学读书时,她与他——同班同学聂劲松,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毕业回锦都,她把这段伤痛深藏心里,对谁也没讲过,甚至父母、丈夫也从不知晓。十多年来,她相夫教子,每天忙碌在医院和家庭,没有精力也不愿去揭开这层伤疤。前年,丈夫患肝癌去世后,也许是孤独,也许是怀旧,她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他。这次来杭州参加同学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见他。昨夜,沉浸在过去的回忆和见面的遐想里,她一直没睡好。
想着,睡意越来越远,她索性下床,去卫生间洗澡。暖暖的水流,在她光洁的肌肤上流淌,“哗哗”的水声,像在欢快地歌唱。随着身体的舒洁和惬意,要强和自尊又回到她身上。“他来不来,与我有啥关系?”她嘲弄地问自己。她用水反复冲涤胸部,似乎要把那些迷惘的记忆荡得一干二净。
洗完澡,她穿上自己带来的睡衣,对着梳妆镜细细打扮。眼前这张脸,还是那白皙的肌肤,秀美的鼻梁和嘴唇,黑幽幽的瞳孔;眼角,仍然细腻柔嫩,没有半丝皱纹——十几年的风霜,仿佛没在上面留下痕迹。她骄傲地端详自己,不由生出高高在上的自信。刚才那几个女同学,虽然精心涂唇描眉,但是与她一比,就像老了许多。难怪,发起这次联谊会的王启志——杭州一家药业连锁公司老板,见到她就惊诧地张大嘴巴:“系花就是系花,还是这么靓丽!”
她拉开行李箱,挑出一件藕荷色蝙蝠袖衬衣,一条墨绿色长裙。换上衣服,她对着镜子,细心地抚抚头发,迈着碎步,不快不慢地走出房间。
小会议室里,已经坐着二十多个天南海北来的同学。进门,鲁丽一眼看见,聂劲松站在窗前,正与几个同学聊着。还是那一米七八的个子、魁伟得像坐小山的身段,在哪里,都能一下抓住人的眼光。“他来了。来了!”鲁丽一阵惊喜,瞬间又漫出怨气:“到了,也不给我来个电话!……”她热情地与其他同学寒暄,装做没有看见他。听到她的声音,聂劲松转过头,兴奋地凝望着她。她矜持地掉开目光,与王启志大声说笑。
联谊会开始了,王启志充满激情地回忆大学生活,感叹转瞬即逝的青春,说起今天相聚的不易。听着听着,鲁丽的心渐渐飘远,不自禁地想起往事……
鲁丽爱上聂劲松,不仅因为他高大英俊,是足球场上的中锋,也不仅因为他学习刻苦,待人真诚豪爽,还因为一件不为人知的小事。
一次,班上同学去灵隐寺玩。鲁丽喜欢摄影,是学校摄影社成员。她带着自己的海鸥4C相机,不停地帮同学照相。飞来峰前,她想留影纪念。不巧,同学要么在嶙峋的怪石上攀爬,要么在冷泉亭上休息。只有聂劲松,傻乎乎地站在一边。她叫聂劲松帮她照相。
“我不会,从没用过相机。”聂劲松推辞。
“我教你,比踢足球容易。”鲁丽拿着相机,耐心地给他做示范,怎样把人放进取景框,怎样按快门。
“我笨手笨脚,别把相机搞坏了。”聂劲松双手蒲扇样地晃着,就是不接相机。直到鲁丽生气地冷下脸,他才战战兢兢地拿过相机,勉强照了几张。晚上,躲在寝室里,窗帘遮得密密实实,用红布将电灯套上,鲁丽自己冲洗相片。显影出来,挟着湿漉漉的照片一看,她不由大为恼怒。聂劲松帮她照的几张,不是面部模糊,就是人是斜的,有一张,甚至头也没有,好像大半边尸体立在那里。第二天,她找到聂劲松,生气地把相片向桌上一丢:“你看,照的啥东西?”
聂劲松捏着相片,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讷讷地道歉。
几个同学说着风凉话,幸灾乐祸地大笑。
十多天后,聂劲松主动找到鲁丽,摸出一个胶卷:“我们再去灵隐寺,我保证给你照好。”
“你?”鲁丽不相信地一挑眼睛。
“对。我天天都在学摄影知识。”聂劲松认真地说。为了证明自己,他随口说起光圈、快门、曝光、焦距等。原来,那天以后,聂劲松下决心学会摄影。他天天晚上到图书馆,囫囵吞枣一样,读了好几本摄影书籍,还做了几千字笔记。
鲁丽心里,霎时荡开感动的涟漪,几乎不假思索地爱上他。就为照废几张相片,天天去图书馆看书,还记笔记,这是何等的真诚实在!而且她清楚,聂劲松来自烟台农村,家庭相当困难。平时他在食堂打饭,专挑最便宜的菜,有时,吃个馒头算一顿。这个胶卷,又要花掉他几天的生活费。
“好,看看你的技术。”鲁丽娇嗔地一推他。
由于鲁丽主动,他们很快相爱了。聂劲松大鲁丽三岁,恢复高考进大学时,已经26岁。他对鲁丽,既有恋人的激情和温柔,又有父兄般的关心和体贴。学校离西湖不远,走路20分钟左右。柳浪闻莺前,孤山下,苏堤上,到处都有他俩相依相偎的影子。一次,去绍兴游玩,他们终于将自己交给对方……
“鲁丽!——”谁在喊。她一惊,思绪被打断,惶然地抬起头。
“想啥,那么出神?该你介绍自己了。”李明红好笑地提醒。
“哦。”鲁丽镇静下来,轻轻地一拂额前的发丝,含笑起身:“学校出来,我分到锦都儿童医院,一直工作至今。毕业第二年,我结了婚。现在,儿子13岁,读初一。”
“这么简单?职称、职务、收入、婚外恋、老公……”王启志打趣地问。李明红慌忙一碰他,制止他说下去。中午,李明红悄悄给他讲过,鲁丽丈夫已经去世。
王启志尴尬地点点头:“下面该谁了?接着说。”
鲁丽淡定地笑着,似乎不经意地一扫聂劲松。他纹丝不动地坐着;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正探询地注视着她。
二
晚饭一共三桌。不知无心还是有意,李明红将鲁丽和聂劲松安排在同桌。他俩对面坐着,眼光刚一触到,又窘涩地闪开。大家知道,他们曾经爱得死去活来,后来又突然分开——为了避免难堪,都谨慎地不去触起他俩往事。
李明红环视着典雅的宴会厅,打量着叫花鸡、酱鸭、西湖醋鱼等地方特色菜,羡慕地问:“这个宾馆不错,收费一定很贵?”
“当然。这是省政府下属酒店,在我们杭州大大有名。不是王总有关系,不容易订到。”一个杭州同学插话。
“本来,我想安排在延安路一带,离医大近一点儿,也有怀旧的意思。可是,大宾馆会议多,小饭店设施差。想来想去,干脆到这里。环境不错,离西湖也不算太远。”王启志解释道,话头一转:“哦,你们听说没有,医大要合并进浙大?”
“真的?”几个声音同时问。接着,大家无限怀念地谈起读书时的种种趣闻,谈起这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劲松,你怎么不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地喝酒?放心,山东大汉再善饮,也喝不完杭州的酒啊!”王启志笑道。
聂劲松憨厚地笑笑:“我的话本来就少,想说的,又被你们说完了。听你们讲,也蛮有趣的。”
“怎么,也不对鲁丽说几句?”王启志借酒调侃。
聂劲松的脸,霎时红到耳根。他讷讷地想说什么。鲁丽大方地一笑,模仿他的山东腔普通话:“刚才自我介绍时,他已经说了,他在青岛一家大医院,正在评副高;女儿14岁,上初一;这么多年虽然平常,但还顺利。混到这个地步,对得起老聂家了!……”
大家开心地笑起来。
聂劲松感激地一瞥鲁丽。
鲁丽机械地吃着菜。渐渐,身边的喧嚣仿佛沉寂,聂劲松好像幻化出另一副面容:表情颓丧又痛苦,嘴唇嚅动几下,努力挤出一丝笑容,笑得苦涩、辛酸、无奈……
那是毕业前两个月,聂劲松的父亲来学校以后。一天晚上,聂劲松把鲁丽约到学校足球场上,忽然没头没脑地说,要毕业了,他们只有分开。
“为什么?为什么呢?你给我一个理由!”犹如惊雷炸响,鲁丽不敢相信地一怔,立即撕心裂肺地大喊起来。
聂劲松求饶地要她小点声,吞吞吐吐地说出原因。
16岁时,家里给他订下“娃娃亲”,女方小他五岁,是邻村果农。因为他发愤读书,一心想出人头地,婚期一推再推。与鲁丽相爱后,他写信告诉父亲,他已爱上一个同学,要家里退婚。那时,女方已经住到他家,帮着照顾父母、下地干活,像过门的媳妇。“你对得起人家吗?读了大学,就想当陈世美?我们老聂家祖宗18代的脸,被你丢尽了!方圆一二十里,哪个不知她是你媳妇,你是她男人?你要敢赖婚,我先找校长告你,再死在你面前。”父亲当即赶到学校,狂暴地脱下鞋子打他,又倔强地闷着抽烟,不说话,不吃饭。
在父亲的威逼下,聂劲松也感到的确对不起女方。可是,他又深深地爱着鲁丽。正值分配前夕,假如父亲真的大闹一通,不仅自己挨处分,鲁丽也会受到牵连。痛苦地犹豫几天,他找到鲁丽,硬着心肠提出分手。
“这边是爱情。那边,是你父亲和那个农村女人。你自己掂量。”鲁丽从震惊中醒来,愤愤地说。
聂劲松嗫嚅着,一副欲语又止的可怜相,但他愧疚而乞求的目光,清楚地表明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