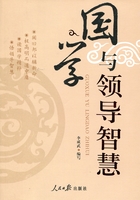一天里发落了两个嫔妃,低位的陆氏且先不提,章悦夫人被削了宫权,总要有人再掌宫权——横竖不能让皇帝料理着政务再来为后宫操心。
目下的后宫和从前不太一样。若在从前,没有皇后、没有掌权嫔妃,总还能有皇太后或者太皇太后来掌理后宫诸事,可本朝……
皇帝的生母殉了先帝,太皇太后倒是还健在,可也不在锦都宫里——她老人家跟着太上太皇云游去了,两耳不闻后宫事。
是以皇帝能做的,只能是从现有的嫔妃里挑一个来执掌凤印。
这事可说是毫无悬念可言,既然夺了章悦夫人的权,便该由佳瑜夫人窦绾来掌凤印。莫说别的,她本就是该做皇后的人,也住着长秋宫,凤印不给她给谁?
当晚下来的旨意却有些出乎众人意料。皇帝命娴妃和佳瑜夫人共理六宫事,不分主次,谁也不掌凤印。
这就奇了,娴妃虽则也是后宫里口碑颇好的人,但若说掌权之事,一时不该轮到她。何况前不久还有一桩事——皇帝本是许她为章悦夫人协理六宫的,不几日却出了错处,又撤了权。
按理皇帝对她该是有所不满的,又或是为了避嫌也不该用她,怎的这次反倒更器重了?
众人一壁揣摩着皇帝的心思,一壁思量着接下来该往哪边靠、盘算着章悦夫人是否还靠得住,很快却又出了另一道石破惊天的消息。
——据御前的人说,皇帝传了佳瑜夫人和娴妃去、下了旨,接着自然免不了嘱咐二人两句,末了竟是提了一句:有什么拿不准的事,大可问充仪几句,她从前把太子府里打理得不错,对这些熟。
不咸不淡的一句话,让后宫上下都哑了声。
一直以来,苏妤曾是正妻这事是谁都不敢在皇帝面前轻易提起的,因为皇帝不喜苏妤,也因为得罪不起章悦夫人。
皇帝自己更是不曾提过。人人都知道他曾经多么厌恶苏妤,厌恶到她做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错。
如今却突然自己亲口提了,还毫不避讳地说了她从前的太子妃身份,让佳瑜夫人和娴妃多去请教她去……
那二人会不会去并无所谓,要紧的是……莫不是皇帝眼里最会打理六宫的,还是这位从前的正妻?
难不成两年多来大家都搞错了局势?
后宫陷入了一种罕见的沉寂。谁也不敢擅言、不敢擅动,都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生怕一不小心寻错了靠山,搞不好就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这种小心翼翼的气氛在各处都能体现出来,晨省时犹为明显。章悦夫人失权,晨省自是改到了长秋宫去,苏妤仍禁着足,免了这一道。娴妃回宫后却告诉她说:“两年多了,也没见过晨省能这么消停。一个个都安静得很,大气也不敢出的样子。”
更是没人敢提章悦夫人一句吧。
苏妤笑了一笑,素手轻碾着眼前碟子里的花瓣,一点点地碾出汁液来,轻轻笑道:“这样挺好。不过也干净不了多久,她们很快就得拿定主意,不知道跟得对不对也得赌一把跟一个。宫里头,墙头草是最容不下的。”
娴妃点头,垂眸看着那碟子里慢慢漾开的花汁,幽幽又道:“新家人子也该入宫了,是消停不了多久了。”
不仅如此,叶景秋也不会这么忍下去。
那天的事,确是她害了叶景秋。手段说不上高明却很管用,利用的不过是陆才人的“蠢”罢了。
临离开月薇宫时,苏妤心思一动,折回了娴妃的住处,笑对她说:“捡日不如撞日,我们做得突然,她更加没有防备。”
她不想惊动齐眉大长公主,但既然想好了要做,总不好错过这个机会。便托娴妃差了个级别高些的女官去传话,说自己是叶景秋身边的人、说苏妤要去成舒殿面圣,再挑唆几句,就凭陆氏那么点心思……太好骗了。
她不会有防心,没有防心也就不会刻意去留心那传话之人长什么样。
是以陆氏不能证明那人就是叶景秋差去的,叶景秋也没本事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晚娴妃悠悠道:“任章悦夫人怎样的谨慎,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那陆氏身上栽跟头,当真是阴沟里翻船。”
“嘁。”苏妤听言一声不屑的轻笑,“她要拉拢这种蠢人,就该知道兴许有朝一日会出岔子。还真当后宫是她一人说了算了么?这陆氏,便是我不利用,只怕佳瑜夫人也得用。”
那还不如自己出这一口气。
齐眉大长公主果真是要在宫里留些日子的,就住在晳妍宫。苏妤禁着足本不便去见,皇帝闻之却笑道:“想去就去吧,也不是什么大事。旁人问起来,说是大长公主传你便是了。”
反正齐眉大长公主也不会不护着她。
又过两天,宫正司对于皇长子早产之事有了结果,从绮黎宫寻出的各样人证、物证足以证苏妤的清白。
苏妤自知那些个证据是怎么来的,还是颇为严肃地领了解禁的旨意,叩首谢恩。
是以也没别的事可作,便几乎日日去拜见齐眉大长公主。倒是不曾傍晚去过,这日傍晚却很是有空,佳瑜夫人传口谕说觉得疲乏,免了当晚的昏定,苏妤用罢晚膳就悠闲地和折枝一并散步去了,走了一会儿,离晳妍宫已不远,索性去看看。
早春,天黑得仍早,晳妍宫里灯火通明。苏妤踏进宫门去,即有宦官要去通禀,被她伸手一拉,笑道:“这么晚了,我也没什么大事,不必通禀了,免得又劳舅母招待。”
说着便径自往正殿去了。天色已逐渐泛黑,看不清周遭,待得走近了,才看出门口候着的那人是御前的宦官何匀,苏妤朝里望了一望,问他:“陛下在?”
何匀一揖:“是,娘娘可是来见大长公主的?臣去通禀。”
既然皇帝在,再不通禀便不合宜了。苏妤点点头,何匀刚要踏进去,苏妤却听得殿里传来齐眉大长公主微有愠怒的一句:“这样的事,陛下怎么能不告诉她!”
直觉告诉她这是和她有关的事情。苏妤一拦何匀,语声冷了些许:“大人且慢。”
侧耳倾听,里面又道:“苏澈才十五岁,他如是有什么闪失,陛下伤的不止是苏家,还有霍老将军!”
苏澈?!苏妤大惊,惊得面色发白。何匀看出她神色的变化,滞了一滞又忙不迭地道:“臣去通禀……”
“大人!”苏妤将他喝住,何匀不敢再出声。
殿中的谈话还在继续,皇帝似有一叹,道:“朕知道,所以才更不想告诉阿妤。她知道了也不能如何,何必让她徒增烦扰?”
“那是她亲弟弟!”齐眉大长公主不悦道,“她母亲去世得早,这两年和父亲也多有不合,就这么个弟弟始终还亲近。苏澈的事,陛下不该瞒她。”
“姑母。”皇帝沉了一沉,遂又缓道,“朕也不想瞒她,但毕竟……”他摇了摇头,“苏澈是朕派出去办事的,如今这般……”
“陛下说过要好好待她。”齐眉大长公主锁了眉头,一字一顿地说,“夫妻间不能失了坦诚……”语出一滞,转而又说,“即便她现在已不是陛下的妻子,但陛下既想好好待她,又怎能瞒着她这样的事?”
皇帝面容沉肃,思了一思,缓言道:“待他好些,朕自会告诉阿妤。”
“那他若是死了呢?”齐眉大长公主不留情面道,“如是他就此死了,陛下不让阿妤见他最后一面,阿妤又会如何?”
“姑母……”贺兰子珩刚欲再言,便听得外面一声惊呼:“充仪娘娘!”
一惊间循声望去,立即夺出了门。
何匀和折枝一起扶着苏妤,苏妤却好像身体不受控制似的一味地向下坠着,面色苍白得连嘴唇也失了血色。
“阿妤。”皇帝也忙伸手去扶,触及她胳膊时便觉她倏有栗然,双目无神地望一望他,却是仍站不起来。
何匀和折枝各自垂首不敢言,皇帝视线一扫,略作踌躇便弯下腰去,手上一使力将苏妤打横抱了起来,一边往殿里走着一边吩咐徐幽道:“去传御医。”
苏妤先前莫名其妙地昏倒过,后来又有过全然没有因由的梦魇,他总担心她会不会是得了什么怪病,可她平日里又都正常得很。但现在这情形……还是请御医走一趟来得稳妥。
径直去了寝殿,齐眉大长公主也随了进来。皇帝把苏妤搁在榻上,只感她一直在不住地发着抖,贝齿不停地相磕轻响,死死地望着他,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
“阿妤……”皇帝想和她解释清楚,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连笑也笑不出分毫。
苏妤觉得不可控制的发抖让她的牙齿嗑得都生了疼,抓着他袖口的手也根本松不开力,死死地攥着,隔着两层衣料,仍能觉得手心被指甲掐得隐隐作痛。
“陛下……”她终于艰难地出了声,每一个字都掀起了一阵心中的慌张,还有那久违的对他的恨意,“苏澈……”
在她最难的日子里,家人的安危可说是她唯一的支柱,现在亦是。况且……她曾很清楚地在梦中看到过他们的死,心知自己根本无力承受至亲的离世。
好不容易……她以为事情可以不一样、以为梦中的那些事是可以避开的,却就这么快地发生了。
“他才十五岁……”每一个字都像是死命逼出来的,冷涔涔地沁出齿间,情绪复杂。
苏妤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却知不管是因为何事,他想要苏澈的命都太容易了,无论用明用暗,苏澈……甚至是整个苏家都没有反击的余地。
怔然凝望他许久,苏妤在慌乱中近乎崩溃,梦中的一幕幕再度呈现在眼前,瞬间击碎了她所有的不屈。
“陛下……您放过他……”
这句话如利剑般直刺入贺兰子珩心中。他知道,如是苏妤得知了此事,必定会担心、会难过;但他没有想到,听说了苏澈出事却又不知细由的苏妤,头一个想到的竟是觉得他要杀苏澈。
她对他的信任还是这么薄弱。但她可以不信他,他却不能因此不跟她解释。前世,他可以随意对任何一个令他不快的嫔妃置之不理,今生也可以,只除了她。
“苏澈没事。”皇帝略勾起一笑,手隔着袖子反握住她死攥着他衣袖的手,循循解释道,“朕没动他,只是前阵子差他去和沈晔一起查些事情——这事你是知道的。后来途中出了些岔子,苏澈受了重伤昏迷不醒。朕怕你担心才没有告诉你,差了御医去医治。”他故作轻松地捏了捏她的手,“会好的。”
苏妤在他的解释中逐渐平静下来,认认真真地端详他许久,寻不到什么说谎或是隐瞒的痕迹。略微放下了心,犹是惊魂未定地又问了一句:“真的?”
“嗯。”看着苏妤的无助,贺兰子珩忽而有一种在哄小孩的错觉。回了回神,俯身吻在她额头上,低低道,“君无戏言,不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