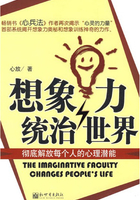“婕妤不必多礼。”佳瑜夫人浅淡一笑,遂侧身一引请皇帝入座。皇帝回头睇了苏妤一眼,见她双眸微垂目不斜视,径自去落了座。
苏妤松了口气,亦去自己的位子上坐了。宫宴总是很热闹,一贯的觥筹交错。酒过三巡,皇帝搁下杯子往殿下望去,九阶之上的众人见其神色便安静下来,九阶之下随即也安静下来。
皇帝静了一静,思量着沉稳道:“苏澈来了吗?”
苏妤微惊。他起先答应过她,如若她不愿意便可不见苏澈,他会替她拦着,何以主动问起来?
苏澈到殿中行了大礼,苏妤疑惑地望向御座,正巧皇帝也正看过来,视线一触,皇帝招了招手示意她过去。
苏妤在四下安寂中离座上前,在他案前不远处福了一福,才去他身边坐了。皇帝一握她的手,复又朗朗道:“苏澈,你姐姐刚晋了位份,头一件事就是给你谋了个官职。”
苏妤怔住,拜伏在地的苏澈也一惊。阖宫上下谁不知道,苏妤今年十八岁,苏澈才十五岁,一个未及冠的少年,能担得起什么官职?皇帝这么特意提起来,难不成不仅突然而然地宠了苏妤、还要直接宠上天去,甚至把苏家捧起来?
皆安静地听着,心里都明白,如若苏妤当真不知天高地厚地给这十五岁的弟弟求了什么高职,朝堂上必定又要闹上一番。
苏妤始终紧张地望着皇帝,皇帝却是没有看她。沉默一会儿才再度开了口:“沈大人常说禁军都尉府人手不够,你就先去做个校令。”
没有太多赘述,瞬间却是一阵倒抽冷气之声。官职不高,算起来在七品之下;禁军都尉府……谁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风光归风光,却因涉及诸多秘事而极其严格,皇帝这是要……
转念一想,众人更是一凛:苏婕妤提的议?
一时间,众人摸不清头脑,竟就无人敢吭声了。除夕的宫宴乍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少顷,却是沈晔上前一揖,口吻冷冽:“陛下,禁军都尉府确是少了些有识之士,但禁军都尉府不养闲人!”
全不留情面,甚至可说是直言抗旨,皇帝面上一冷。沈晔自然清楚自己方才说了什么话,也大抵猜得到现在九阶之上的皇帝必定有所不快,却是没有退怯的意思——只觉如此下去必定不行,皇帝宠这苏氏太过。旁人兴许还觉不出什么,他禁军都尉府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替苏氏遮盖着那些大罪也还罢了,把她弟弟塞进来……日后还得出怎样的乱子?
苏妤沉吟着,看到皇帝面上那一缕若有似无的笑意时,却倏尔明白了皇帝的意思。视线飘向九阶之下,她定睛看了看一袭飞鱼服的沈晔,一声轻笑:“沈大人,谁说要你禁军都尉府养闲人了?”
这却不是她该说的话。
沈晔微有一凛,遂添了两分蔑意,清冷地还了一句:“朝中之事,何来女人干政?”
语声不大,却是无比清晰地传入各人耳中。苏妤睨了睨皇帝的神色,见他未有愠意,便又续道:“沈大人,苏澈不是‘闲人’,他是苏家人。”顿了一顿,苏妤颌首重重道,“有劳大人。”
泰半朝臣与内外命妇仍是云里雾里,却到底有人明白了。沈晔带着几分惊疑默了良久,终是一揖:“诺。”
苏澈抬头望了一望,未能看到长姐,倒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存着几分敬意地拱手:“长姐,我自会转告父亲。”
那晚的宫宴之后,是苏妤第一次和皇帝如此随意地在宫中散步。皇帝的意思,沈晔明白、苏澈明白,她也明白。
在外人眼里,把苏澈搁在禁军都尉府里,相当于人质。如果苏家再有什么异动,苏澈很可能死得不明不白——如若这是皇帝的意思,那么苏澈就是彻头彻尾的人质。
但……偏生是她提的。
皇帝是替她让她父亲明白了,即便她在宫中侍君,也断不希望苏家野心迭起。为了让苏家死心、让父亲不再望想,她可以亲手把弟弟交去做人质。
只为释君之疑。
她始终有意识地和皇帝隔着半步之遥,皇帝也就维持着这段距离不刻意靠近她。漫步许久,皇帝笑喟一句:“做得这么明白,你父亲若还不死心……”
苏妤轻哂,接了一句:“便怨不得陛下了。”
朝中斗争素来都有个成败输赢,皇帝肯一再提点已是给足了面子。如若父亲当真还要一条道走到黑……她也就委实再求不得什么。
黑暗中,有可怕的场景在她面前一闪而过。
她看到父亲死了,就吊死在家中正厅的房梁上……
弟弟也死了……是被腰斩于市!
淋漓的鲜血使她眼前一黑,失去重心般地栽了下去,折枝急忙一扶:“娘娘?”
“阿妤?”贺兰子珩微惊,也急忙搀住她。觉出她微微发着抖,借着宫灯暖黄色的光,他看出她的面色有些异样的白,“怎么了?”
苏妤下意识地撑着他的胳膊稳住身子,缓了缓神,却是摇头道:“没事,大概……喝多了。”
贺兰子珩眉头微挑,心道真是不会说谎,明明低酒未沾……
倒没有揭穿她,只命宫人抬了步辇来,送她去成舒殿。
那一晚,梦魇彻夜。从前的一幕幕再次浮现眼前,和并未发生过的种种连成一片。苏妤看到她的昏礼、他的无情,看到她在宫里备受冷落……甚至再度看到家人的死。
有些画面来得颇是奇怪,譬如折枝说:“过了今天就是建阳三年了,又是采择家人子的时候……”
那就该是建阳二年除夕说的话,就是今天。
可今天分明没有那话。
画面中的一切更是不对,她看到自己还置身霁颜宫中,凄清得紧,和先前的两年一样,却与今时今日大不相同。
即便是睡梦中,她还是一遍遍地告诉自己,那不过是场梦。
但即使在她醒来后,她也无法说服自己那只是一场梦。一切都太真实了,历历在目,甚至比今天真正发生的事还要让她印象深刻。就好像庄生梦蝶,让她辨不清哪一边是梦、哪一边是醒。
“折枝!”一声惊呼,苏妤惊坐起来。茫然地四下望着,心里是很久都没再有过的慌乱。
上一次有这样的慌乱……还是在佳瑜夫人入宫那天、她昏厥的时候。
可此时的她……几乎已想不起佳瑜夫人入宫的事,好像整个人都活在另一个世界中,满心都是她并不曾经历过的事。
仿佛不受控制地坠入了一段并不属于自己的记忆,越坠越深,逐渐打散她最后的清醒。让她再也无力提醒自己……那只是一场梦。
因睡不着在正殿批着奏折的贺兰子珩被寝殿传来的这一唤惊住,不觉间与徐幽相视一望,徐幽即刻揖道:“臣去看看。”
“不。”贺兰子珩放下手中的那本册子一叹,“朕自己去。”
入殿,就见苏妤蜷缩在榻上坐着,眼中毫无神采。两个宫女有着几分怯意地在旁劝着她也不理不睬。
皇帝挥手命二人退下,径自坐到了榻边,温言道:“怎么了?折枝现在大概歇下了,朕差人去叫一声?”
明明是温和的口气,却让她觉得字字锥心。一阵瑟索,苏妤张惶地抬起头,满眼疑惑不解:“陛下怎么在……”
皇帝一怔,遂笑而解释道:“朕方才睡不着,去正殿看了看折子……你不舒服?”
看折子?苏妤头中发懵,迷惑地环视四周之后,似是有几分不可置信般地道:“这是……成舒殿?”
皇帝被她飘忽的口气弄得浑身一悚,定睛看了她须臾才确信她确实问了那句话,点头应道:“是……你怎么了?”
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苏妤一阵头痛,只依稀记得自己睡了一阵子,一直在做梦,一个又一个的梦。但再往前发生了什么……她似乎记不得了?
“陛下?”她惶惑地望着眼前的帝王,带着犹豫地问说,“是陛下传臣妾来的?”
“……是。”皇帝眉头紧蹙,全然不知她这是怎么了。虽是在途中有过不适,但回到成舒殿时她已无碍,气色也好了很多。他想传御医,是她自己拦了下来,说只是太累了,歇一歇便好。
怎么一觉醒来竟是……
“去传御医来。”皇帝发了话,候在外面的宫人立刻领命而去。苏妤怔了一怔,贝齿一下下在下唇上划着,心中竭力地回忆自己是不是又怎么惹他不快了。
却是想不起来。她身子蜷得更紧了,好像缩起来就可以避开一切人和事、可以逃开父亲与弟弟的死,她的下巴死死抵在膝上,颤抖着说:“陛下……别杀他们……”
“什么?”皇帝愣住,看着她的惊慌失措,他更加无措,“阿妤?”犹豫须臾,他试着伸出了手,抚上她的额头。
她好像是碰了什么碰不得的东西一般蓦地一躲,慌乱中不知是怎样的一闪念,竟同时伸手一挡,继而便未经思索地咬了下去……
“陛……”徐幽大惊,刚要上前却被皇帝抬手示意止步。
贺兰子珩看着狠狠咬在自己手背上的她,一边惊惧于她今日是怎么了、一边却又躲也没躲。她很久都没松开,反倒越来越用力。但看着她眸中的空洞,贺兰子珩隐隐觉得……似乎一切都是无意识的?
究竟怎么了……
从醒来的那一刻,苏妤就觉得心中空落落的,好像四周也都空落落的。平日里她喜欢盖着厚厚的被子睡觉,觉得那样才能添一份安全让她安稳入睡。但成舒殿里炉火很旺,虽是严冬也半点不冷,并没有备那样厚的被子……
她只觉毫无所依,心底越来越慌、越来越乱,只有对眼前之人无尽的恐惧。一口咬下去间,好像所有的恐惧都随着口中的使力舒了出去,是以她浑然未觉间越咬越深。
直到一阵腥甜在口中弥漫开来,苏妤心中清明半分,接着察觉出了周遭淡淡的龙涎香与檀木香混合的味道。
她干了什么……
“阿妤?”一声带着些许尝试意味的轻唤彻底扯回了她的神思,口中一松,初一抬头却被猛地撞入一个怀里。那阵温暖中,两段截然不同的记忆在她的脑海中撕咬着,她有些发懵地听到他问,“你怎么了?御医一会儿就来……”
紧紧地被他搂着,她在他怀里一壁发着抖一壁死命摇头:“陛下……臣妾不是有意的……”
“……什么?”他愣了一瞬,看到手上那两排血印时才反应过来,“哦……手……没事,你别在意。”
他一边几近刻意地故作轻松,一边无论她在他怀里怎么挣他就是不放手。过了好一阵子,苏妤才终于平静了些许。贺兰子珩低头看了看她,掩饰着心底的几分惊疑,一声低笑说:“晚上没吃饱?要宵夜不要?”
“陛下恕罪……”醒过神来的苏妤,只觉得片刻前的自己必定是疯了。终于从他怀中脱出来,怔怔地望了一望他手上仍留着血的伤口。没来得及再说话,他便随意地将手一垂,宽大的衣袖覆在手上掩住伤口,全不在意地将她再度揽了过来,笑言一句:“先别睡了,朕陪你待会儿,等着御医来。”
苏妤身子发僵,木然地倚在他肩上,余惊未消。方才的她想不起先前发生了什么,现下清醒过来的她却清醒地记得方才发生了什么。
她那么失态、那么失常,看上去一定就像……疯了一样。却又觉得好累,累得连担心自己前路的力气都没有。
只短短片刻,贺兰子珩觉得肩上的她气息不复杂乱。试探着动了一动,果然毫无反应。
……还是睡着了?
他想了一想,没有打扰。如是需要,等御医来了再叫她也不迟。
伸出手看了看,虎口处两排牙印都渗着血,真是咬得够狠。一阵阵火辣辣的疼,凝视了须臾,忽地沁出一笑。
若方才这一切都是毫无意识的……
他侧首看了看倚在肩头的她:阿妤,你怨我怨到食肉饮血方解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