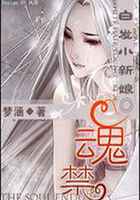假犯人高声喊道:“犯人只以直言叫阍,无甚大罪。又是朝廷大夫,那里轻加重刑!宪官不知重朝廷之礼么?”今也假犯人所供所说,尽是胡古绥所教的。胡刑部乃佯作大怒,喝道:“胡说!有圣旨究核,狠加拷掠,那里敢言大夫不大夫,亟加夹起来!”早有左右衙役一声答应,恶狠狠提起夹棍,将假学初夹起。可怜假学初痛楚得死去活来。孔目复命喷水回。只是那死囚,积年贝戎,惯尝铜棍滋味,复得白白地厚赂,只为忍痛叫声:“屈死我也,痛杀我也。”胡刑部更不拷掠,自言自语道:“认是公言,只将犯人所供应旨罢。”此时,郑司徒家人,魏国公心腹伏侍之人,各来宪衙门外探听,从外窥见,恶夹犯人图赖,莫不吐舌气忿忿。听处街上三三两两行人,一人道:“事关钦案,非同小可,但不能审得的。”一人道:“既然开了衙门审核,如何不使众人看过?”听听的一人道:“宪庭严威,那容闲人喧集的?”这一人复道:“并与衙役皂隶,如是远远排立,又是何意?”那一人又道:“如今之世,那有应旨不应旨的?”如此言言谈谈,过去了。
两府家人听了,知有话中有机,即使一人走还,将途上问答之言飞告英阳公主。公主大怒,暗暗使一太监率领多小宫奴府隶,待犯人审勘画供,还下天牢时,在街上等候,一时拿到府中,审知动刑不动刑,真个拶夹,然后还下牢里。
话分两头。胡刑部只将假学初口供,糊胡涂涂,妆成供案,上复请裁。喝令左右,解了犯人缚束,依旧套上脑箍、匣牀、铁锁,还下天牢。衙役们一时动手动脚,将假犯人箍了脑,锁了铁索,拽出宪庭门外,走到街上。
忽有太监一员,率领许多端公属员,如虎似狼的,一齐动手,套拿假犯人,飞也似去。刑部衙役,那里听敌当得起,只言:“刑部犯囚人,法不当如此,冒法私套。”那宫隶属员,那里肯听,只为不答走去。刑部刽子们,只自还告胡刑部:“犯人下牢,中间驸马宫中送太监属员,套拿去了,道是贵主娘娘旨意的。”胡伯远听的大惊,唬得三魂失二,七魂剩一,口呆不出一言。古绥在傍,告道:“叔叔无虑。这是夫人之事,不过是审认犯人动刑不动刑。彼今夹棍,皮开肉绽,血淋淋的,那里想得真假?但知其重刑,还送天牢。今夜叔叔使严侍郎缚束脚膝,外涂狗马之血,假作蹒跚匍匐之状,暗暗送了天牢,以待皇旨发落,谁人知道些儿呢?”伯远听了,道:“你说的是了。”虽然如此说,又不免怀着鬼胎。
且不说胡伯远还家。且说英阳公主闻说太监拿到犯人,满身腥血,移不得脚步,匍匐膝行,满面垂泪痛楚之状,随令太监押送牢里。贾孺人问道:“太监平日也知严学初那厮之面庞么?”太监躬身道:“小的昨年入宫任差,严侍郎囚在天牢多年,平日不曾见过。但闻皂隶们俱说老严了。”春娘道:“这厮们之说,那里明白。娘娘且待丞相亲见一见,可以的知呢。”说犹未了,丞相入内,问太太午安毕,春娘问道:“老爷曾识严学初面目么?”丞相笑道:“那厮阴鄙谄卑,我虽不曾同席,一般朝廷,宁可不知其面?”英阳公主道:“今严有可疑,拿在门前,丞相一审真假罢。”丞相笑道:“天下虽多假称假做的,宁以犯人应旨动刑拶夹,有谁假做代受苦楚的?但老严不知怎么的献供?那刑部又是奸徒,必然护党了。”英阳道:“虽然无假犯代刑的,丞相试看他何样罢。”丞相道:“这非难事,我且看他贼脑贼头,怎的生的如是鄙悖了。”即出外堂,遂令皂隶拿到犯人。一言才发,堂下一齐答应,如鹰搏兔的,拿跪庭下。丞相熟视道:“果然是老严贼头了,何须问他?拿还牢里罢。”众手未及动手,犯人叫声道:“青天知我无罪。我虽囚在牢里,便是朝廷大夫,丞相那可私拿问招呢!”丞相一闻其声音,大惊大骇,心内想道:“我虽不与他接语,曾于午门外候朝时,看他老严在张修河面前,聒聒噪噪,言三语四,心甚鄙之。听他音声,还是声嘶,又是齿落,语多声虚。今他语音不嘶不虚,况三年牢里,倒也还少。这是作怪。”遂故意问道:“犯人曾识我否?”假学初想道:“丞相屡建大功,严侍郎必当双贺。他既屡叩相府,丞相必当一来谢答。”想毕,高声道:“我那里不识丞相?我屡进相府,候拜丞相。丞相又一番屈谢荜庐。我怎么不知丞相?”丞相大笑道:“我何尝过你之门?你又何时来我府中?我且问你:你曾豁了齿,声又嘶,你今齿豁么?”假学初道:“我不曾落牙齿了。”丞相道:“你家在那里?”假学初虽被胡古绥教他口供、问答之话,一夜仓卒之间,何曾说老严家居胡衕,无辞抑说,便闭目作垂死样,道:“我在牢里久,今又受刑重伤,精神昏瞀,不省外事了。”丞相知是假学初,怒道:“你是假学初!你是何人?敢冒犯人,何苦来被刑苦楚,必有来历,勿讳实告罢。”假犯人道:“我便礼部侍郎严学初,那里是假犯冒称?”丞相大怒道:“这般光棍,如不动刑,那肯直招?庭下的,一发拶夹罢。”左右齐声答应,一时动手夹起来。
那假严学初登时昏绝。丞相命取水喷起来。众多衙役取水喷他,便作落汤鸡一般,旋复苏来,高叫道:“我是朝廷大夫,丞相虽尊贵,也非刑部宪慈,又无应旨,如何私自施刑?”丞相喝道:“好个泼皮!你是那里来的匪棍花子歪货,敢生撒赖!庭下们,另拶取服罢。”皂隶一倍拶接几次,假学初虽然愤吃夹棍,一般是骨肉,先又已多伤损于刑部,那里忍得住皮开肉绽上加了恶刑?便叫:“宽松我暂时,我且供真的。”丞相命少息接。假犯人道:“我是礼部侍郎严学初。当初疏语,犹可不是,今我又供怎的?”丞相冷笑起来:“这厮善吃夹的,只边益加拶罢。”左右又动手夹起来,不暂歇息。
假学初那里忍耐,登时死去活来。半日,声在喉间道:“我今死了,白顾了他不得。”丞相道:“这犯说甚么?”假犯人再叫道:“我非严侍郎。昨夜胡刑部使他侄儿,如此这般。那严侍郎,胡刑部安安稳稳的藏在刑部老爷家里。小人貌似严侍郎,受厚赂,代受拷夹,今至死境,不得另讳了。”丞相大骇道:“你果甚么人?”假犯道:“小人便是响马牛二的,囚在天牢待死。总是刑部爷之吩咐呢。”丞相便命拿出,囚在牢中,转入内堂,备说假学初受赂代刑之事。
英阳大怒,登时命鸾轿,入侍太后娘娘请安。太后答罢,道:“女儿有甚不平?气也好不舒服。”英阳大哭,呜咽不能对。太后摸不着,问道:“女儿有甚委屈,这般苦恼?”英阳遂将胡伯远究核假学初,拷问之事,一五一十,告了一遍。太后大怒,拍案道:“不杀这贼臣,如何出我与女儿口气!待万岁入来,当有发落。”说未了,皇爷入于内殿,见英阳,问了道:“御妹何时入内?刚才刑部官复上贼臣严学初之审供,游辞妆撰,抵头不服。明日当更亲问得情,以快妹妹心罢。”太后推破玉如意,大声道:“不杀贼臣胡伯远,何以明英阳之心!”天子惶惧,奏道:“刑部官虽然不得奸情,犯人抵赖,罪不在于刑部官。”太后冷笑道:“昏君。”随将假学初讯夹供招之事说道:“胡伯远可是不杀的?”天子大怒大骇道:“有这般奸党之欺蔽,不可迟待明日。假犯人今在哪里?”英阳道:“方拘留在驸马第呢?”龙颜大怒,即出外殿,登临震怒,登时诏会文武官员。此时朝廷震惧,不知事体如何,莫不战栗骇奔。天子即命左柱国张君正、御史大夫狄弼琦按治。又命拿下了刑部尚书胡伯远,缚紧,拶夹起来,问那严学初贼犯藏在那里。
伯远魂飞天外,强饰招奏道:“严学初囚在天牢三年,臣承诏旨,刚才拷掠审究,还下狱里,驸马杨少游夺拿私第去了,非臣之罪。拿下杨少游招问,知臣不诬了。”天子大怒道:“奸党饰辞图赖,如见肺腑。”即命夏太监往丞相第,拿到假犯人。又命兵马团练使吴成团住胡伯远家,搜捉严学初以来。两人分头出捕。
先说夏太监,飞到驸马第,问那假犯所在。宫里太监、端公们,一时动手,将假犯出来。夏太监看来,惊道:“这是严侍郎,如何说假的?不论真犯人、假犯人,承命拿去罢。”不满一顿饭时,拿到庭下,禀告天子。龙颜熟视道:“严学初搜来那里藏?”太监奏道:“奴卑承命,往驸马宫中,拿来假犯人的。”天子倒甚骇然。
狄弼琦先问假犯人:“尔是甚么人,敢冒犯人之名?”假犯不敢隐瞒,俯首供道:“小的是牛二的,积年响马,囚在天牢。前夜,胡刑部的侄儿相公,来到牢中,给白银二百两,谓小的假做严侍郎,如此这般。小的只依其侄子所教,死罪,死罪。”此时,胡伯远见了拿到假犯人,听着他所供,分明一个霹雳当头打下来,只恨没有地缝儿,不能一时钻去了。天子听那假犯招出胡伯远侄子,亟令一同拿质。
再说吴成承旨,调发五城兵马五百,团团围住胡伯远第宅,水泄不通。彻内彻外,搜来搜去,引了家丁,一一盘问。索到内堂套间小书房里,严学初正与胡古绥讲说假做拷掠状,登时见了许多军健,搜到捉拿,便与胡古绥一同捆如攒马四蹄一般,至于殿庭下边回禀天子。
天子看他严学初越发忿怒,即命先将古绥拶夹究核。古绥那里忍得?终将昨夜张修河暗赂金银,为严学初百般调全,初不动刑,只凭口供胡涂应旨之事,一一确招。
天子大怒,即命一齐夹棍起来。金吾拶夹,非同小可。胡伯远胫骨尽碎,严学初昏绝复苏,知不得讳,遂将当初张修河自制弹文,构陷郑鄤、杨少游,使他论核呈上之事,胡古绥夜到天牢,解释脑箍,暗出天牢,藏躲胡伯远之内堂,复将死囚中貌类替为刑楚,教他图赖,鬼鬼祟祟,糊胡涂涂,上复之由,一长一短,直供招来。
天子又怒又骇,开言道:“奸党欺君误国,恶贯满盈,天不可终欺。”即令监刑官推出严学初、胡伯远、胡古绥三个贼臣,腰斩于东曹市。籍其家产,小大家眷尽为诛戮,凡四百八十二人。下张修河于天牢,以待诏旨。
罢朝,还内,便将三奸诛殛之事,一一告诉太后娘娘,又待英阳贺喜。太后、公主俱为大喜。
此时一国之人,莫不快活,朝着清明。
未知张修河在天牢狱中,如何发落?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