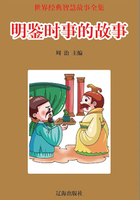越琮领命退开,张放旋又转身朝怀嘉下令道:“怀将军,我命汝行镇军将军事,即刻督率京四营,协助越大人守城。再晓谕冯迟,命据武库,戒备非常,以免城中奸细作乱!令狐大人,包围宫城后,你与老夫速去拜见甄太后,陈说利害,此次定不能放过那李即老贼。”
众人诺诺称是,心下无不凛然。
张放下令以后,神情顿时变得疲惫不堪,乃仰天叹道:“老夫寻此下策,实非得已,不过张某问心无愧,亦对得起先王在天之灵!我但在位一日,定要辅佐明主,振我大业,勿令小人当道,而致祖庙蒙羞!”
池阳。
卫将军营。
卫将军臧虎乃仪比三公的四将军之一,全权负责南境军事。自霸王敬被武哀帝大败龙鳍以来,臧虎接替许原担任此职,一晃便是十五年。此间,他数次随同张放、越琮南征,是霸国老将中杰出代表,尤其是吴历三百三十五年越琮伐前师失利,霸军被敌将孙杞击败,臧虎独以池阳营少部甲士,力阻追师三日夜,保证了大军安全撤离。此役臧虎负大伤二十处,手下仅余甲士百名。归国后,骠骑大将军越琮亲临臧府,亲为理药问疾,传为佳话。
臧虎谋深识远,曾就师于天焦著名兵法家魏悝。魏悝与同国毛白、伏氏国平德远、北雁国崔营并称为“吴四贤”,虽则魏氏已丧,却在诸国中仍享有极高声誉。
魏悝在世时择徒极严,座下弟子方只百人,常被戏称“毛白十一”,即嘲弄他的弟子数连毛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天焦著将项冀、段煨皆出门下,尤其是项冀等封拜上将之后,仍常赴“魏庐”拜谒师尊,令海内称羡。
臧虎轻不议政,因而屡被李党忽略。暗地里,自李氏上台后,他却是牢牢握住池阳营军权,裨将以上均不提拔朝廷选派之人,因而其营亦被诸将军暗地称为“臧家营”。除此之外,臧虎还通过旧属、门生的关系,对霸国各军事指挥权变动了如指掌,并在张放被黜前推荐其子臧容任北宫卫士令职,手握北宫禁卫甲士三千人。这一切,都为他十余年稳掌帅印,提供了条件。
未王与大将军李即来到池阳,臧虎恭敬接待,调集了精锐甲士五千人,组成军团,操练于池阳校场。此举令未王大悦,即増其邑百户,又赐名剑一把,大加关宠。李即亦暗地里撒下大把银两,心中早把这“赳赳武夫”当作了他李氏门阀中的心腹爱将。
实际上,张放、越琮被黜的消息,足使得臧虎三日未能安寝。震惊之下,不由得也为自己的前途与一干老臣性命担忧起来。他年近六旬,与张放私交二十年,与越琮更是儿女亲家,怎会不知他们的为人?他自然知道,张、越等下野后不与往来,实则是在保护自己。可叹李老贼不识大体,一力邀媚于上,抢窃权柄,鼠目寸光,又怎能令人归心?
如今,李氏亲属、门下把持内外,不可一世,而张放年七旬,越琮过半百,都非壮时,这场龙争虎斗,到底孰胜孰败呢?
此时的臧虎,凭借着多年的经验,意识到定有变故发生,从未王南巡开始,他便搬入池阳营大帐居住,传令三军戒备,不得随意出入,一切都按战时状态部署。
八月辛丑日,未王南巡结束,准备回京,臧虎考虑再三,决定不出席饮宴,只派遣精壮甲士八十人持斧钺前往,“以壮行色”。
中军主帐。
参校来报道:“禀将军,营外有数骑前来,声称将军旧属,要求入见!”
臧虎眯起眼睛,思考了足足半盏茶的功夫,这才微微颔首道:“传令:大帐四周,备好五十名刀斧手,不得老夫命令,有敢出帐者,斩!”
参校高声道:“得令!”趋步退下,稍顷,两排弯刀甲士于帐中、帐外列队,如临大敌。
臧虎强自镇静地看着大帐外逐渐走近的三人,心中着实有些忐忑。如果是大王真的对自己不放心,只须都护营与池阳郡合兵,就管保“臧家营”得拼上老底,但这当儿,自己也只能放手一搏,与赵矛一拼性命了!
三人中一人以笠遮面,身后二子,亦垂头披发,似乎是怕被人见到了真面目。
臧虎冷声道:“站住!汝等何人,为何冒充本将旧属?”
戴斗笠者微微一笑,轻声道:“臧大人,烦请摒退左右,我们慢慢说话不迟!”
臧虎方待大怒,却又是吃了一惊。怔了半晌,又复急急挥手将甲士遣退,叫道:“任何人不得近我大帐三十步内,违令者斩!”
甲士们虽奇怪于主将言语反复,却仍是令行禁止,潮水般退出,未见丝毫紊乱。臧虎待众人离去,这才起身,急步来到说话者跟前,火急火燎地抬起那人笠沿,怪叫一声道:“越兄,果真是你!”
来人大笑,却正是被黜的原霸国大司马越琮!
身后二人也跟着大笑,各自抬起头来,乃是越琮子豹、臧虎子祥。
越豹官拜奉义校尉,随父免职。臧祥却是臧虎小子,一直随越琮在军中历练,琮免职前,将其调至他郡,这才没有连坐免官,如今已被趾郡太守辟为武勇从事。
臧虎又惊又喜,随即脸上色变道:“张大人决定举事了?”
越琮知其深通军略,识见过人,但见他竟能预料到政变发生,也不禁暗暗佩服,知瞒他不得,敛容点了点头。
臧虎叹息道:“如此,老弟怎还敢冒险来此?须知大王与大将军尚在城中!”
越琮见臧虎仍是心向己方,不禁将担忧抛之云外,大笑道:“有兄长这一句话,越琮死而无憾!不过张大人何等英杰,又岂会不识李即之计?他这招以退为进,实是精湛无比,如今京畿、四郡都握在太尉手中,老夫这才敢涉足池阳营卫将军臧虎大人的中军帐呢,哈哈,哈哈!”
臧虎吃惊地道:“京畿四营,加上左右羽林、羽林都骑军,不都是李即的人吗?此事决难易与,越兄不要骗我。”连连摆手。
臧祥见越琮愈发大笑,忙向臧虎解释道:“父亲望安,越大人所言无虚。李即插手京畿军务,早为诸将军不满,京四营怀嘉、冯迟,皆越大人旧属也,今已会同四营甲士,效忠太尉。左中郎将迟湛代行大将军事,据羽林都骑营,单欣与之旧好,更无他言。如是便只有左右羽林驻在城中,张大人以太后名义,羁押左右监,改由曹珍、李抗分掌,而京师百姓向对李党深恶痛疾,太尉复职,那还不都欢欣鼓舞着么?”
臧虎眉头大舒,露出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越豹见状接口道:“今日我们此来,便是请臧公随张大人举旗讨贼。他日立功受赏……”
越琮眉头一皱,喝道:“放肆!汝怎敢对尊长妄言,你叔为我朝立下赫赫军功,岂是你这小子能随口与夺?再说此番内乱,实是朝廷不幸,我等为国讨贼,谈何功勋!还不快快向大叔请罪!”
越豹吃了一惊,跪倒磕头。臧虎连忙搀起,朝越琮笑道:“看来老夫不接令都不行啊!贤弟这一番话,哈哈,说得淋漓尽致,真是痛快、痛快!如此,老夫纵受天谴,亦甘愿为太尉、越兄听命驱策!”
越琮大喜,与之双手紧握道:“如此甚好。张大人有令,请臧兄密遣池阳营部,三日内赶到前波谷!我等将于此地伏击李即,包围大王车驾。小豹素善追击,便留在臧兄帐前听用,小祥还随我回京师,臧兄以为可否?”
臧虎见越琮如此试探,知是表示忠心的时候,奋然拍胸道:“请张大人、越兄放心!既有定策,某还怕他谁来?某池阳营中,皆勇壮之士,必定不亚那都护营半分!”
前波谷。
七日后。
大将军司马白尧派往京畿的哨马都不见回报,心知有异,急急禀报主上。
李即正与其弟中书令李斡,其婿黄门侍郎左乐等在车帐中饮宴,推杯换盏,狎玩女婢,不一而足。
白尧策骑来到车旁,报道:“禀大将军:京畿三司九台、各营都不见接驾,哨马北遣者亦不见归。末将以为事有蹊跷,此时不宜轻进前波谷,应待奏明大王后,请旨再行!”
帘布一动,李即怏怏地探出脸来,皱眉道:“竟有这事?十日前我便传旨澧阳,大王回京,他们怎能不派人接驾?这些个胆大包天的鼠辈,非拿来严办不可!”
李斡忙道:“大哥先勿动怒,莫非是老贼处有变……”
白尧松了一口气,插口道:“末将亦以为如此,请大将军从速讨旨,以都护营急进京郊,察明情况,以策万全。”
李即怒道:“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退下!”
白尧色变,纵骑而退。李即这才烦躁地挥了挥手道:“绝不可能!左右羽林、羽林都骑、城门校尉、京四营,都在我控制之中,若张贼造反,手无寸柄、亦无军权,何以成事?这必定是有人从中造谣,让我们自生疑窦。再说,如今有大王在此,谁敢乱来?”
李斡心下一放,却仍规劝道:“大哥切勿轻敌。张贼在朝中颇有威信,门生客卿无数,若他果真阴结死士造反,京师诸营被胁从入伙,还是极有可能的。”
左乐咬牙切齿地道:“当初便该杀了那几个老匹夫!”
李即思忖半晌,突地哈哈大笑,道:“我有大王依恃,都护、池阳营与各郡人马都在,如他果真叛乱,还正合了我的心意!此刻不过庸人自扰,到了京师,你们便知我所言不虚。”
李斡还待再谏,李即摆摆手,不以为然地道:“你们太过小心了。我李氏如今光宗耀祖,朝廷内外,皆我亲眷、手下,扫平区区琮、放之辈,易如反掌!更何况我军权在握,只须大王下旨,便可动用十数二十万人马,那时对张贼雷霆一击,管叫他皮毛不存!”
傲然地命令继续起程,天黑出谷,明日黄昏前须至王城。
申时。
都护营中军。
斥侯快骑急报,甚至不及下马,“禀报将军,前方谷口为乱石所塞,车马不得通过!”
奋威将军赵矛接报,顿知不好。适才劝说大将军未果,他便令前后军分开入谷,待前军通过,后军再入,这下明知中计,却亦被困于谷中,前后无序,无法与后军王驾联络。情急之间,持枪跃马,高叫道:“诸军士,速速返出谷外,保护大王车驾!”
后队未闻喊声的,仍在前行。当下赵矛身边亲将便吹响号角,大军霍地返身,有条不紊地往后退去,虽情况紧急,军容却丝毫不乱。
然而,猛可间两侧谷上人头躜动,谷口隆隆作响,夹杂着呼喝、惨叫之声,一听便知都护营甲士吃了大亏。赵矛心下发寒,仍强自冷静,叫道:“甘平,速领人马寻路,掩护前军撤退!”
有人高声称是,领军往回杀去,赵矛又命自队分散开来,前锋加快步伐往谷口冲锋,探看究竟。
此时前波谷口尘烟漫天,无数巨石从侧旁滚下,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企图强行通过的都护营一部,都呆瞪着眼睛不知所措,没人再敢往前半步,连赵矛亦无可奈何。
此际都护营谷外的后队,也发现敌军合围的迹象,副将凌代忙而不乱,指挥士卒紧缩成圈阵,稳屯待援。慌了手脚的李即不停地发出胡乱指令,自然无人理睬。
从三路逼来的卫将军池阳营、羽林都骑军和骠骑将军繁城营人马呈合围之势,浩浩荡荡,将都护营并王驾围于谷前。
未王冲惊慌失措,在车上声嘶力竭地嚷道:“是何人敢阻本王?你们都造反了么!”
近臣急得垂泪道:“大王,恐怕是前师的兵马,这下子完了!”
未王惊得浑身发抖,紧紧搂住身旁美姬,喃喃自语道:“快来勤王护驾,快来勤王护驾——凌将军……”
偏将军凌代神情冷静,在马上抱拳道:“臣在!大王,我看这些都是本朝军马,不象是前师遣来的追兵。”
未王冲闻得此言,顿觉腰杆子又硬了些,朝车旁的李即道:“大、大将军,你去问问这些人,为何要阻本王归路?他们……他们难道都要造反不成?”
李即早紧张得话都讲不出来,结结巴巴地答道:“是、是是那该、该死的张放,他串通京畿上五军造反,谋弑君王。大王,您、您可要为臣下作主啊!”
未王冲被李即前言不搭后语的恳求弄得神色阴晴不定,强作镇定道:“凌将军,速派人去讲和。若真是张放,那他们要什么,本王就给什么,千万不要惹恼了他们!”
凌代暗自叹了口气,领命退开。不一会儿,都护营军校在阵前高叫道:“来者何人?可是勤王之师?”
左路羽林都骑军遣出一将,手捧黄绢诏书,驰至六十步开外,高叫道:“奉甄太后之命,捉拿反贼李即!其余一概不问!”
凌代大怒道:“呔!难道汝等不知我王御驾在此?竟敢口出狂言!若汝等为恶作乱,休怪我凌某手中大刀无情!”
语声震天,然三路兵马纹丝不动。那将军哈哈大笑,展开诏书道:“正有太后懿旨在此!‘罪子赵冲听旨:霸王赵冲,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太尉张放领策,以一元大武告于宗庙,遣冲归藩于郃,以避王位——’”
高喝一声,“来人,请醴王冲并拘拿罪臣李即!”
羽林都骑军两队长枪甲士缓缓开出,都护营士卒皆惊疑不定,不知该做什么。凌代心道不好,叫道:“站住!不得靠前,否则我便要传令放箭了!”
那将军大怒,举起手中黄绢册书道:“太后诏旨在此,谁敢违抗?凌代,汝若以都护营为恃,对抗朝廷,必会以不臣之罪伏诛,讨灭九族!”
凌代微微一震,右手握紧大刀,杆身竟至微微抖动,可见其忧愤之烈。未王冲闻得太后懿旨,早已象鼻涕虫一般软瘫在地,兀自喃喃低呼:“本王是霸国君主,你们无权废我,你们无权废我……”
李即更是不住地抖颤,象溺水者胡乱握住一根救命稻草般,朝凌代祈求:“凌将军,王公大臣和大王的性命,在乎将军一人身上。将军万万不能将大王交在叛贼手里啊,那……那张贼矫诏废王,大逆不道,将军可不能轻信了他们哪!”
凌代咬牙出血,忽地举刀大喝:“放箭!”
都护营甲士皆都身经百战,闻得将令,前排擎盾,后排张弓,嗖嗖射出,一时对面开来的长枪甲士乱了阵脚,惨声迭起,顿时倒下大片。羽林都骑军齐声怒号,以枪格荡,退出二十丈开外。
对面那将军拔剑劈掉几簇箭矢,高叫道:“凌代抗旨违命,罪大恶极!诸军愿降者免死,不降者杀无赦!”
凌代见身边军士面带疑容,大喝道:“废话少说!你要都护营归降,先得赢我手上大刀!”
对面那将冷笑连连,并不答话。对峙少顷,只听鼓号齐鸣,池阳营军卒持旗号分开二路,当先涌出两排将领。为首一人,须发皆白,却正是卫将军臧虎!
都护营甲士无不震憾!
凌代勒紧马缰,也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原来对方果真掌握了大部戍军,这才能唤出象臧虎这般的重臣宿将。张太尉大权在握,硬抗下去,谁都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李即目瞪口呆,李斡亦脸色苍白,一拉其兄袍袖,道:“大哥,兵败如山倒。为今之计,只有突围出去,往封州借兵击贼,才是生路。”
李即犹豫道:“三面合围,怎样能突出去?唉,二弟啊二弟,我真后悔没听你劝,落到这样的下场。”
李斡道:“这些话休再说了。待凌将军与贼厮杀之时,我们便向东突出。白尧,你带兵西向,掩护大王、将军。我等性命,就交在你的手上了。”
白尧微微一晒,仰天叹息道:“末将遵命!”
李即又复抬头,问道:“那凌将军……”
李斡面无表情地道:“大哥,军情紧急,谁也顾不得了。此番只要逃出命去,定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休再作妇人之仁!”
李即摇头痛悔不已。此际,凌代已鼓起十二分勇气,冲上前去,与臧虎硬拼,大将军司马白尧趁势一挥手,叫道:“众军都随我来,我们突出阵去!”
人喊马嘶,战鼓隆隆。都护营与未王戍卒数千人兵分两路,喊打喊杀地妄图冲杀出去……
(第二节
秋九月,霸国骑督偏将军文杰追斩李即、李斡兄弟于东城,即子辅国将军李遂、从兄城门校尉李豫等皆伏诛,诏灭三族。
未王冲举迁醴地为侯,李王后废号,逐入冷宫,两月后发病薨,无子,甄太后听政。
其月,以张放为太傅,总决政事,越琮为大将军。张放乃上表,恢复了楼太后、卫太后的尊号。
澧阳南郊宗庙。
九月甲子日。
松柏成林,苍苍莽莽,虽值深冬季节,仍有漫山怒绽之草菊,迎风飘摆。
祭坛外,霸国比二千石以上车驾密密匝匝,停满原野。坛坡土阶四周,皆有衣甲鲜明的卫士执戟于风中肃立,衣裾飘摆,形象严整、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