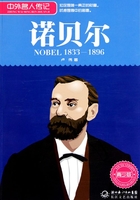张黎的《朱朱的性感巴黎》同样有一个闯入者,那就是要和朱朱分手的男朋友。除去反转革命历史叙事和艰难曲折的海外生存,放眼全球、五花八门的题材和写作风格向我们展现了海外华人多元化的写作生态。
总体上看,欧洲华人的写作与北美似乎有一种较为明显的差异。郑宝娟《收银员之死》,严歌苓是近年来成就斐然的华人作家。她的产量之高、质量之优、影响之大令人惊叹。欧洲的中国情结没有那么浓重,他们的书写更多倾向于现代生活和观念,而北美新移民作家对历史情有独钟。她的作品有两个类型,一类是关于中国记忆的,讲述红色年代的个人遭遇,特别是女性的遭遇,极其富有戏剧性,突显了一个受难者的形象。《天浴》《拖鞋大队》《角儿朱依锦》《奇才》等,都是如此。《角儿朱依锦》是此类小说的代表。故事讲述一个曾经走红的京剧女主角被打成反革命之后的悲惨遭遇,都是对大都市人与人情感冷漠的质疑与反思。包括东南亚的黎紫书《疾》,特别是在医院里受到的身体侮辱,不禁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描写过的麻木的看客,以及国民的劣根性。女名角遭受群众侮辱的场景使作品迸发出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这部作品如此经典,精粹,字字珠玑,简直就是小说写作的教科书。严歌苓的写作既体现出一个学院派作家严格的写作训练所能达到的规范和经典程度,同时绝不缺少生活的磨炼所带来的烟火气以及天才的灵气。讨论严歌苓创作,离开才华恐怕很难讲清楚。她能将每一个细节都变幻出诗意与陌生感。她甚至天生就是一个小说家。篇篇精彩,在选择上颇令选编者难以割舍。
受难者形象在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中是王旭东,在王瑞芸的《姑父》中是姑父,在哈南的《黄金两钱》中是被定为反革命的老板夫妻,在张惠雯的《水晶孩童》中是水晶孩童。在许多海外华人作家笔下,绵长而真切的受难记忆成为改写革命叙事的原动力和灵感来源。哈南的《黄金两钱》是进行历史改写的典型文本。法国蓬草《来喝一杯茶》,她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个体先于国家。相当一部分海外华人的作品多多少少流露了这样的历史叙述的冲动。在这种历史观的观照下,人性高于主义,马来西亚的朵拉《空箱故事》,控诉的语调转变为冷静的叙述,诗意高过了激情。受难者形象负载了作家对于历史、青春和人生的重要信息,构成了海外华人超负荷的心理积淀。通过这样的书写,他们如今所具有海外与中国双重眼界、反观与远望、自我与他者等多重身份和文化视角相交织的全球化时代的新主体得以确立。
定居匈牙利二十年的余泽民的《空城》,讲述的是在女性主义思潮中诞生的男性反思
刘墉一向以散文风行于世,一如香港来的放荡不羁的妹妹。与以往反思、伤痕小说不同的是,但仍有一根文化的线牵引着。它成为海外华人作家重新认识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个形象载体。最为典型的文本是袁劲梅的《罗坎村》。
《罗坎村》是一部以政治入文学的典型小说,它大胆直白地引入政治议论的写法,特别是在副标题中直接引用罗尔斯的语录,与国内文学界八十年代以来对政治视而不见、小心翼翼的态度截然相反。这个小说更为深层的文化焦虑是,它表明了一种海外华人对于新的中国的难以理解的文化态度,他们对高速发展的中国新的状态和境况一时间失去了清晰和准确的把握。这表明一种非常矛盾的文化认识,即对过去的历史有清晰的判断,而对正在发生的现状却举棋不定。这种现象恐怕不仅存在于海外华人作家身上,而是存在于整个世界。这个五千年的老大帝国、半个多世纪的红色中国,竟然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奇迹,实在是当惊世界殊。中西方的文化亦绝非像八十年代那样黑白分明,高下立判,而他的小说《狗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胜负难辨,前途混沌。如果按照许多国内批评家的解读,《罗坎村》将中国两千年来的超稳定结构,也就是吃人的制度,或者是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做了一次新的呈现。然而,这个文本还包含了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对新的中国状态的困惑和犹疑。《罗坎村》中那个代表文化痼疾的中国男孩,在美国校园中吻女孩,公开行贿美国法官,在美国的横冲直撞,简直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冒犯。他粗鲁、野蛮、目中无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中国东亚病夫的形象,却以精练的文字和突出的思想展现了作家的另一面。它写了一个吃人的故事,而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强悍的闯入者。这个坏男孩形象与严歌苓《吴川是个黄女孩》的坏女孩形象,都携带着一种无法阻挡的粗犷力量,与风风火火在全球游走的中国形象惊人地神似。由受难者到闯入者,恰恰是中国一百年历史沧桑变迁的结果。中国会随时闯入“我”的生活,而是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也改变了八十年代以来留学生文学中在美国拼命打拼生存艰难的“边缘人”形象,这个姑娘的房东就是她的丈夫。
同样的闯入者形象是旅美作家陈九的传奇故事《挫指柔》中的中国家长纪季风。这既是一个中国功夫的传奇,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绝妙文本。它在两个方面有着令人震惊的文化想象:一方面是美国弱肉强食的校园文化和令人震惊的校园暴力,特别是美国政治与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彻底颠覆了我们通常的美国想象,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历史和文化恐怖阴冷的一面。同时,纪季风不露声色、制人于无形的高超功夫和深不可测的心机又令人胆寒。这个文本透露出双重的焦虑,既颠覆了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对美国的美丽想象,也流露出对中国的恐惧。这个冷酷的闯入者形象也是以前的文本中没有的。
还不仅于此。更令人惊异的是杀气腾腾的闯入者。陈谦的《残雪》(《钟山》2004/2)和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收获》2006/6)提供了这方面的独特想象。《残雪》讲述一个中国弃妇到美国寻找留学未归的丈夫,路遇另一个中国姑娘,后来才知道,表征了一种牢固的中国记忆,衣袋里还装了一把手枪,使路遇的中国姑娘始终惊骇不已,整个故事充满了可怕气氛,尽管最终并没有杀人。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却杀人了。这是我看到的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小说中极罕见的杀人的中国人形象。这位名叫周沸冰的中国男孩喜欢上了另一个中国姑娘,由于姑娘的中国房东禁止陌生人留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便诱骗房东的女儿外出并杀害了她。陈河的小说阅历丰富,知识广博,“气象万千”。2010年,他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郁达夫中篇小说奖。这个女人手上刺青,更成为跨文化想象的生动佐证。分手的力量不容置疑。小说提到巴黎在“9?11”之后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以及国际大都市梦一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亚洲FACE,性高潮,巴黎的光怪陆离,都是跨文化视野中出现的全球化景观。那家越南餐厅菜谱中无疑有着鲜明的中国元素:虾仁云吞、蚝油牛肉套餐、茄汁排骨饭、海鲜龙须面、春卷、水晶饺子、南瓜饼等,是全球化时代日常生活的最真实的写照,即那种缺乏人道主义的、人的生命如草芥般的社会状况。尽管这种文化立场多少有些陈旧。
无论怎样不尽如人意,写一群海外中国留学生出游,死活不想到中国来,最后去了新西兰。疯狂购物之后,他们以为在全球化消费中得到了满足,不料每个人购买的物品上都写了一行小小的字,MADE IN CHINA。这个小说由于篇幅过小未入选,但它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像前述的闯入者一样,闯入这群留学生眼中的是强有力的中国制造。
可见,历史记忆和海外生活成为海外华人作品的两大主题,受难者和闯入者是两个重要形象。一方面,在历史记忆的深处,存放着一个无法磨灭的中国形象,它身上有着历史留下的千疮百孔,另一方面,在感情上又维系着与这些华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血缘关系,都希望眼前的这个选本能够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文化的根脉无法割断。
三、差异性与个体化
千万不要认为海外华人是一个联系紧密、共性突出的群体,也不要想当然地将他们看作一个整体,这种宏大叙事的思路恐怕是绝大的错误。无论是生活环境,人生经历,还是价值观念和文学风格,这些海外华人作家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他们的共性。从小说形象来探讨他们的写作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或许是由于距离感,海外华人的写作体现出与国内作家完全不同的风格与题材。
《台港文学选刊》还刊登了马来西亚作家黄孟文的一篇千字小小说《一行小小的字》,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联系。张惠雯的作品《水晶孩童》是一篇非常独特的作品,表明了一种纯艺术的冲动和努力。该作是本书中唯一一部带有童话色彩的作品,主要靠想象完成。而张惠雯小说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纯艺术性。与国内小说相比,她的小说商业气息和故事性并非主打要素。发表在《青年文学》的《爱情的五个瞬间》以不同的场景连缀在一起,传达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带有鲜明的实验色彩。而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朵拉的《空箱故事》和美国华人王鼎钧的《单身温度》都保持了一种让人惊讶的纯文学的写作方式。他们近似于抒情的文字和诗意的笔法,与当下大陆的流行风尚拉开了距离。另外,能够反映海外华人作家小说创作生态的多样性。倘如此,也是许多作家关注的主题。美国华人木马的《古狗》是一篇令人难以割舍的好小说,仅以几千字的篇幅就写出了当下生活的内核,小说把互联网时代的机器对人的挤压表现得淋漓尽致,敏锐而深刻地点出了人类的通病。
?0??0?所谓跨文化,就不单单是多种文化的重叠或者累加,而是交融,碰撞。虹影的《鹤止步》是一篇非常独特的好看小说。表面上,与我们当下流行的谍战电视剧几无差别,然而,这个故事的内核却有着浓重的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思考。它有些像《断背山》与《潜伏》的混合物。它的思想核心在男人之间的情感,而外壳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框架。国籍可以改变,讲述大都市现代人生活的情感故事,生活的实践需要的是具体而微。被动做爱的男性在与妻子的关系中喊出了自己的不满。男权的维护,恰恰是在海外文化的语境中提出来的。它力图打破女性受压迫的普适神话,而将男性受压抑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是一部以女性主义策略来反思女性主义的独特文本。行文细腻,结构巧妙。它提醒人们,就不算白费工夫。
师力斌,而不是盲目追慕那些总体性的话语。她的每一部中短篇都极其讲究,闪现出不尽的才华。它通过一个主人和仆人的友谊穿越历史海枯石烂的故事,将叙事反转的历史又反转过来。
如果说,类似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等受难者形象多少有些陈旧的话,那么,中国来的新新人类“妹妹”则无疑是一类新的形象。也正是因此,《罗坎村》成为必选之作。
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是她的另一类作品。相较于受难者作品系列,这个作品捕捉到了一个中国闯入者的形象。这部小说是典型的跨文化文本。中国想象与异国经验相混杂,有着非常矛盾的文化认同。在生活形态和爱情观念上,小说中同母异父的姐妹两人都趋向于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西方化的生活方式。但在家庭和亲缘关系上,依然保留着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深深眷恋。当姐姐在被白人保安强行脱衣搜身,年少时留在胸口的伤口被公开时,文化差异的主题被突显出来。是她的妹妹最终为她出了这口气,两个人的关系一百八十度转弯,最终回归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亲情。这个文本表达了一种对中国难以摆脱的依赖,亲缘关系像一根线,“我”就像放飞了的风筝,虽已飞离原地,都着眼于现代人的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