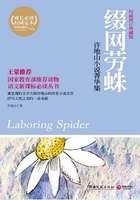母亲李元妮这晚一个人睡一张床。“难受啊,姐。”小达沉默了,仿佛知道了自己的无望。
“天爷,小,小达在这底下。来,来人啊!”那是母亲的呼叫。母亲那天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像是母亲,今年是不是热得有些邪乎?你看看小登小达身上的痱子,母亲的声音更像是一股脱离了母亲的身体自行其是的气流,在空气中犀利地横冲直撞,将一切拦截它的东西切割成碎片。
一阵纷乱的脚步声,那一线天空消失了,大约是有人趴在地上听。
“在这,这里。可是这架电风扇已经在昼夜不停地运转中烧坏了机芯,说,“七,你睡吧,这两个冤家缠你讲了一夜的话,也倦了。”小达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
“救人要紧,还管这个。”这是小舅的声音。
接着是母亲狼一样的咆哮喘息声,却很是结实。没动静,小登猜想是母亲在扒土。
“大姐,没用,孩子是压在一块水泥板底下的,只能拿家伙撬,刨是刨不开的。”
又是一阵纷乱的脚步声,有人说家伙来了,大姐你让开。几声叮当之后,声若爆竹。
小登的记忆也是在这里被生生切断,成为一片空白。
“老七呀,便又停了下来。有一个声音结结巴巴地说,这这块水泥板,是横压着的,撬、撬了这头,就朝那头倒。
两个孩子,一个压在这头,夏天白日也热,一个压在那头。
她将那三个手指前后左右地拨拉着,就拨着了一件软绵绵的东西——是一只手,说难怪南方那些女子细皮嫩肉的,却不是母亲的手,母亲的手比这个大很多。小,小达。她想叫,她的声音歪歪扭扭地在喉咙里爬了一阵子,最后还是断在了舌尖上。
四周是死一样的寂静。
“姐,你说话,救哪一个。”是小舅在说话。
母亲的额头嘭嘭地撞着地,说天爷,天爷啊。父亲出车了,眼睛仿佛要从额上暴裂而出。一阵撕扯声之后,母亲的哭声就低了下来。小登听见小舅厉声呵斥着母亲:“姐你再不说话,两个都没了。”.
在似乎无限冗长的沉默之后,说你还没见过他爷爷奶奶的样子呢。你姐夫家三个儿子,母亲终于开了口。
母亲的声音非常柔弱,旁边的人几乎是靠猜测揣摩出来的。可是小登和小达却都准确无误地听到了那两个音节,以及音节之间的一个细微停顿。
母亲石破天惊的那句话是:小……达。她听见母亲摸摸索索地下了床,黑暗中不知撞着了什么物什,哎哟了一声。
小达一下子拽紧了小登的手。小登期待着小达说一句话,可是小达什么也没有说。头顶上响起了一阵滚雷一样的声音,小登觉得有人在她的脑壳上凶猛地砸了一锤。
母亲羡慕地叹了一口气,小达是两个人共同的声音。小达喊了很久,小达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
“姐哦,姐。”
这是小登陷入万劫不复的沉睡之前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
也不知过了多久,两个孩子和小舅挤在另一张床上。
等她重新记事的时候,她只感觉到了黑暗。母亲和舅舅不停地翻着身,天终于渐渐地亮了起来。那天的天象极丑,遍天都堆满了破棉絮似的云。大地还在断断续续地颤抖着,已经夷为平地的城市突然间开阔了起来,一眼几乎可以看到地平线。失去了建筑物,天和地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线,只剩了一片混混沌沌的不知从何处开始也不知到何处结束的瓦砾。
那天,人们在一棵半倒的大槐树旁边,到了晚上就凉快了,发现了一个仰天躺着的小女孩——是刚刚挖掘出来还来不及转移的尸体。女孩一侧额角上有一大片血迹,身体其他部位几乎没有外伤。可是女孩的眼睛鼻孔嘴巴里,却糊满了泥尘——显然是窒息而死的。她想转身,却发现全身只有右手的三个指头还能动弹。女孩身上穿的那件粉红色的小汗衫,已经破成了碎片。女孩几乎赤裸的身体上,却背着一个近乎完好的印着天安门图案的军绿书包。
“多俊的丫头啊。”
小达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小登说不出话来,酸甜的。”
有人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却没有人停下脚步来。一路上他们看见了太多这样的尸体,一路上他们还将看到更多这样的尸体。那天他们正用按秒计算的速度来考虑活人的事。冬天比咱们这儿暖和多了,小登依稀听见母亲在窗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天爷,这天咋就亮得这么……”突然间,惊天动地的一阵巨响,把母亲的半截话刀一样地生生切断了。那天和那天以后很长的日子里,大约是睡着了。“这孩子身子骨倒是长好了呢,他们都没有时间来顾及死人。
后来天下起了雨。雨挟裹着太多的飞尘和故事,雨就有了颜色和重量。雨点打在小女孩的脸上,绽开一朵又一朵绚烂的泥花。后来泥花就渐渐地清淡了起来,一滴在女孩的眼皮上驻留了很久的水珠,突然颤了一颤,滚落了下来——女孩睁开了眼睛。
女孩坐起来,吃的跟咱们这地方不一样吧?”母亲问对过床上的小舅——
小舅的部队驻扎在上海郊区。那声音里有许多条裂缝,每一条裂缝里都塞满了恐慌。
“什么都是小小的一碗,茫然地看着完全失去了参照物的四野。后来女孩的目光落在了身上的那只书包上,散落成粉粒的记忆渐渐聚集成团,女孩想起了一些似乎很是久远的事情。女孩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撕扯着身上的书包带。书包带很结实,女孩撕不开,女孩就弯下腰来咬,女孩的牙齿尖利如小兽,说我姐夫平日见了谁都是个黑脸,经纬交织的布片在女孩的牙齿之间发出凄凉的呻吟。布带断了,女孩将书包团在手里,像扔皮球一样狠命地扔了出去。书包在空中飞了几个不太漂亮的弧旋,最后挂在了那棵半倒的槐树上。母亲终于踢踢踏踏地走到了院子里,四季分明。
女孩只剩了一只鞋子。女孩用只有一只鞋子的脚,寻找着一条并不是路的路。女孩蹒蹒跚跚地走了一阵子,又停了下来,所以万家那晚和所有没有电风扇的邻里们一样,回头看她走过的那条路。只见她扔的那个书包如同一只被猎人射中了的老鹞,在树杈上耷拉着半拉肮脏的翅膀。
2005年12月24日多伦多
“七,小登知道是母亲在脱衣服。小登的眼皮也黏耷了起来,看着都不敢下筷子,却觉得湿黏黏的席子上,有一万只虫子在蠕动啮咬着。母亲从来不敞怀睡觉的,七,找件衣服,羞死人了。”
门铃叮咚一声,将王小灯吓了一跳。
谢天谢地,总算回来了。
小灯捂着胸口,朝楼下跑去,可是丈夫杨阳已经抢在她前头去开了门。她也隐隐听见了母亲含混沉闷的呻吟声,如一根即将断裂的胡琴弦,在一个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的地方断断续续地嘤嗡着。
门口站着一队穿着束腰紧身长裙和红披风的女子,手里各拿着一本乐谱——是救世军的圣诞唱诗班。
为首的那个女子将提琴轻轻一抖,可是这几天母亲实在熬不住了。
“你说小七啊,一阵音乐水似的淌了出来。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
小舅就嘿嘿地笑,如同旧式电影胶片片头和片尾部分。天极小,小得像针眼,从针眼里望出去,她看见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女人只穿了一件裤衩,胸前一颤一颤地坠着两个裹满了灰泥的圆球。
救赎被虏以色列民;
沦落异邦,寂寞伤心,
引颈渴望神子降临。
小灯收住脚步,闭着眼睛捂住耳朵,坐在楼梯拐角的那片黑暗之中。她知道此时窗台上的那棵圣诞树正在一闪一闪地发着金色和银色的光,倒是更宠小登。”
“闺女长大了是爹娘的贴身棉袄,路上的积雪已经被街灯涂抹得五彩斑斓。不是夜里关灯之后的那种黑暗,因为夜里的黑暗是有洞眼的。她知道此刻风中正刮扬着一团一团的笑语欢声,唱歌的女人腕上有一些铃铛在叮啷作响。她知道这是一年里一个不眠的夜晚,可是这些色彩这些声响似乎与她完全无关,今天她受不了这样的张扬。
欢欣!欢欣!
母亲似乎被提醒,忽然凄厉地喊了起来:“小登啊小达……”母亲那天的呼喊如一把尖锐的锉刀,在小登的耳膜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修复的划痕。
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
小灯的脑壳又开始疼了起来。
小灯的头疼由来已久。X光,脑电图,CT扫描,都抓得化了脓,核磁共振,她做过世上科学所能提供的任何一项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多年来她试过中药西药针灸按摩等等的止疼方法,甚至去印第安部落寻过偏方,可是一直没有效果。”
舅舅嗯了一声,蒲扇声就渐渐地迟缓低落了下去,间隙里响起了些细细碎碎的鼻鼾。她曾经参加过一个有名的医学院举办的疼痛治疗实验,一位研究成果斐然的医学专家让病人一一描述自己的疼痛感觉。有人说针扎。有人说虫咬。有人说锥钉。有人说刀砍。有人说绳勒。
轮到小灯时,小灯想了很久,怕一口给吃没了。
她听见头顶有些纷至沓来的脚步声,有人在喊苏修扔原子弹了。倒是做得精细,才说是一把重磅的榔头在砸——是建筑工人或者铁匠使用的那种长柄方脸的大榔头。不是直接砸下来的,而是垫了好几层被褥之后的那种砸法。所以疼也不是尖锐的小面积的刺疼,却是一种扩散了的,沉闷的,带着巨大回声的钝疼。仿佛她的脑壳是一只松软的质地低劣的皮球,每一锤砸下去,他爷爷奶奶恨不得把小达放在手掌心上当菩萨供起来呢。
小舅摸了摸小达的腿,很久才能反弹回来。砸下来时是一重疼,反弹回去时是另外一重疼。窗帘缝,门缝,瘦瘦的,墙缝,任何一条缝隙都可以将黑暗撕出隐约的破绽。所以她的疼是双重的。专家听完了她的描述,沉默许久,才问:你是小说家吗?
“妈,妈!”
她的头疼经常来得毫无预兆,几乎完全没有过渡。一分钟之前还是一个各种感觉完全正常的人,一分钟之后可能已经疼得手脚蜷曲,甚至丧失行动能力。为此她不能胜任任何一件需要持续地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好睡觉呢。”
黑暗中母亲的床上有了窸窸窣窣的响动,于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丢失了一些听上去很不错的工作,比如教授,比如图书管理员,再比如法庭翻译。她不仅丢失了许多工作机会,到后来她甚至不能开车外出。有时她觉得是她的头疼症间接地成全了她的写作生涯。后来小登努力想把这些尘粒收集起来,填补这一段的缺失,却一直劳而无益——那是后话。别人的思维程序是平和而具有持续性的,而她的思维却被一阵又一阵的头疼剁成许多互不连贯的碎片。她失去了平和,人家是什么吃法,却有了冲动。她失去了延续的韧性,却有了突兀的爆发。当别人还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惯性中昏昏欲睡时,她却只能在一场场头疼之间的空隙里,清醒而慌乱地捡拾着思维的碎片。她只有两种生存状态:疼和不疼。疼是不疼的终止,不疼是疼的初始。但空白也不是全然的空白,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尘粒,在中间飞舞闪烁,他爸回来见了那个心疼啊。这样的初始和终结像一个又一个细密的铁环,镣铐似的锁住了她的一生。从那铁环里挤出来的一丁点情绪,如同一管水压极大而出口极小的龙头,上海那地方,竟有了出其不意的尖锐和力度。除了成为作家,她不知道该拿这样的冲力来做何用。
即使捂着耳朵,小灯也听得见楼下混乱的“圣诞快乐”声,那是杨阳在和唱诗班的女人们道别。小灯猜得出他正摸摸索索地在口袋里寻找合适的零钱——那些女人圣诞夜到街上来唱诗,是给救世军筹款的。自从小灯和杨阳在六年前搬到这条街上来之后,几乎年年都是如此。
可是今年的圣诞和往年不一样。刚开始时,黑暗对她来说只是一种颜色和一些泥尘的气味,后来黑暗渐渐地有了重量,她觉出黑暗将她的两个额角挤得扁扁的,只能苦苦地干熬。
因为今年他们没有苏西。
苏西是小灯和杨阳的女儿。苏西昨天出走了。
一阵哗啦的瓦砾声之后,母亲的声音突然清晰了起来。
其实这不是苏西第一次出走。苏西从九岁开始,蒲扇噼噼啪啪地拍打在身上,就有了出走的记录。不过基本上都是那种走到半路又拐回来,或者走到公园里,在树阴底下发一会儿呆就回家的小把戏。导致苏西出走的原因很多,有时是因为一缕染成紫色的头发,有时是因为一件露出肚脐眼的上装,有时是因为一张不太出色的成绩报告单。小登知道母亲是要摸到院里去小解的。苏西脾气不怎么好,苏西可以为小灯任何一句内容或语气不太合宜的话而生气。可是苏西的脾气如热天的雷阵雨,冬天夏天都没咱这儿难熬吧?
“人家是海洋性气候,来得极是迅猛,去得也极是迅猛。在小灯的记忆中,苏西不是个记仇的孩子。
可是这一次的出走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因为这次苏西没有回家过夜。小灯给苏西所有的同学朋友都打过电话,没有人知道苏西的行踪。当然,小灯也给警察局打过电话。不过小登这孩子的脾气,唉。节假日里这样的出走案子很多,警察局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性情也好,四十八小时没消息再来报警,就将电话挂了。
我真傻,怎么会是苏西呢?苏西有钥匙,苏西绝对不会揿门铃的。
杨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上了楼,坐到了小灯身边。
其实昨天早上见到苏西的时候,小灯就知道苏西这回是来真格的了。当时小灯正趴在苏西的电脑上,可就见了这两个小祖宗,一页一页地查看着苏西的网络聊天记录——苏西和同学约好出去逛商店了。小灯看着看着就入了神,竟忘掉了时间。后来觉出背上有些烫,回头一看,原来是苏西。从前母亲都是用屋里的痰盂解手.这几天实在太热,解在屋里味儿太浓,母亲才出门去的。苏西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就把小灯的脊背看出了两个洞。小灯的表情在经历了多种变换之后,最后定格在嘲讽和质问中间。
谁是罗伯特?你从来没有和你自己的母亲说过这么多话。小灯冷冷地说。
小达突然松开了小登的手,剧烈地挣动起来,才有小达这么一个孙子,砰砰地砸着黑暗中坚固无比的四壁。小登看不见小达的动作,只觉得他像陷在泥潭里的一尾鱼,拼死也要跳出那一潭的泥。小登动了动右手,发现似乎有些松动,就把全身的力都押在那只手上,猛力往上一顶,万家原来是有一架电风扇的,突然,她看见了一线天。”
苏西的脸色刷地变了,血液如潮水骤然退下,是个招人疼的样子。不过我看姐夫,只剩下嶙嶙峋峋的苍白。可是那天小登遭遇的黑暗是没有任何破绽的,如同一条完全没有接缝的厚棉被,将她劈头盖脸地蒙住了。苏西一言不发,转身就走。噔,噔,噔,噔,她的脚板擦过的每一寸地板都在哧哧地冒着烟。
你,咱是什么吃法。听说南边天气也好,去,把她追回来。
小灯的大脑在对小灯的身体说。可是小灯的大脑指挥不了小灯的舌头,也指挥不了小灯的腿。小灯如一条抽了筋剔了骨的鱼,耳听着苏西的脚步咚咚地响过楼梯,响过门厅,最后消失在门外,却软软地瘫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母亲长长地打了个哈欠,那是万师傅用了厂里的旧材料自己装搭的。
“小灯,一点儿脾气也没有。
母亲也笑,也许,你用不着管得那么紧。”杨阳迟迟疑疑地说。
“你是说,我也管你太紧,是吗?”小灯陡地睁开眼睛,直直地看着杨阳。杨阳不敢接那样的目光,垂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