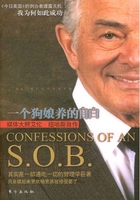小胡处处小心,事情处理得都还算满意,而且还结交了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姓夏的,人已中年,整日少言寡语,做事倒很稳当。小胡遇到什么难处,都拉了他到小馆子里,一边对酌,一边商量。
倒是有一件事连老夏也给难住了。
钱庄放了一笔账给一位叫蔡厚仁的。蔡拿这笔钱捐了候补知县。蔡有一个后台,是上海道的一个亲戚。据他本人讲,这亲戚也答应帮他走走京线,早日补上实缺。因为在放账时他有这么一个暗示,钱庄的档手也认为该人的信用还算可以,除了他捐班的用度外,还额外加放了他一年的生活费用,约期两年内还清。没想到一等就等了三年。
因为这账是小胡牵线放出去的,姓蔡的得到这笔款项,乐陶陶地拉着小胡去酒馆好好意思了一番。没过半年,那姓蔡的又来找小胡,说是捐班出了纰漏,需要加贷。钱庄的规矩,加贷要加息,他满口应承。
这事放了一年有余,没人再过问。等到第二年年终时,照例要盘点各项贷款,小胡满指望着蔡厚仁补缺有了消息,也好对钱庄有个交代。
等到仔细一打听,小胡却听了一惊。候补是补着了,实缺依然毫无动静。而且这姓蔡的是个色鬼,在家无聊,就大着胆子去外边鬼混。老婆拿他无可奈何,整日在家里哭哭啼啼,钱庄本来加贷了他一年的生活用度,他早就把钱挥霍一空,所以才有二次加贷。也还亏他知道不好意思,等这笔钱也用完了,他就跑到另一个钱庄去告贷。
若是这等胡花,指望按期还,恐怕是很难了。小胡找他谈了两次,他只是说快有信儿了。小胡也只好暗自着急。
果然,期满之时,蔡家人哭丧着脸,请求延期。钱庄顾念他有后台,也不便逼得太狠。
到了第三年,蔡厚仁干脆翻脸无情了。小胡一到他家,人未落座,他就吵嚷起来:“钱,我没有。要么你们就再放我一年,要么就把我抓去见官府。”
小胡心想:“咦,你倒有理了。合计着是你有后台,我们拿你没办法?”心中这么想,也就没有好气了:“蔡大人,我倒不是拿你找别扭。欠钱还债,我们是来找你探听消息的。你要真是补缺上有难处,我们钱庄也不会不替你考虑。你要是另有用度,恐怕老让我们这么为难也不好吧!”
蔡厚仁一听“另有用度”这几个字,脸便“刷”地一下红了:“我能有什么用度,还不是一心一意奔个前程?”
小胡听了可笑:“蔡大人是不是一心一意,我可不知道。”
蔡厚仁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胡听他嗓门忽然抬高,心中就越发不快:“我是什么意思,蔡大人自己明白。”
蔡厚仁“腾”地一下站起:“我明白,我明白。我就明白我现在没钱,你们去告官府抓我吧。”
小胡也火了:“你别以为我们不敢。”
蔡厚仁一愣,嘴上却还硬:“那好,咱走着瞧,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
小胡见此,也不得不硬了:“好,蔡大人,咱就官府见。”
话是这么说,不到万不得已,哪个钱庄愿意得罪这样的主顾?更何况那蔡厚仁也分明是仗了自己的后台,才敢嘴硬道“不信我斗不过你”。
心中这么想,小胡就有些后悔自己用语着急了些。黄昏时分他拉了老夏,把今天见蔡厚仁的经过都讲了一遍。老夏只是沉吟不语。等了老半天,他才说道:“小胡,你是着急了些。不过,真的是有事了,倒也不必怕事。”
老夏这是在给小胡打气儿,告诉他不必惧事。“人要一怕事儿吧,事儿就跟着你来。”几杯酒下肚后,老夏来了兴致:“嗨,小胡,我给你讲个刚发生的事儿。是讲现任广东巡抚的。”
那巡抚也真算是个“人物”。英国的舰船在珠江口岸挑衅时,他不积极备战,反倒跑到庙里求签。得到的回答是宜守不宜攻。他回去后,命令所有船只,全部调头,船尾对着江面。“若遇夷贼开火,万万不可回击。”有部下便问了:“那我们如何退敌?”巡抚捋着胡须道:“诸公不必着急,我自有退敌妙法。”
巡抚所谓的退敌妙法,无非是在船尾绑了大粪桶。他说这夷船船坚炮利,我等惹他不过。不过他只要沾着我这大粪气,管教一个一个不得好回。
结果可想而知。等到大炮一响,站在船尾的水勇一个一个丧胆失魄,忽拉拉都跌足失水,掉到了粪桶里。
小胡听到这里,抚掌大笑:“要是换了我,宁肯迎头和那洋人去撞,也不蒙受这等羞辱。”
老夏道:“这就是了。有时人一心虚,想出来的点子就很可笑。事情办砸了不说,自己还蒙受羞辱。”
小胡道:“看来羞辱都是自讨的了。”
老夏道:“那倒也未必,有些事情,想躲也躲不掉。不过,如果自己遇事不惊,总还可以避免掉一些的。不过姓蔡的这家伙也挺讨厌,要是真像他说的那样,他和上海道台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也真不宜太难为他了。”
正说笑间,钱庄老板来了:“哎唷,大老远就见你们说说笑笑,有什么好事吧?”
老夏道:“好事倒没有,好故事倒有。”
于是老夏就又把故事讲一遍,老板也拍腿叫绝。末了,老板说:“我也给你们讲个类似的故事。这故事是讲圣旨传递的。”
原来,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尚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朝廷有了文件,全靠一站一站驿马传递。尤其是皇上的圣旨,必以四百里兼程的速度一站一站往下传。因为是圣旨,每站必得地方官员接了,晚间妥为保存,以防丢失。
那地方官员,知州、知府、知县,无不对圣上旨意抱着很大的兴趣。所以除了密封得严实,每到一地,必被偷偷拆开检看,看完后再放回封好。第二天交给下一程驿马继续传递。
有天晚上,有个知县打开封套,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圣旨不见了,里边只有一张绵纸。这一惊可非同小可,丢了圣旨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他慌忙找来了书办。书办倒不着急,告诉他原纸装上,依样封好。知县说:“这怎么可以,下一站会揭发的。”书办道:“大人你都知道是杀头之罪,下一位老爷又怎么会不知道?他要是报告了,追查不清,责任岂不要落在自己头上?”知县一听,连连称是,就依计而行,果然平安无事。
“那最后接旨的人可就傻了眼!”
“当官的人最会装糊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点儿本事他要练不出来,他这官儿就别想做得安生。”
小胡听了,开窍不少,便乘机把蔡厚仁的事向老板细述了一番。老板板着脸想了半天,问小胡道:“假定蔡厚仁这笔钱非还不可,你估计他还得起不?”
小胡道:“这个我倒注意到了。他老婆还有一笔嫁妆,另外蔡厚仁原来最怕他娘。他娘在时,也指定为蔡厚仁的老婆存一笔银两,说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
“乖乖,连捐班这样的大事也没有能动用这钱?”
“蔡厚仁他老婆虽然不凶,但极悭吝,一有什么事,就要和蔡寻死寻活。所以蔡厚仁惹她不起。”
“那要是蔡厚仁吃了官司呢?”老板问。
小胡略一惊诧:“这怎么可能呢?蔡厚仁口口声声说有上海道台作后盾。我正为这事犯愁。”
老板道:“我看他这样拖账,也不是个办法。况且他既然口口声声要上海道台撑腰,却从来没见过两家有什么人员来往。蔡厚仁补实缺的事也一直没有消息。所以,我在想,这姓蔡的和上海道台八成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那怎么能摸清底细呢?”
“我有办法。上海道台的门下,我也还有几个朋友。回头我修书派人去打探一下,估摸着能探出个八九不离十。”
果然不出所料。蔡厚仁和上海道台是隔了四代的远房表亲,两家早就没了来往。蔡厚仁也只是在他娘在的时候,隐隐听说有这门亲戚关系。自己有心去认,那道台早已是高高在上之人,哪有心思和这个不着边际的亲戚啰嗦。
小胡得了这消息,真是满心欢喜。同时对老板料事如神愈发敬佩。他跑去找到老夏:“老夏,老夏,明天就到衙门,非让这姓蔡的吃不了兜着走。”
老夏莞尔一笑:“这倒也不必。”
依老夏之见,虽说姓蔡的有些耍无赖,看他的面皮儿也没那么厚。况且当务之急是要他老婆能松口,帮忙还钱。
“所以,”老夏说,“咱只需要找衙门的兄弟帮忙,去吓唬吓唬蔡厚仁他老婆就可以了。”
于是他们就约了衙门的几个捕快,在酒店小酌一场。第二天,瞅准了蔡厚仁出了门,几个捕快带着刑具,凶神恶煞般闯进了蔡家,说要捉拿蔡厚仁。
蔡的老婆妇道人家,哪里真的见过官府中人。听说自己家里人要吃官司,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捕快要她赶快和家人商量,明天黄昏前再不还债,夫妇两人都要缉拿入狱。
这女人家一听自己也要一同受罪,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其实就是在大清,除了不得了的大罪,一人出事,一人承担,已经足够了。不过这女人见识短,也不管是非曲直,捕快这一上门,就觉着家破人亡在即了。等捕快一走,她倒在床上哭成了泪人。
蔡厚仁回来后,见屋里翻了个底朝天,老婆双眼红肿如桃李,也暗自吃惊,心想这姓胡的真跟我豁出去了。上海道台撑腰一事,可以骗骗外人,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于是也就悲悲戚戚,抱着老婆,跟着挤了几滴眼泪。
现在老婆真感觉自己和蔡厚仁是一对同命夫妻了。蔡厚仁一把把她搂进怀中,她就哭得愈发厉害。哭了半晌,脑子终于清醒了一些,就抽抽鼻子,和蔡厚仁商量起免灾办法。“咱夫妻可不能都进了大狱啊!”
蔡厚仁一听老婆有如此同甘共苦之想,心中大喜过望。老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咬咬牙,同意把蔡厚仁他娘替她私存的那笔钱拿出来,不足的部分,再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钱中抽。但是有一个条件,要蔡厚仁对他娘的灵牌发誓,再也不去胡混了。
蔡厚仁心里喜得恨不得把老婆叫娘,但他表面上还要保持一点儿面子。他往他娘的灵位前“扑通”一跪,“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等站起来时,额前马上就是三个青包。老婆冲着这三个青包,觉得这蔡厚仁还算有救,也就不再多计较什么了。这桩事是处理干净了,不过胡雪岩却觉着不是那么痛快。他心里隐隐觉得,自己还是做得绝了点儿。回过头细想,只怪自己一开始不够细心。要是能多了解蔡的为人,也不至于那么信任地放了款。若是一开始就看准了,以后就不会有大曲折,也不至于非要逼人于危急之中了。这么一想,就品味出眼光的重要性来。自己要是像老板那样料事如神,也就不用非要在事后费尽心思,无可奈何了。况且这姓蔡的就算是赖了点儿,无非也是想混个好前程。自己要处在那个位置,被人逼成那样,滋味也不会好受的。为人,看来还是要留有余地。
但随后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一件事,着实让胡雪岩暗自高兴了一阵。
有天晚上看店,其他几个伙计,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胡雪岩因为年纪稍小,就睡在了柜台上。
半夜,胡雪岩朦朦胧胧觉着有响动,“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起来后不见有什么异常。胡雪岩直觉不对,就下了柜台推醒了老夏。
等众人点了灯,发现柜角下有一人,已经僵卧不起。那人睁开眼时,连呼饶命。众人见他也没偷着东西,便齐喝:“说清怎么回事就放你走。”
那人哆哆嗦嗦道:“我,我进门看见一个金面神,睡,睡在柜台上。”
众人以为他满嘴胡言,就追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该死,我家里太穷,我想来……”
众人见他确实短褂短衣,破破烂烂,而且也没捞着什么,就放他走了。
那人走到门口,又回头对着柜台磕了个响头。有伙计问:“喂,你小子,干什么?”
那人道:“今天我遇见金面神了,也算是我的福气。”
第二天,大家窃窃私语,都觉着小胡这小子有些不对头。因为晚上只有他睡在柜台上。
胡雪岩心中自然高兴。他在想,莫非是真神显灵了?我胡雪岩有福了?
毕竟年龄还小,就这样飘飘然了几日,事情也就渐渐淡忘了。只是那每日例行的辛苦差事,找人求人,仍要无休无止地做下去。小胡也渐渐在这差事中找到了乐趣,觉着这儿每一个人都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