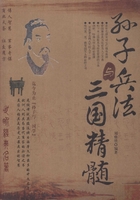“你说什么?”方书恒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差点把手里的茶碗打翻,他瞪着眼前一个左脸上长了颗大痣的矿丁,几乎不敢相信他的话。
“姓尹的领着那些新客有说有笑的干活,新客们都管他叫旭子,亲热着呢。”矿丁说了情况,自己也一脑门子官司,那些贱民怎么就不摆以前的死人脸了?
方书恒听了矿丁的话,失神地站了一会,才慢慢坐回椅子上,脸上渐渐露出一些从容:“这尹旭,倒还真有办法。”
“总管,不是个事呀……”矿丁犹豫了一会,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继续下去,小的担心猪仔们会变得跟那些老客一样不服管啊。”
“不服管?嗯……那边的情形怎么样了,新客们上手了没有,要是上手了,就把尹旭他们调回来吧。”方书恒悠悠然喝了口茶,道。
“上手了,其实小的们也跟着看了,姓尹的那些个法子简单得很,三两天就成事了,之前还给了他们七天,绰绰有余。”
“七天……”方书恒心底泛起一丝苦涩,喃喃地道:“时间给多了!”
见总管似乎有些神思不属,矿丁怕再呆下去会吃苦头,遂小心翼翼地道:“要没什么事,小的先告退?”
“别急,烟馆赌场的事筹办得如何了?”方书恒摆摆手,看着矿丁道。
“房子都备好了,只是这两天大雨,总会派过来的掌柜和荷官怕是误了行程,再说随行的还有器具家什,走山路不便,至于那些窑子里的那些日本娘们,嘿嘿,总管也知道,这天气,她们更没法上山了。”
“我不管。”方书恒把手里的茶碗重重隔在茶几上,站起来道:“你派人去山下镇子里打电报,不管什么天气,都要马上把人给我送上来,这边必须马上开张。”
“总管,这么急,小的担心总会那边又吵吵。”矿丁陪着笑道。
方书恒听得这话,抬起眼皮扫了他一眼,脸色沉了下去:“马大龙,你大小也是个执事了,遇事多用用脑子,严老虽然总理着矿上的事情,他老人家却从没插手过实务,这次为什么千叮呤万嘱咐地要我们把馆子开起来,你就真没想过?”
“小的……小的有些笨。”矿丁,不,执事马大龙战战兢兢地道。
“笨?我看你还是真笨。”方书恒背负双手,在屋子里踱了几步,才轻叹了一声道:“咱们兴昌栈是个新公司,在矿务上也是新手,现在什么都刚刚起步,跟那些几十年的老矿业比起来,咱们最缺什么?缺人,当前最要紧的,就是能有一拨长期的熟练工,可你看看那些老客,能留得住吗?留不住。”
“用婊子和膏药栓住他们……”马大龙听到这里,才总算有些明白了。
“我就说到这里为止。”方书恒摆了摆手,不耐烦地道:“利害你都知道了,要用心地去办这件事,你马上派人下山去打电报。”
“是,小的明白了,小的这就去安排。”马大龙说着,鞠了一躬,就要退出去。
“还有,”方书恒叫住了他,道:“你跟白总管的人商量一下,过几天新客营区就要撤围子了,叫他的人看严点,别跑了人。”
“是,小的明白。”马大龙说着,退了出去。
“老马,怎么才回来呢?”
马大龙刚回到矿区的凉棚里,便听到一个声音在叫自己,回头一看,便勉强笑了笑,道:“杨头,没事跑我这里干嘛来了?”
来人正是杨攀,他本来在井下,干得久了上来透口气,远远看见马大龙来了,便走过来打招呼。
“雨大,来躲躲。”他说着就进了凉棚,大大咧咧地找把竹椅坐下。
“起来,起来。”马大龙看了看四周,脸色紧张地道:“有人看着呢。”
“怕什么,咱们这关系……哎,怎么说你也是执事,还怕了那些小鱼小虾?”杨攀似笑非笑地盯着马大龙。
马大龙一把将杨攀从椅子上拽起来:“这个会里的人,最本事的是告密,让人知道你在我这里这么随便,我就不用混了。”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杨攀一听这话,脸色拉了下来,道:“你让我帮你教训姓白的,我干了,现在事完了,你就不认人了。”
“小声小声。”马大龙急得用手去捂杨攀的嘴。
“得得得,我也不要你为难。”杨攀挥手挡开他,脸上的笑透着一丝狡黠,装出一副老实惶恐的样子来,给马大龙鞠了一躬,大声道:“见过马执事,不知道马执事找小的来,有何贵干?”
马大龙这才松了一口大气,抹着额头的汗水,低声道:“怎么是我找你有事了,不是你找我么?”
“哦!”杨攀恍然大悟一般道:“是这样,这段日子吧,承蒙马执事关照,我专程来谢您呢。”
“不敢当不敢当。”马大龙把柄抓在人手里,哪里敢托大。
“嘿嘿!”杨攀一笑,又坐回了竹椅上,坐下时还装模作样地大声道:“谢马执事赐座。”
马大龙此刻脸上的表情,可谓精彩至极。
杨攀也不管他,左右四周看了看,发现附近没什么人,才向前探着身子,低声道:“上次咱们说的,你们在垄川那个分会到底怎么样,你知道的,我那个表哥人傻,要是入了会,不会吃亏吧?”
“你还信不过我?”马大龙顿了顿,脸色又恢复了正经的样子,小声道:“那边八月间出了事,总管、管事这些都被召回总会了,现在做总管的是我二叔,放心的去,保证没人敢欺负他。”
“哎哟,那敢情好……哎,那边出啥事了?”杨攀对这类消息显然很感兴趣。
“告诉你,你别拿出去说。”马大龙又把身子往前凑了凑,道:“严老的大徒弟白十七被人宰了,手下连他在内五个人,被人打成了马蜂窝。”他说着,比了个手枪的手势。
“你就唬我吧。”杨攀翻了翻眼皮,道:“你们岭南会馆的人,在爪哇岛都是横着走,谁还敢在你们头上动土。”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马大龙瘪嘴道:“岭南会馆算什么,义兴会才是爪哇岛上的老大……会里都在说,是义兴会的人干的。”
杨攀转了转眼珠子,洒然一笑,指着马大龙道:“老马,你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差点被你唬了,怎么说早年我也是混过的,道上的规矩我也知道一些,无缘无故义兴会杀你们大将,这种犯忌讳的事儿,他们做得出来?”
“屁,什么无缘无故?”马大龙见杨攀不信他的话,急了,又看了看左右,发现四周没人,这才道:“那白十七干了不该干的事,得罪了义兴会大龙头,你说他不该死谁该死?”
“我就奇怪了,他干什么不该干的事儿了,就惹得别人要他的命?”
“咳,这事说来话长……”马大龙欲言又止。
“那你就长话短说,这大雨天的闷得慌,聊些闲话打发时间。”
“这可不是闲话。”马大龙顿了顿,终于还是没忍住,道:“听说他绑了一对刚来南洋的兄妹,很有背景的那种,连义兴会都得罪不起的人,这垄川可是义兴会的地盘,人在他们的地盘出事,他们还不想着摘干净?所以,就把白十七给突突了。”
“哎!”杨攀一歪脑袋,笑了:“这事儿有点意思,说说,说说,那两兄妹什么来路?”
“来路嘛,倒是不清楚,不过听活着回来那两人说,好像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马大龙说着,脸上神情变得神秘起来。
“日本人!”杨攀差点被口水呛着:“真他妈会掰。”
他想了想,又道:“不会是那俩小子为了把自己摘干净编的吧?”
“这我就不知道了。”马大龙瘪了瘪嘴:“那两个家伙事发十来天后才偷偷跑回来,白十七那几个又在一间破庙里全被人宰了,这事来龙去脉究竟怎么样,还真是他们两个说了算。”
“老马……”杨攀脸上泛起一丝坏笑:“就你这么好打听的,就没请那哥俩喝喝酒,套点什么内情出来?”
“去去去,你才好打听呢。”
“哎哟!”杨攀突然一拍额头,像是想起什么一般,急道:“老马,这事不好,你们岭南会馆得罪了义兴会,不会被人家铲了吧,我那傻表哥过去,不是正好撞上么?”
“要有事我还敢让他过去?”马大龙白了杨攀一眼,道:“放心吧,陆老幺说了,义兴会好像也不敢把这事捅出来,他们在垄川乡下呆了十几天,也没听到什么消息,要不哪敢大张旗鼓地坐火车回来。”
“哦,那我就放心了……哎,陆老幺是谁?”
“哎呀,不是说了么,白十七那两个手下嘛,一个叫陆老幺,一个叫姚中平,算是严老的徒孙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