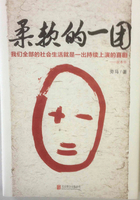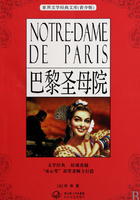“嘿嘿!”老人笑了笑,脸上全是不屑地表情:“半死不活,生死未卜,关你什么事?这两个是你的儿女?不是吧,就算是你店里的伙计,那也说得过去,问题是他们什么都不是,你管这闲事干什么?”
“话不投机,请吧!”邱云来不想跟这人废话,坐回椅子上,端起茶碗举了举,又重重地放下。
“不急,不急。”老人摆摆手,斜吊的眉眼间,显出一丝得意:“既然你嫌我刚才的话不好听,那我就说点好听的。”
“你不是报了案吗,那好,我就问问你,你知道是谁绑了那小姑娘,又是谁在那年轻人身上捅了刀子?”老人斜靠在椅背上,歪着头,斜睨着邱云来。
“除了义兴会那个黄三,还会有谁?”邱云来翻了翻白眼。
“证据呢?”老人又笑了笑,拈着胡须道:“没有吧。”
邱云来愣了,一直以来,尹正纲跟义兴会黄三的恩怨他都只是听说,起先是听田方城说的,后来又得尹正纲的默认。安安和治国出事的时候,他几乎想都没想,便认定了这事跟义兴会有关,却从没想过要去搜寻证据。
是啊,证据呢?怎么才能证明这事就是义兴会做的?如果不能证明是义兴会做下的事,又从哪里去找线索?如果没有线索,又怎么能找到安安?以捕房的名义发寻人启事?那真是大海捞针了。
“你一时头脑发热倒也罢了,我也不怪你,你本就是这么个人。”老人看着邱云来犹豫的神色,有些为扳回这一局而得意,摇头晃脑地道:“可你把田家拖下了水,这我就不得不管了,你不是田家人,你当然无所谓,可怜我这侄女儿,也是个不带脑子的……”
“够了!”脾气再好的人,也不会容得别人在自己家里这样羞辱自己,更何况这人还是跟自己不和了十几年的田家老二,他一把抓起茶几上的茶碗,猛地摔在地上,青花瓷刹时四分五裂。
“哟嗬!”老人吓了一跳,焦黄的圆脸扯动着,立刻就变了形:“你还要打人是怎么地,我……我告诉你,你再横,我也是你老婆的二叔,打长辈……打长辈是要天打雷劈的!”
“长辈,你也配?滚出去!”邱云来怒不可遏,脸色发白,指着门外的手指不住颤抖。
“我也不想在你这个地方呆!”老人怒气冲冲地站起来,理了理自己的长袍,蹬蹬蹬就往外冲:“话我带到了,你自己看着办,田家是不会给你撑腰的。”说完头也不回地去了。
“云来……”田清站在一旁,看着喘着粗气的邱云来,脸色有些难看。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邱云来摆摆手,在椅子上坐下,皱着眉出了一会神,才叹息一声,道:“我刚才是冲动了一些,可这十几年里,我只要一见到他,就会想起小弟……”
“当年那事,只是意外……”田清知道丈夫从不轻易发怒,但每次生气后,总有头疼的毛病,便走到他身后,在他太阳穴上轻轻揉着。
“意外?那不是意外,狗是他故意放出来的,他就是见不得穷小子踏进你们田家的门,他只是没想到他养那几只大狼狗会咬死人罢了。”田清轻柔的动作让邱云来渐渐平复下来,此刻说起当年那段惨事,倒也不见方才那般激烈了。
“正纲的事……”担心丈夫又会胡思乱想,田清赶忙把话题岔开。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一会找找正纲去,看看他那里有什么线索,他刚从贼人手里逃出来,应该有所发现。”邱云来摆摆手,示意田清给他端过一杯茶水来。
“云来,我想……”田清犹豫着,欲言又止。
“你想什么?”
“既然甲必丹和玛腰府都出面了……我想……我想这事我们可能……”田清支支吾吾,低着头站在邱云来跟前,脸上神色有些闪烁:“而且……昨天阿书回来也说了,那艘美国船刚刚离开巴城,要回来也是一个月后了。”
邱云来听得这话,便知道了妻子的想法,一时也沉默了下来。虽然先前因为一时激愤,赶走了岳父的弟弟,但冷静下来一想,还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在荷印这块土地上,没有华人可以违背一位甲必丹的意思,更何况这个意思还出自玛腰府。他不知道尹正纲的事怎么会牵涉到玛腰府,但他明白,自己一个小小的商人,绝对没有跟玛腰府抗衡的能力。即便这些都不论,单说这次,一贯强横的玛腰府和甲必丹能和和气气地托人上门说和,而不是如平常一般直接破门抓人,就已经足以说明这件事情的复杂性了。
况且,找不到周全德,没有那美国人来撑着……
“我是不是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邱云来在心底暗暗地问自己。
“顺子!”
尹正纲坐在自己房间的床板上发呆,听得外面一阵窃窃私语,似是说到了什么玛腰,什么甲必丹,而且听门外站着的几个负责看守他的年轻人的语气,邱云来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心里一时着急,便叫了一声。
“哎!阿纲,什么事?”精灵的顺子应声跳了进来。
“你们在说什么?是不是老板家里有什么事情?”
“呃……”顺子看着自己的脚尖。
“说话!”尹正纲瞪着他。
“正纲……你别急,那个……那个,我们可能遇上了点麻烦。”顺子咽了口口水,脸色有些忧虑:“方才宅子里的阿年过来说,他刚在老板家里听到田家二老爷来了,跟老板吵起来了呢,好像是甲必丹和玛腰不准老板去帮你报案。”
“咳!你也别担心,大不了咱们兄弟一起上,不是还有法不责众这一说么,逼急了咱们几十口子一起到玛腰府请愿去,说什么也得让他们把安安找回来。”见尹正纲脸色有些难看,顺子忙挤出笑脸,安慰道:“退一步说,就算咱们不去告状,就凭咱们这么些人,要找安安回来也比你一个人容易得多不是……总之啊,你别担心就是了。”
尹正纲听了他的话,半天没开腔,只是眉头微微皱起,那一张国字脸上因为思考太过专注,折起几道皱纹。
“正纲,正纲……”顺子叫了几声,他似乎没有听见。
玛腰府——尹正纲的思绪现在清晰得很,在听到甲必丹和玛腰这两个词的那一刻,他便把甲必丹归到不需要注意的那一类。玛腰的地位在甲必丹之上,那么意思肯定出自玛腰,那位在荷印至高无上的华人领袖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呢,难道是因为义兴会?
“顺子,我问你件事。”他忽然抬起头来,看着顺子道。
“哎,你问。”
“坐,先坐下。”他把顺子拉过来,坐在自己旁边,才道:“三宝垄这个地方,有哪些人在做猪仔生意,你平时有没有留意?”
“嘘!小声点。”顺子立刻紧张起来,拉过尹正纲,在他耳边道:“这事可不敢乱说。”
随即又一愣,讶然道:“你怎么问起这个,是不是担心安安会被他们卖掉?”
“我就是问问。”尹正纲淡淡地说。
“你不知道,荷印这地方,现在不敢大张旗鼓地贩人,七年前黄老先生做了玛腰后,就不准那些杀千刀的做这种断子绝孙的生意了。”
说完,他又拿眼睛瞟了瞟门外,压低了声音,在尹正纲耳边道:“不过那些个会馆和会党都在偷偷做,这事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没人敢公开说出来,那话怎么说来着,对,就剩一层窗户纸没捅破了,玛腰府肯定知道,只是睁只眼闭只眼而已。”
就从这句话,尹正纲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证实了先前的猜测。
“就没人管这事?”
“谁管?头两年玛腰府还管过,那些人都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所以也还老实,这些年,啧啧,管不了咯,玛腰府也懒得过问了,只要不闹到台面上来,才不会过问呢……大前年《泗滨日报》那个记者,就是在报纸上骂了两广会馆那些人,说他们贩猪仔,第二天就被刺死在报馆门口,玛腰府倒是管了这事,把两广会馆关了,可过了没几个月,人家换了个岭南会馆的名字,不照样贩。”顺子说着,在地上啐了一口。
尹正纲又沉默下来,听了顺子的话,他的思绪不由有些纷乱。
“玛腰黄伯真跟义兴会那个黄永盛是什么关系,你知道不?”良久,他才问道。
“这个嘛……黄家在垄川是个大家族,黄伯真是他们这一族的族长,黄永盛那一房跟他们关系远着呢,听别人说,在国内,两家都不是一个地方的,更别说什么亲戚了,只不过在南洋这块,要论真正沾亲带故的,却少的很,所以一般只要是同姓,都会邀到一起,在一个祠堂里供祖宗……”
说到这里,顺子忽然顿了顿,像是恍然大悟一般,惊道:“黄永盛就是跟你有仇的那个啊!阿纲,你是不是觉得,玛腰是为了黄永盛才……”
“我就是这么觉得。”尹正纲凝眉看着顺子,沉声道:“就算不是一房的,黄永盛毕竟还是跟他同族,邱老板要帮我对付黄永盛,他又怎么会袖手旁观呢。”
他说的不完全是实话,但意思是表达到了的,同时他心里也有了一个决定——云来客栈里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他毫不怀疑为了帮他找到安安,这些人会不惜冒着被抓进监狱的危险去玛腰府门前请愿,但这事现在已经不是起初那么简单了,他绝不能连累他们。
一念及此,尹正纲站起来,端端正正地在顺子跟前一揖到地。
“正纲,你这是干什么?”顺子被他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赶紧拉着他。
“顺子,阿纲求你一件事。”尹正纲抬头看着这个比自己小了一岁的小伙子,面色严肃地道。
当得到消息的邱云来赶到客栈后院的时候,这里已经站满了客栈的伙计和师傅,众人都低着头,面有愧色。
“怎么回事,人怎么就走了?”邱云来站在院子里,看着打头的关永泉,对他吼起来。
“是我的错。”站在关永泉身后的顺子低着头,说话有些哽咽。
“你个小兔崽子,关你屁事。”关永泉把他朝后一拨,抬头看着邱云来,道:“老板,人是我放走的。”
“你……好……好……”邱云来指着关永泉,气得说不出话来,憋了半晌,才颤抖着道:“你们这是放他出去送死啊!”
“老板!”关永泉突然大喝一声,道:“正纲是对的,我们不能拦他,咱们这些人包括他,都受了您的大恩,咱们不能连累你。”
“连累我?”邱云来许是气得过头了,毫不客气地冲这位大厨道:“我受不起,你们是怕连累自己吧。”
这话说得重了,院里几个女工立刻呜咽起来。
“扑通”,顺子从师傅身后钻出来,跪在邱云来面前。
“老板,邱叔,您听我们一句吧,咱们就算一年不开张,也要把安安找回来,这不算啥,可正纲……正纲现在不能留在这里,这是为了保咱们,更是为了保他。”
“保他?”
“老板,您不要瞒着我们了,我们知道玛腰派人来找您了。”关永泉稍微冷静了一些,也不暴躁了,只是看着邱云来,沉声道:“正纲是对的,现在义兴会、玛腰府都盯着他,义兴会是些什么人,黄伯真又是什么人,咱们都清楚,老板,咱们斗不过啊!”
“放你娘的屁!”邱云来指着关永泉的鼻尖,几乎是嘶吼着道:“我斗不过,你放他一个人出去就斗得过了?如果义兴会想要他的命,今天晚上我们就得给他摆祭堂,找,都出去给我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