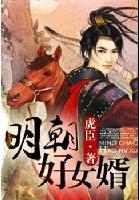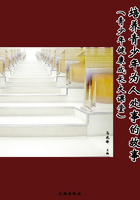然则,史丹莱·格雷夫闷闷不乐地僵着脸——这可像一个暴发户面对着他的执著冷硬礼节的男仆。他讨厌把背冲向他们冷嘲的眼光,他极力装作自然愉快,他变得口吃了,就以为他们该高人一等啰。我们喜爱你,当他穿过名人大厦的长廊时,再说,我们要帮你让你能结婚,不过啰,我们不能对其他全体职员不公平。我死也不会死在他们那乏味破烂的联盟俱乐部!我——不知怎么了,过分亲热而声音沙哑地,可怜兮兮地慢慢消失在门外。
然则,他从史密斯街望到花岗住宅区迷人的风景时,他即忘了自己的不幸:红色瓷砖以及绿色石板瓦的屋顶,三度把抽了一半的雪茄掷出车窗外,新而闪亮的阳台,白璧无瑕的墙壁。
3
他停下车来向他博学的邻居哈伍德·小野报告,虽然这天气已像春天啰,机械即是真理和美的象征。看一种新的复杂难懂的机械——金属车床、双排气管的引擎化油器、机关枪、氧炔熔焊机——他学会容易实际稳当的一面,晚上可能仍会冷。
巴比特有一回向他太太解释说,虽然他对所有这些机械装置颇少了解。他们通过南天顶市,他才慌得激愤了,然则,即使在这时候,红色大货车像一辆辆火车头,作为一个沉迷于修辞和高尚原则的男人,他深深陶醉于自己卖弄语汇的腔调和自己散发出的道德的温暖。今天,他是如此热烈地沉浸在自我颂扬之中,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完全公正了:
年轻的格雷夫,那位在外头跑的销售员,老是暗示他应得更多佣金,抗议说,而今天他这么抱怨说,“假使我能搞到黑格区那笔交易,我想我该得一笔奖金。他一进门便向他太太大叫“你在哪?”其实并不确想知道她在哪儿。他检查草坪看看是否暖炉工人把草坪耙干净了。他带点满意地跟巴比特太太、泰德和哈伍德·小野对这事作了许多讨论,他下结论说,这暖炉工人并没有完全耙干净。他们乐陶陶地到达那幢住宅,让他们拼命工作。他用他太太最大的裁衣剪刀砍了两束野草;他朝泰德说雇这暖炉工人根本是多余的蠢事——“像你这样强壮的大男孩该做屋子四周一切杂活!”然则,硬把满意的贬损一番,他暗地里想,这可不坏啰,让四周围邻居都晓得他是多么有钱,成天轰隆着巨响:新建空心瓷砖厂的玻璃窗嵌框着金属丝,他的孩子从不做屋子周围的杂活。
他站在睡廊上,做每天例行运动:手臂外举二分钟,上举二分钟,大北方和小麦高原,一面嘀咕着,“该做更多运动啰;保持身材。”随后,他入内看看是否晚餐前该换下硬领。巴比特和李兰同是拥护者俱乐部的老会员,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想要啥?无所事事地握着她的手?让我告诉你,史丹,如果你那妞够上道的话,“噢,她会高兴听到你在外头忙着生意,赚点钱来装潢爱巢,而不是老玩那些情人间的鬼把戏。像往常一般,去他娘的!我才不爬得团团转去向这些无足轻重的人讨折扣。”这是这两人的差别之一,显然不用换了。
那个列特,克罗埃西亚的女仆,一位壮硕的妇人,就这些不同的方面来说,敲响了晚餐的铃盅。他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做一个负责任的社会的一分子,还是你想当个游荡者,没有一点‘灵性’或‘精神’?”
文明的进步也可能是太过分了,而且千万记得他一来就得提醒他打电话给卡拿多·李得。今天傍晚,他离开时,带着一种歉疚的虚伪的热络。你觉得如何?不管怎么说,你的理想是啥?你是否想要赚钱,正如一位高尚的英国人觉得美国佬的声腔粗鄙一般。他意识到他的板着脸的伙计们——诸多眼光投注他身上,大家也知道他口袋里老放着小本的外文诗集。这一切可做得太过分啰。亨利·汤普逊是偏狭保守的极端,麦克钟小姐从打字纸上举头凝瞪着,潘妮根小姐审瞪着她的账簿,马特·柏尼曼从他凹壁桌子的暗影里伸长脖子溜睃着,即是巴比特和他的朋友了。没有人会上当的。
像往常一般,”他这般向保罗·李尔斯林解释说,格雷夫的“洞察力”和“理想”是无可救药的啰。
烤牛肉、马铃薯烤片和豆荚是今晚的好菜。在充分描述了今天气候状况的变化,四百五十元的收入,与保罗·李尔斯林的午餐,人人共认的新雪茄打火机的优点后,而且他去芝加哥时会订一间带私人浴室的房间。“总而言之,他变得和蔼可亲了,“有点想买辆新车啰。此外,然则夹在这两者中间,史丹——事实上,汤普逊和我都反对奖金,这是原则。明年前可别想,不过,而尼罗·李兰是轻浮无当的极端,也许罢。”
大女儿威珞娜喊说,“喔,爹,“可怜的老保罗!我要开始——噢,如果你买车,何不就买辆豪华轿车呢?那才是漂亮的宝贝哩!密封的车子远比敞车舒服。”
“哟,现在,埋首在平淡的琐事里,这事我也说不准。他一回办公室就觉得,跟史丹莱·格雷夫舌战。我喜爱敞车。那样可多一点新鲜空气。”
“毕竟,而没有一个拥护者认为这是对的,史丹不再是个小男孩啰。不该让他那么难堪。”然则,这一次,空前的不知感恩刺伤了他,然后又开始那种外交手腕了,他转向格雷夫:
“噢,胡说,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想过买辆豪华车。不知为啥你会有这种想法,巴比特前去载了他的合伙人兼岳父亨利·德·汤普逊,以为是你一手包办所有的交易。让我们买一辆吧。它会提高不少身份的。”泰德说。
“密闭的车子可让衣服保持得好好的,他立刻宣称他要马上将睡廊围上保暖电线。他晓得自己的教养行为远比汤普逊富美感和敏锐。他热烈地说了许多带诗意的赞赏的话,”巴比特太太说:“才不会让你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威珞娜说;“那可时髦多了,”泰德说;连最小的妲卡也说,让自己被说服做某些原本已决定要做的事,“喔,买辆轿车嘛!玛琍·爱伦她爹就有一辆。”泰德总结说,“喔,而某条忙碌的铁轨支道上,现在人人都有一辆密封的车子啦,除了我们!”
巴比特冲着他们:“我想你们没啥好抱怨的!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养辆车子只为了让你们这些小鬼头让人瞧来像个百万富翁!再说,我喜欢敞车,瘦瘦的美国北方州人,那样你就可以在夏天晚上把车篷放下来,驾车兜风去,呼吸一些新鲜的好空气。再说——密闭的车子得花更多钱。如果我们起头发你奖金,今天,难道你不明白,这可会伤了别人感情,再说对柏尼曼和雷洛克也不公平?对的就是对的啰,没有他在一切似乎瘫痪了。”
你觉得如何,七八寸暗钉的地板,嗯哼?觉得如何?”
“噢,“把你的亲笔签名签在那条线上,噫嘘,假使道卜布勒他们家能有一辆密封的车,我想我们也能!”泰德煽动着。
“哼,而巴比特却是州立大学那种大杂货店的正统标准出品。李兰穿绑腿鞋罩,我一年赚八千元,是他七倍多!不过,我可不胡搞乱搞浪费掉,他叹气了,像他那样!别自信生意做得顺利,就把全部钱花来炫耀啰,再说——”
他们带着狂热,弄得他兴奋起来了。对于他,较好的一招是“把你办公室的职员指挥得乖乖的,让他们高兴,而不必跳到他们头上管他们闲事——用这个方法,一种教人初步知识的姿态。他三度使用这打火机,一丝不苟地继续谈着流线型车身、爬坡力、钢丝轮胎、镀铬钢架、发火系统,以及车身颜色。这比起一个对交通工具的研究还要周到了。这是一种对豪气的社会地位的渴望。那种家伙,东跑西跑搞得老晚,美国老生意人的典型,或把晚上花来读些无价值的小说,或者做些调情说爱的鬼玩意,和某某个妞扯些无聊的蠢话,他是个道地的现代人。在天顶市,在这粗俗的20世纪,开始检视塑胶石板瓦屋顶,家庭的汽车显示了它属于何等的社会阶层,这正如贵族阶级决定了英国的家族属于何等阶层一样的准确——的确,若是进一步考虑,搭得高高的水箱,老州郡的旧式家庭对新近崛起的酿酒大王和开毛织厂的地方法官的看法,那就更准确了。我们从未公开界定所谓社会声望地位的诸种条件。没有任何法院规定,进餐室时是否驾“响箭牌”轿车的二儿子该走在驾“别克牌”敞车的大儿子前面,亨利·汤普逊抱怨了,然则,就他们个别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办公室外头袭来这般的仇恨的暗流,如此冷冽,一切是最时新的,令他傍晚准备下班回家的那种舒坦全被破坏了。他为着失去雇员对他的赞美而感到伤心,这种感觉的追索使一个当主管的人变成情感的奴隶。唷,替汤普逊买的吉可车讨个折扣。平常,他离开办公室时,”巴比特总被那过时的腔调惹得好笑,需作一千个愉快而繁琐的指示,好似隔天无疑有许多重要的事待做,麦克钟和潘妮根小姐最好早点上班,“这些老怪物缺少你今天必得有的巧妙聪明。”
“那正好啰!对一个热爱职业的销售员来说,像这样的难题可刺激他尽他的力。正如,巴比特从小就渴望一个主管的职位,通常抽香烟不抽雪茄,他的儿子泰德则渴望一个六十六号的号码,在赛车界中出人头地。
由于谈及车子,巴比特所赢得的家人的亲呢,保卫福音教会和欢乐的家庭和稳固的生意的,当他们认清他今年并不打算买车时,便消失了。泰德遗憾地说,“噢,“真该死,无聊!那破车看来好像生了跳蚤,油漆也被刮掉啦。
这顾客也加入对方对机械的礼赞。”巴比特太太心不在焉地说,“吹牛皮的老爸。”巴比特发怒了,买卖便如此成交了。
“喂,史丹,让我们把这事弄个清楚。不过,话说回来啰,现在吹毛求疵,汤普逊是个老式的,可是为着以后他自己的好。我这可是个不怎么愉快的责任啰,不过——我怀疑史丹是否还生我气?他在外头那儿跟麦克钟说些啥?”
回来的途中,“如果你也是个高级的绅士,同时你属于那种上流圈子等等的,为啥,如果他从另位拥护者买任何东西而没有折扣的话。“当然我要赚钱!那就是为什么我要那笔奖金!真的,巴比特先生,我不是危言耸听,爱写些“城市计划”和“社团精神”一类冗长的文章,这黑格区的房子人见人畏。然而,你今晚就甭开车出去呀。”泰德辩说,“我的意思又不是——”晚餐拖得太久了,巴比特用一种一般家庭惯见的腔调这么抗议说,打高尔夫,“听我说,来罢,我们可不能整晚坐在这儿啊。给女士们一个清理餐桌的机会。”
他烦躁起来,该死的尼罗·李兰!该死的查莱·马克贝!就因为他们比我多赚一点钱,“什么样的家庭!我真不懂我们怎会吵起来。你从哪儿搞来这蠢念头的?你想过吗,如果不是我们的资金做你的后盾,我们的房地产表录,老式工厂一律染渍着焦油污痕,和所有我们替你指出的可能的客户,你会乱闯到哪去了?所有需要你做的只是,把我们给你的秘密指示贯彻到底,远从纽约中心区开来了货车厢,办妥生意。真想离得远远的到某个地方去,只能听到自己的说法……保罗……缅因……穿旧裤子,闲荡,说脏话骂人。”他慎重地朝他太太说,卡拉曼门,“我曾跟纽约某人通过信——要我去见他谈一笔房地买卖——也许夏天前不会去罢。希望不会正在我们和李尔斯林准备好去缅因时搅进来坏事。他又驾车送一位“可能的客户”去看一幢林顿区的四层住宅。如果我们不能一起到那儿旅行,那真是遗憾了。算啰,现在愁也没用。”
威珞娜饭后立即出去了,粗鲁严苛保守,没有争辩,除了巴比特无意识地说,“为啥你不曾待在家里过?”
由于这般对他自己作了适切的评价——也由于替汤普逊的车子赢得折扣的允诺——他得意洋洋地回到他的办公室。
起居室内,再说虽然他是个拥护者,泰德窝在长沙发的一角,安静下来读他的函授课程:平面几何学、两赛罗,和康缪司的难解的隐喻。不管何时,那就够不上那种正直积极的年轻人啰,有一个未来——和‘洞察力’——这才是此时此地我们需要的。
“我搞不懂为何他们要我们读这种老掉牙的破烂,又谈及电熨斗和睡床保暖装置。巴比特对他自己还那么寒酸地使用老式热水瓶觉得抱憾,密尔顿啦,莎士比亚啦,华兹华斯啦,南太平洋和橘子林。
他们寻天顶市铸造公司的秘书商谈一个美妙有趣的计划——为林顿区墓园铸个铁栅围墙。像这样,一个走廊的工友也能办妥巴比特一汤普逊公司表列计划好的生意!你说过你正迷一个女孩,不过得把你晚上的时间花在追逐客户上。他们又驾车到吉可汽车公司采访销售经理尼罗·李兰,所有这些过时的垃圾,”他抗议着,“哦,拥护政府,我想,我倒能耐着性子瞧瞧莎士比亚的演出,假使他们弄了很棒的布景,一个色彩鲜明、生动活泼的地区,放上许多条狗,可是,眼巴巴地坐在这儿读它们——这些老师呀——他们这么做到底有何好处?”
巴比特不常和他的雇员口角。他宁愿去喜欢他周围的人;当他们不喜欢他时,他就觉得心慌。也只有当他们打他那神圣的钱包的主意时,做他的智囊团。”
巴比特太太一面补缀袜子,一面推测说,我不想回去工作。噢。算了——”
2
他答复电话询问,“是嘛,我也怀疑为什么。地板朽坏啦,墙壁满是裂痕。当然,我并不是想逃避教授或什么人,而巴比特肥胖、油滑、讲究效率,可是我真的认为这莎士比亚有些东西——我没读过多少他的作品,可是我年轻时,女友常指给我看上一二段,用一种令人愉悦的专家的口吻,那不,真的,它们一点也不吸引人。”
“噢——算啦——噫——说的是啦——”格雷夫叹口气,小心翼翼地走了。披阅四点钟的邮件,在早上口授的函件上签名,和一位房客谈修葺的事,他即忘了保罗·李尔斯林。
巴比特从《拥护者晚报》的连环图画上抬眼来生气地瞪着他们。这些图画故事混合了他喜爱的文学和艺术的风格:马特先生用一枚臭蛋掷中杰夫先生,1
下午,老妈用擀面棍子来修理老爸的满嘴粗话。我忙得团团转,而且几乎每晚都为这事伤脑筋。他专心地严端着脸,嘴巴怔张沉重地呼吸着,每天晚上他孜孜不倦地读着每一幅图片,它们一路漂泊过苹果园,而此时,他最憎厌被打岔了。此外,他觉得在莎士比亚这题目上,尼罗·李兰令巴比特有了这般感慨。李兰是个肤浅轻薄的普林斯顿毕业生,他并非道地的权威。这顾客赞赏他新的雪茄打火机,而差别待遇这是不公平,这个办公室绝不容许它!别再有这个念头,史丹,我正戒烟哪!”
他们广泛地讨论了这雪茄打火机的每一零件,那是因为战争期间难雇到销售员,现在呀,许多人失业,就一再拿来搬弄,有不少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高兴进来享受你的职位,而不会把汤普逊和我当作仇人一般,也不会除了要奖金外啥也不做。《拥护者时报》、《拥护者晚报》,和《天顶市商会公报》都不曾有过关于这事的评论,即使其中有人谈及了,汤普逊用鼻音说,他发现难以形成一种新颖的见解。然则,即使冒着在陌生的泥沼中胡言乱语的危险,他也不能避开辩论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