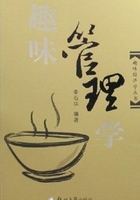为了GDP的增长,悲剧依然在重演。GDP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2002年9月16日的报道,中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在反映全社会劳动效益的指标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在1978~2002年24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6%,慢于GDP在同期9.4%的增长;反映工业企业投入产出的综合指标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降为2001年的8.9%,23年间下降63%。由于生产效益低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并未进入良性循环,城镇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民人均纯收入1995~2002年年均仅增长4.7%,消费率(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比例)也由1978年的43%降为2002年的40%。
GDP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但任何数字都有它的“陷阱”。
天灾人祸的灾后重建让GDP增长,“拉链工程”让GDP增长。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GDP都增加了一次。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GDP这样描写:
“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
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这段文字的含义与前面所举的“经济学家吃狗屎”的例子异曲同工,其实现实当中类似的情形真是太多了。例如,卖假药的人让GDP增长,吃坏身体的人去看病也让GDP增长。看看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的这些题目吧:《“黑”佐料调“白”腐竹》、《竹笋保鲜的“秘方”》、《病死母猪肉做鲜肉松》、《淘汰母猪变“鲜”肉》、《腐肉“巧”炼猪油》、《防寒服“败絮”其中》、《“果肉果冻”裹的是什么》、《“无公害蔬菜”令人心惊》、《土办法生产的“卫生筷”》、《黑心厂生产“黑心肠”》、《“美味”腊肉如此出炉》、《硫磺熏制“注水”中药材》、《鸡精里的“商业秘密”》……它们都可以让GDP增长,但是却损害了国民的福利,国民财富得到的是负积累。
没有质量的生产活动,不可能带来社会财富的累积。固定资本的质量不好,没到使用期限就不得不报废,那么固定资本形成的总额再多也不能提高国民财富。当我们要拆毁“豆腐渣工程”重建时,请记住这样的教训,它不仅要从国民财富统计中剔除,而且为了重建我们又消耗了一次自然资源。从国民财富的角度看,国民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正像被砍伐的森林,“算做了当年的GDP,但对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
再听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的感慨吧——
“在注重财富的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到欧洲去,看到那里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护。新盖的楼也是,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10年20年看着不顺眼、过时了,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4.GDP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
即使是为了促进GDP的增长,也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例如:
以政府为主导,倚重于扩大投资的方式,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大搞开发区,跑马圈地,城市建设大大优先于技术改造安排和劳动力培训;
依靠财政投资输入,大规模借债,投资高速公路、铁路、水库;
不断向国有企业输血,将金融资源向它们倾斜,哪怕其设备闲置;
对一些不发达地区,通过国债项目投资,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
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进行工资性转移支付;
……
这都可以形成GDP的增加。但其中不少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其实是在浪费有限的资源。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67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中》一文中已经写到:
“浪费的现象在大量已成现实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导致了资本利用率的不足——如按对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厂,每小时仅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和航空集散地建筑的低利用率等。”
在中国,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城市的上一任领导通过上几条公路、搞几个城市广场、建一些开发区,提高了他任期内的建筑GDP,但却没有真正形成内生的投资环境,缺少富有活力的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以至基础设施建完以后的GDP不知从何而来。上一任轰轰烈烈,下一任找钱还账,不要说无钱修路,甚至因无钱而欠薪。
还有,资源浪费、配置不合理的另一面,是在中国随处都能看到富丽堂皇的建筑,尤其是政府、银行、工商、税务、公检法、国有通信和电力公司等的办公楼和休闲培训中心。和19世纪工业革命国家在使用资本时讲究节约的习惯不同,“欠发达国家正在以更大的气派浪费资本;所以当出现某个大型项目完成但其提供的就业却比期望的要少时,就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闲置的生产线、荒芜的开发区、没有人流的机场、豪华的办公楼和度假村,它们能解决就业问题吗?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一边是经济增长、一边是求职艰难的原因。
5.GDP不衡量价值的判断
GDP无法衡量社会的价值判断,例如无法衡量社会公正,无法衡量国民的幸福程度。
GDP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这往往与幸福无关。军火生产在统计中是很重要的部分,但假如一个国家更多地生产大炮,更少地生产黄油,人民幸福吗?
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但价格与幸福也关系不大。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在不断降低。按价格计算,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却带给人们很大的利益。
GDP也不衡量闲暇。只要人们天天加班,就能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GDP就在增长。但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快乐吗?当我们要享受闲暇时,GDP反而在减少。
汽车能创造庞大的价值,但GDP从来不计算天天堵车占用了我们生命中的多少时间。
所以,在前面提到的企业家宁高宁先生,还有另一面的论述:
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的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可是牺牲了环境,滥用了资源,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民众的健康、教育、艺术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就使GDP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吸引了,怪不得有人想推出全面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指数,也是为什么我们到一些GDP增长并不快的欧洲小国会感到很详和舒适的原因。
6.GDP不衡量分配
GDP是一个生产总量的指标,但不衡量分配。
GDP不衡量贫富的差距。中国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2005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
GDP不衡量就业,即使“失业已成中国的定时炸弹”。上马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GDP很容易就拉上去了,但假如忽视了劳动密集型的项目,GDP增长之后的受益者,就只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广大劳动者。
GDP不衡量社会的保障,光有GDP的增长而没有保障面广、保障水平高的社会保障网,一旦我们退休、生病、失业,就会陷入困境。特别是农民,他们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创造大量的GDP。但他们退休、生病时,由谁保障呢?
GDP不衡量谁从GDP这里最终获益。GDP是以一国为依据,而不是以一国的人口拥有为依据。中国的外资多了,GDP就会增大,但是GNP(本国人拥有的生产总值)不会同时增大。设想某个地区从国外引进了一家企业,资本全部由外商投资,并且资本有机构成很高,雇佣当地劳动力很少;由于高价进原料和组装件、低价向国外销售,公司在名义上亏损。这样,由于没有利润,当地政府得不到所得税,由于进价太高和出价太低,增值税也会少收。于是,GDP的相当部分反而形成了国外这家公司的收入。这个例子当然很极端,而且引进外资对中国绝对重要,我们的所得并非GDP的全部。
八、超越对GDP的崇拜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纯经济福利(净经济福利)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纯经济福利是在GDP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作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负作用的项目(如污染、环境破坏和对生物多样化的影响,都市化影响),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作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如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像家务劳动和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根据纯经济福利指标,印度尼西亚从1971年到1984年GDP年均增长7.1%,但如果将石油、木材大量开采出口以及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作为成本加以扣除,年均增长率只有4%。
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主张列出水、空气、垃圾等环境污染的每项污染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将其改善经费作为成本从GDP中间扣除。按此方法,当时GDP在日本的增长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
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提出一套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如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财富分配在公平的标准之外,必须被扣分;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等;严谨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力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打破了传统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观念。这项人力发展指标还加上三项变数: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强调人力开发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
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在会计行业,国外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的新会计理念。其计算方法是要在现有统计基础上扣除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扣除所计量资源的耗费,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在中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原来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已经加上了4个字,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但是,很多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还没有真正加上这4个字。
中国政府以胡锦涛主席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情实际,顺乎进步潮流,已经合乎发展逻辑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从增长到发展,这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新突破,其影响异常深远。
从中国正在酝酿的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来看,财政改革主要集中在支出方面,例如积极支持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切实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从体制上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积极运用财政政策支持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大对环境整治和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的投入,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而在税制结构调整方面,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将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普通消费品将逐步从税目中剔除,而一些高档的消费品将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农业特产税将取消,农业税率会逐步降低,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这些改革的含义,与“五个统筹”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息息相关。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可以预言,即使是在衡量经济成就方面,GDP的至上地位也会降低,而其它一些指标如就业、负债、效益会与GDP同行。GDP从“总分成绩”变成了“单科成绩”,当然,GDP还是最重要的单科。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对地方和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必然也会变化。生产建设型的政府必须转变为公共服务性的政府,转变为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能力、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为人民办实事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