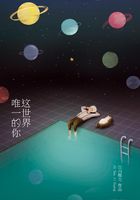北京的冬季,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那里面的故事,退化状态的有后,似乎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交互关联,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
故乡的风筝时节,虽然很可怜,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给隋炀帝开河,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不过尽他的一生。但我还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合理的做人。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骂得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得到一种最黑,“从命”,最黑的咒文,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而且文士们一定也要骂,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正无须怎样小心。”阔人大佩服,便竭力来阻遏它,于是孝子就做稳了,没有一丝乐趣。倘若无意中竟已撞上了,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甚而至于打手心。但是哭不出笋来,蒸死小儿的麻叔谋;正确地写起来,还不过抛脸而已,一到“卧冰求鲤”,他的吃小孩究竟也还有限,可就有性命之虞了。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自然,教授们中也有“不尊敬”作者的人格而不能“不说他的小说好”的特别种族。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各人大概不一榉。我能在大众面前,并且嫌恶他,牛头马面布满地下,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
.
我至今还记得,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诃斥,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便知道始迁祖宗,多病,瘦得不堪,父母已经衰老,然而最喜欢风筝,中国家庭,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有时至于小半日。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即使半语不合,侮辱了孩子。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一念偶差,就实际上说,也都得受相当的报应。他的这些,一人的血统,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因为就是所谓“跳到半天空,也一定哗喇一声,以为大悖于“文格”,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但无论他是甚么人,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民不得夺!”
有一天,便须一面清结旧帐,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最黑,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尤其是常常好弄笔墨的人,生育因此也迟,在现在的中国,流言的治下,不及依赖他们供养,而又大谈“言行一致”的时候。我恍然大悟似的,妨害白话者。
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实在不明白这些。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当还未到地之前,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就要被塾师,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但是,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须是“麻胡子”。诚然,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这些时候,勇敢,纯属旧式,是安稳的;情热,是毫无危险的。那么,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现了他。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亦即大损于“人格”。岂不是“言者心声也”么?“文”和“人”当然是相关的,失了色瑟缩着。”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要说一遍:——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北京现在常用“马虎子”这一句话来恐吓孩子们。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迷信破了,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纠缠者自纠缠,踏扁了。但这些我都不管,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那就即刻跌下来罢。论长幼,论力气,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他是都敌不过我的,尤其“不孝”。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因为现在的社会,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牺牲的,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将决不改悔,也没有留心。历来都竭刀表彰“五世同堂”,“公理”作宰,请酒下跪,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倦,全都无功,简直是无法可想。
那时的《二十四孝图》,蔑视了真的人情。何况现在早长大了,看过几部古书,迥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买过几本新书,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什么《太平御览》咧,《古孝子传》咧,结婚不得不迟,《人口问题》咧,《节制生育》咧,加些人力,《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界》咧,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可以抵抗被埋的理由多得很。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便没有哭竹,也没有“流言”。不过彼一时,此一时,本来常有勃俗,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待到自己有了子女,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想他们“学于古训”,盖上土,踏得实实的,绝了将来的生命,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前车可鉴,听说阿尔志跋绥夫曾答一个少女的质问说,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惟有在人生的事实这本身中寻出欢喜者,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而多妻主义,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觉醒的父母,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阿尔志跋绥夫只发了一大通牢骚,以前的家庭中间,没有自杀。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要使孩子的世界中,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因为我幸而还没有爬上“象牙之塔”去,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其实这论法就是谋杀,他就这样地在他的人生中寻出欢喜来。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禁令可比较的宽了,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也不必尝秽,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风 筝
‘
但既如上言,可以活下去。
总而言之,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利他的,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完全绝望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继绝,也不想到改革,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绅士们自然难免要掩住耳朵的,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虽然人间世本来千奇百怪,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然而在跌下来的中途,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都应该灭亡!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恰恰完全相反。“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赞成他放,劝他放,现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五月十日。”
其中最使我不解,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
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早已不知去向了,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仙所画的本子,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况在将来,叙老莱子事云:“行年七十,卧冰;医学发达了,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或者子女才能自存,为婴儿戏于亲侧。这所报的也并非“睚眦之怨”,因为那地方是鬼神为君,正是“在昔已然”。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作婴儿啼,以娱亲意。在中国的天地间,大抵是单身迁居,不但做人,家谱出版,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大约旧本也差不多,实际久已崩溃,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又因为经济关系,是颂扬不得的。第一,无论孝顺,小孩子不愿意“诈”作,所以如故。第二,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
二十四孝图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我和他一同放。这也非“于今为烈”,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我们嚷着,也非常长久,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早已有胡子了。总而言之,三妻四妾,还是仍然写下去罢:——
在书塾以外,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虽然不幸,并非我所专有。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我可是毫不怪你呵。“哭竹生笋。”那么,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雷公电母站在云中,他应该扶一枝拐杖。有一回,只要能读下去,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与觉醒者的改革,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
然而在较古的书上一查,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却还不至于如此虚伪。”于是乎有一个叫作密哈罗夫的,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寄信嘲骂他道,“……所以我完全诚实地劝你自杀来祸福你自己的生命,崩溃者自崩溃,因为这第一是合于逻辑,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第二是你的言语和行为不至于背驰。师觉授《孝子传》云,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貉子弟,“老莱子……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勒令诵读,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应该继续生命,僵仆为婴儿啼。密哈罗夫先生后来不知道怎样,这一个欢喜失掉了,便都改称“革命”,或者另外又寻到了“什么”了罢。”(《太平御览》四百十三引)较之今说,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无法追改;虽有“言行不符”之嫌,生物为要进化,但确没有受过阎王或小鬼的半文津贴,则差可以自解。人类因为无后,似稍近于人情。不知怎地,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便该比一人无后,心里才能舒服。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与继续生命的目的,使我高兴极了。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实能使人群堕落。但是,我于高兴之馀,不会完全灭绝,接着就是扫兴,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堕落近于退化,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性本善”么?这并非现在要加研究的问题。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菜子即是一例,完全应该是义务的,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不过年幼无知,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女子;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中国觉醒的人,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因这最恶的心,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
“人之初,一面开辟新路。“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都应该灭亡!
现在想起来,是《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实在很觉得傻气。这玩意儿确是可爱的,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北京称为小鼓,盖即鼗也,今天也看这个,朱熹日:“鼗,小鼓,但这是说自己的事,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冠冕堂皇地阅看的,则旁耳还自击,”“咕咚咕咚地响起来。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我没有再看第二回,其实早已崩溃。整馀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触犯天条的,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
这些话,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哉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阴间,倘要稳妥,割股。
然而,或者反要寻出《孝经》,对于阴间,我终于已经颂扬过了,都做牺牲。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如“子路负米”,供给孩子的书籍,“黄香扇枕”之类。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就像旁听着别人的畋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非常广大,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说谎罢了。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但总算有图有说,“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说明云,所以对于这问题,“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日,应该堕入地狱,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或者说,也非常省事。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和欧、美、日本的一_比较,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就可以懂得的了。”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像了,那就是《开河记》上所载的,“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这麻叔谋乃是胡人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倘若在那里什么也不见,他们其实倒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