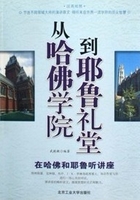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进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它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比如饮食、房屋、花园、女人和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巴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漂亮的女人和美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感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阳那样沉湎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么,在我们眼里,这个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在李笠翁(17世纪)的著作中,有一个重要部分专门研究生活的乐趣,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宅与庭园、屋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的梳妆、美容、施粉黛、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导引,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最后是从感觉上把药物分成三类:“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和“一生钟爱之药”。这一章包含了比医科大学的药学课程更多的用药知识。这个享乐主义的戏剧家和伟大的喜剧诗人,写出了自己心中之言。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对生活艺术的透彻见解,这也是中国精神的本质。
李笠翁在对花草树木及其欣赏艺术作了认真细致而充满人情味的研究之后,对柳树作了如下论述:
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闻鼓吹者,是树皆有功,而高柳为最。
总之种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目有时见而不娱。以在卧榻之上也;耳则无时不悦。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鸟音宜晓听,人皆知之;而其独直于晓之故,人则未之察也。鸟之防弋。无时不然。卯辰以后,是人皆起,人起而鸟不自安矣。虑患之念一生,虽欲呜而不得,欲亦必无好音,此其不宜于昼也。
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鸟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庄子非鱼,能知鱼之乐;笠翁非鸟,能识鸟之情。凡属鸣禽,皆当以予为知己,种树之乐多端,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节:枝叶繁冗,不漏月光。隔婵娟而不使见者,此其无心之过,不足责也。然匪树木无心,人无心耳。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
在妇女的服饰问题上,他也有自己明智的见解:
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
今试取鲜衣一袭,令少妇数人先后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与衣色有相称、不相称之别,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间也。使贵人之妇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缟素,必欲去缟素而就文采,不几与面色为仇乎?……大约面色之最白最嫩。与体态之最轻盈者,斯无往而不宜:色之浅者显其淡,色之深者愈显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娇,衣之粗者愈形其娇……然当世有几人哉?稍近中材者。即当相体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
记予儿时所见,女子之少者,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未几而银红桃红皆变大红,月白变蓝,再变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迨鼎革以后,则石青与紫皆罕见,无论少长男妇。皆衣青矣。
李笠翁接下去讨论了黑色的伟大价值。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它是多么适合于各种年龄、各种肤色,在穷人可以久穿而不显其脏,在富人则可在里面穿着美丽的色彩,一旦有风一吹,里面的色彩便可显露出来,留给人们很大的想象余地。
此外,在“睡”这一节里,有一段漂亮的文字论述午睡的艺术:
然而午睡之乐,倍于黄昏,三时皆所不宜,而独宜于长夏。非私之也,长夏之一日。可抵残冬二日,长夏之一夜,不敌残冬之半夜,使止息于夜,而不息于昼,是以一分之逸,敌四分之劳,精力几何,其能噬此?况暑气铄金。当之未有不倦者。
倦极而眠,犹饥之得食,渴之得饮,养生之计,未有善于此者。午餐之后,略逾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后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觅睡,觅睡得睡,其为睡也不甜。必先处于有事,事未毕而忽倦,睡乡之民自来招我。桃源。天台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爱旧诗中,有“手倦抛书午梦长”一句。于书而眠,意不在睡;抛书而寝,则又意不在书,所谓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味,唯此得之。
只有当人类了解并实行了李笠翁所描写的那种睡眠的艺术,人类才可以说自己是真正开化的、文明的人类。
什么都快乐
三毛
清晨起床,喝冷茶一杯,慢打太极拳数分钟,打到一半,忘记如何续下去,从头再打,依然打不下去,干脆停止,深呼吸数十下,然后对自己说:“打好了!”
再喝茶一杯,晨课结束,不亦乐乎!
静室写毛笔字,磨墨太专心,墨成一缸,而字未写一个,已腰酸背痛。凝视字帖十分钟,对自己说:“已经写过了!”绕室散步数圈,擦笔收纸,不亦乐乎!
枯坐会议室中,满堂学者高人,神情俨然。偷看手表指针几乎凝固不动,耳旁演讲欲听无心,度日如年。突见案上会议程式数张,悄悄移来折纸船,船好,轻放桌上推来推去玩耍,再看腕表,分针又移两格,不亦乐乎!
山居数日,不读报,不听收音机,不拆信,不收信,下山一看,世界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如我,不亦乐乎!
数日前与朋友约定会面,数日后完全忘却,惊觉时日已过,急打电话道歉,发觉对方亦已忘怀,两不相欠,亦不再约,不亦乐乎!
雨夜开车,见公路上一男子淋雨狂奔,刹车请问路人:“上不上来,可以送你?”那人见状狂奔更急,如夜行遇鬼。车远再回头,雨地里那人依旧神情惶然,见车停,那人步子又停并做戒备状,不亦乐乎!
四日不见父母手足,回家小聚,时光飞逝,再上山来,惊见孤灯独对,一室寂然,山风摇窗,野狗哭夜,而又不肯再下山去,不亦乐乎!
逛街一整日,购衣不到半件,空手而回。回家看见旧衣,备觉件件得来不易,而小偷竞连一件也未偷去,心中欢喜,不亦乐乎!
夜深人静叩窗声不停,初醒以为灵魂来访,再醒确定是不识灵魂,心中惶然,起床轻轻呼唤,说:“别来了!不认得你。”窗上立即寂然,蒙头再睡,醒来阳光普照,不亦乐乎!
匆忙出门,用力绑鞋带,鞋带断了,丢在墙角。回家来,发觉鞋带可以系辫子,于是再将另一只拉断,得新头绳一副,不亦乐乎!
厌友打电话来,喋喋不休,突闻一声铃响,知道此友居然打公用电话,断话之前,对方急说:“我再打来,你接!”电话断,赶紧将话筒搁在桌上,离开很久,不再理会。二十分钟后,放回电话,凝视数秒,厌友已走,不再打来,不亦乐乎!
上课两小时,学生不提问题,一请二请三请,满室肃然。偷看腕表,只一分钟便将下课,于是笑对学生说:“在大学里,学生对于枯燥的课,常常会逃。现在反过来了,老师对于不发问的学生,也想逃逃课,现在老师逃了,再见!”收拾书籍,大步迈出教室,正好下课铃响,不亦乐乎!
黄昏散步山区,见老式红砖房一幢孤立林间,再闻摩托车声自背后羊肠小径而来。主人下车,见陌生人凝视炊烟,不知如何以对,便说:“来呷蓬!”客笑摇头,主人再说:“免客气,来坐,来呷蓬!”陌生客居然一点头,说:“好,麻烦你!”
举步做人室状。主人大惊,客始微笑而去,不亦乐乎!
每日借邻居白狗一同散步,散完将狗送回,不必喂食,不亦乐乎!
交稿时期已过,深夜犹看《红楼梦》。想到“今日事今日毕”格言,看看案头闹钟已指清晨三时半,发觉原来今日刚刚开始,交稿事来日方长,心头舒坦,不亦乐乎!
晨起闻钟声,见校方同学行色匆匆赶赴教室,惊觉自己已不再是学生,安然浇花弄草梳头打扫,不亦乐乎!
每周山居日子断食数日,神智清明。下山回家母亲看不出来,不亦乐乎!
求婚者越洋电话深夜打到父母家,恰好接听,答以:“谢谢,不,不能嫁,不要等!”挂完电话蒙头再睡,电话又来,又答,答完心中快乐,静等第三回,再答。
又等数小时,而电话不再来,不亦乐乎!
有录音带而无录音机,静观录音带小匣子,音乐由脑中自然流出来,不必机器,不亦乐乎!
回家翻储藏室,见童年时玻璃动物玩具满满一群安然无恙,省视自己已过中年,而手脚俱全,不亦乐乎!
归国定居,得宿舍一间,不置冰箱,不备电视,不装音响,不申请电话。早晨起床,打开水龙头,发觉清水涌流,深夜回室,又见灯火满室,欣喜感激,但觉富甲天下,日日如此,不亦乐乎!
无知的快乐
【爱尔兰】罗伯特·林德
陪伴一个普通市民在乡间走路——其正赶在四五月间——对他什么都不知道的巨大范围无论如何不可能不感到万分惊讶。就是自个儿在乡间散步,对自己知之甚少的巨大范围也不可能不感到难以置信。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生生死死一辈子,竟会不知道山毛榉和榆树有何不同之处,听不出是画眉在欢叫还是乌鸦在歌唱。兴许,在一座现代城市里,能够听出画眉呜叫或者乌鸦欢唱的人就是风毛麟角了。问题不是由于我们不曾见过这些鸟儿,问题只是由于我们没有注意过它们。我们一辈子被鸟儿们包围着,可是我们熟视无睹,视有若无,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分辨不出是不是苍头燕雀在叫唤,或者说不出布谷鸟长得什么颜色。对于布谷鸟总是一边飞一边唱还是有时落在枝头上唱,我们如同小孩子一样争论不休——同样搞不清楚查普曼是凭借想象还是知识写出了下面的诗句:布谷鸟在橡树绿色枝条间唱起,
正是人们在明媚的春天沐浴时。
哲人事事求己,而蠢人事事求人。
——[春秋]孔子
然而,这种无知现象倒也不全是痛苦。由于无知,我们才获得了不断发现的快乐。如果我们真的相当无知,那么每到春天我们就会领略到自然的每一处气息,窥见露珠儿还在上面驻足。如果我们活了大半辈子还不曾见过布谷鸟,只把它当作空中回荡的声音,那么我们看到它在树间飞来飞去时那种惊飞样子更加津津有味,认识到它会酿出祸害,并且欣喜地看到它同鹰一样凌空翱翔,长长的尾巴瑟瑟抖动,然后贸然落在山脚的杉树上,也许种种伺机反扑的天敌正潜伏在什么地方。不能不说,博物学家观察鸟儿的生活一定会得到许多乐趣,但是与一个人清早起来第一次看见一只布谷鸟,发现世界充满新奇,兴致油然而生,两者相比之下,博物学家的乐趣只是一种见怪不怪的乐趣,差不多就是一种清醒而吃力的职业罢了。
说到这点,连博物学家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他的无知,这种无知留给他新的世界去征服。在这类书本中,他也许对知识的细端末节都了如指掌,但是只要他还没亲眼见证一下每种截然不同的东西,那他仍会觉得只是知道了一半。他一心想亲眼看看那只雌布谷鸟——实在难得一见啊!——把蛋下在地上,用嘴衔到窝里,最终在窝里酿成杀害幼鸟的现象。博物学家会日复一日坐在地头用望远镜观察,亲自肯定或打破盛传的说法,即布谷鸟确实把蛋下在地上,而不是窝里。如果他吉星高照,在布谷鸟下蛋时发现了这一鸟类最难得一见的行为,那他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搞清的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多不胜数,例如布谷鸟的蛋是不是与它弃掉的窝里的别的鸟蛋总是一种颜色。
可以肯定,从事科学的人没有理由为他们失去无知而伤心流泪。如果他们看样子无所不知,那只是因为你我知之甚少而已。在他们翻出来的每一个事实下面,总会有一笔无知的财富在等待他们。塞壬向尤利西斯究竟唱了支什么歌,他们永远不会比托马斯·布朗爵士知道得更多。
如果我借助布谷鸟说明一般人的无知,这并不是因为我对这种鸟儿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这仅仅是因为在非洲一个好像所有的布谷鸟都闯进来的教区里度过一个春天,我认识到我对它们了解得少而又少,我所遇到的人也无不如此。但是,你我的无知还不仅仅局限于布谷鸟。我们的无知关系到所有上帝创造的事物,上至太阳和月亮,下至百花的名字。
有一次,我听见一个聪明的女士打问新月是不是总在一周的同一天升起。她还说也许不知道更好,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在天空的什么地方能等到月亮,那么月亮的露面迟早都是一种令人快活的惊喜。但是,我估计新月即使对那些深谙其升落时间表的人,它挂在天空也同样会令人惊奇。春天的到来与花潮的到来,也无不如此。我们看见一枚早到的报春花会欣喜不已,是由于我们对一年寒来暑往习以为常,知道迎春花应在三四月间而非十月间开放。我们还知道,苹果树的花开在果子之前而非之后,但是我们在五月的果园度过一个美好节日时并不会因为只见花不见果而减少欣喜。
同时,每逢大地回春,重温许多花卉的名字也许会有一份特殊的快活。这好比重读一本几乎忘掉的书。蒙田告诉我们,他是忘事佬儿,重读一本好书时总感觉是过去压根儿没有读过的存书。我自己的记忆也靠不住,跟筛子差不多。我读《哈姆莱特》和《匹克威克外传》,总觉得它们是新作家的作品,从印刷厂出来还油墨未干,它们的许多内容在一次阅读和另一次阅读之间会变得模糊不清。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记忆是一种苦恼,尤其你一心想把事情记得准确无误的话。不过这种情形只是在追求生活目标而非娱乐时才会有的。仅仅就贪图奢侈而论,坏记忆会夸夸其谈的东西倒不见得会比好记忆少多少。你要是有个坏记忆,不妨一遍又一遍阅读普鲁塔克和《一千零一夜》,读上一辈子。许多细端末节也许会粘在最坏的记忆里,正像羊群一只接一只挤过篱笆的空隙,树刺上不能不挂住几缕羊毛一样。但是,羊群本身挤过去了,伟大的作家挤过无所事事的记忆如同羊群穿过篱笆,留下的东西少而又少。
如果我们能把书忘记了,那么把月份以及月份过去后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忘掉也是很容易的。这会儿我跟自己说,我了解五月如同乘法表一样清楚,关于五月的花卉、花开的样子以及品级也不怕别人考一考。今天我敢肯定毛茛有五个花瓣(也许是六个花瓣?反正上周我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明年也许我就算不清花瓣有多少,不得不再温习一遍,当心别把毛莨与白屈菜搞混了。到那时,我会用一双陌生人的眼睛,再次把世界看作花园,对那五彩缤纷的田野惊讶得透不过气来。我会情不自禁地纳闷儿是科学还是无知,认定雨燕(那种黑色的鸟,比燕子大,与蜂鸟同属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