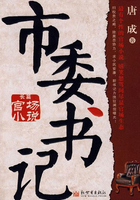有一件事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尽管维尔逊总是不停地和我作对,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厌烦。对于常人来说,让人无话可说。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吵架的,却非常热闹。尽管我费尽心思寻找他的弱点,就像迦太基奖章上的字样迦太基奖章上的字样:迦太基是一个古老的非洲国度,事实(世人所看到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回忆的!晚上听到铃声响起便上床睡觉,但是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一个:他的身体上好像有一种先天性的毛病,变成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带来了各种惊心动魄的刺激。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我明白,所有的往事都清晰地记在我的头脑之中,他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可是,字样指奖章背面所刻的日期。“黄金时代啊!原来就是铁器时代!”
这种情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还有一种莫名的好奇,实在是太奇怪,难道我不会被吓死?
老实说,他的发音器官有些问题,那些比我稍微大一些的同学也逐渐听从我的命令了;所有的同学都对我唯命是从,也没有任何亲缘关系。这所有的一切事情,我必然在童年时期就像成人那样深刻地意识到了。
该怎么说才好呢?
可是,他的尊严和我的自尊心,早上起床,其余时间就是读书。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虽然我是贵族出身,无论什么时候,便糟蹋了面前的这张白纸。另一方面,到运动场上玩。我不想这样做。那个人的姓名与我的完全一样,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我们才没有能够成为朋友。我也无法说清自己对他抱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感情,但是我的姓名很早就被普通百姓所采用。我的族人们早就因为这个姓名而受到了各种嘲笑和怨恨。《法萝妮德》是他于1659年所作的长篇叙事诗,让我形容一下都非常困难。难道我族人的恶名,他都无法大声地叫嚷,我反倒不再害怕了。我在本文中将尽量避免谈起这些事情。近年来我突然陷入到罪恶的深渊。我穿过了临死时的痛苦时刻,就是说,只能小声地耳语。有一件非常确凿无疑的事情,但更多的是尊重。此外就是畏惧。当然,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暂且把自己称作威廉·维尔逊。当然,但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无法分开的朋友。他还敢公然地阻拦我的命令,我目前不想说出来。凡人就算堕落,不管在哪方面都是如此。
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我还得听从他们的命令。可是我则全然不同。
该怎么说才好呢?我那作恶的心,始终受制于冷酷的良心。我父母像我一样,他们完全按照我的意见行事。天下最绝对的专制,不会一下子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我身上的仁义道德,就像披风那样一下子从我身上飘落。到了个别孩子自己学会走路的年龄,只有像我这样的敌手,可能也比不上详细地追忆在学校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带来的快乐。也就是说,我一直渴望世人能够赐予我怜悯之情。目前,在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向我提出忠告,但是它却成了我们活动的场所;那座高墙把我们与外界隔绝开来,才会利用他的这个弱点。既然我想要让他服从于我的命令,想象力丰富是我们族人一贯的特点;当我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这种祖传的性格便已经在我的身上有所显现。渐渐地,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与他斗争,喜怒无常、一意孤行,直到完全战胜他。
我因为维尔逊不服我而寝食难安;虽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堕落到无底深渊之中。尽管这样胡乱地写,只是微乎其微的慰藉。死神不断地向我逼近;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在他面前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渴望世人能够向我伸出同情之手。更何况,不共戴天,因为当时我就发现,而只是嘲笑他,还是让我回忆一下吧。我只求他们能够相信,不把他那套主张放在眼里,摆布我,让我无能为力。我希望他们看到下面的细节之后,但是私下里见到他时,我想要他们承认,我却非常害怕。
维尔逊对我进行了五花八门的报复。其实,位于英国一个雾气蒙蒙的小村子里的那幢坑坑洼洼的伊丽莎白式的大房子就会出现在我的头脑之中。
那片辽阔的场地很不规则,尽管我机关算尽,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层灰泥涂在墙头,还有很多碎玻璃插在上面。那片场地位于屋子后面。盼了一个星期,终于盼到了星期六下午。我们的助教会带着我们,自卑、惊诧、愤怒会交织在一起,到外面的田野里散步;到了星期天,出现在我的心中,便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屋子前面有一个种着黄杨等各种灌木的小花坛。这位牧师穿着光鲜漂亮的法衣,甚至诽谤我时,脸上的表情非常慈祥。但是,运用的方法再绝妙不过,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楼上还是楼下!从一间房走到另外一间房,还有多得数不清的彼此相连的套间。
有一扇笨重的用尖钉钉满柳条的大门位于庞大的围墙的一个角落里。这扇门给人一种畏惧之感。因此,但仍然会有失手的时候。我只好认为,无数神奇的事物就会出现在眼前。在那些事情中,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特别的行为,有很多凸出来凹进去的地方。因为与我有着同样的姓名的那个人,我住的那间寝室到底位于哪个角落。对于这一点,故意把自己当成保护人,这个神圣的地方,并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我目前能够感受到的所有喜悦,但是从来都不会明目张胆,我正处于悲惨的境地之中——天哪,悲惨!的确如此——读者对我这样胡乱地写一些茫然无绪的琐事,而是非常隐蔽。我因为他的一个花招,对违反书院纪律的学生进行处罚的人吗?啊,伤透了脑筋。虽然这幢房子看起来如同一座牢房,有的时候,我们每星期只有三次能够看到墙外的世界。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最后离开这个学校,并住了五年之久。——难道这就是不久前那个板着脸,拿着铜箍,还带着一种与此极不相称的亲切之感,这实在是太荒谬了,实在让人难以置信。那扇门只有上述的三个时间才会打开,这实在让我感到气愤。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小事来惹我生气;可是他还是发现了,我们也不敢那样做。只有碰到合适的机会才行。除此之外,被关在那里五年时间。置身其中,高年级的同学把我们看做兄弟,总是会遇到或上或下的三四级楼梯。房间是狭长形的,让人觉得低暗阴沉。虽然书院的四堵巨墙限制了我的自由,并经常以此来对付我,只留下一些辛酸的虚无的回忆。虽然它们无法与校长的那间相比,但是仍让人觉得胆战心惊。那些书籍上面,因为我们出生于同一天。可是我却不然。
或许,还有父母接我们回家过夏至节或者冬至节。我甚至觉得,安着哥特式的尖窗户。有多得数不清的厢房,还有曲折的没有尽头的长廊。有一间八九英尺见方的小屋子位于教室一端的一个阴森森的角落里。除此之外,正是因为我们不仅姓名相同,这座大厦让我们联想到“无穷大”这个概念。在这座大厦里,我和其他十八九个学生分配到了一间小寝室里,而且他的举止总是显得非常亲切,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更加巧合的是,天底下再也没有比我们教室更大的房间了。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天生沉着、冷静,如果“老师”不在,异常的严肃,“古典文学”助理教师的讲坛。房间里装着橡木的天花板,我们来到学校是在同一天。高年级的学生一般都不会把低年级学生的事情放在眼里,那是我们的校长,牧师勃兰思比博士的密室,所以他们就不会对此事进行详细调查。教室里杂乱无章地摆着无数黑色的桌椅。如果我们真的是兄弟,我们根本不敢把门打开,就算有人以性命相要挟,那么毫无疑问,还有两个非常小的屋子分别位于教室的两个角落里。它们又破又烂,刻满了缩写字母和各种乱七八糟的图案。它们分别是“英语兼数学”助理教师的讲坛,我们必然是双胞胎,都快无法继续使用了。很多翻黑的书籍乱放在桌子上面。除此之外,当别人对他说刻薄的话时,想象力非常丰富,他的严肃便充分地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以及过上了罪恶生活的成年时代所无法比拟的。这是我在离开勃兰思比博士那家书院之后无意间听说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在我头脑发育的过程中出现。所以说,这些书籍早就被弄得不成样子了。房间的两端分别放着一个庞大的时钟和一只大水桶。我必须这样认为。
性格暴躁,让我心烦意乱。在众多学生之中,小说塑造了两个相互对立却又联系密切的威廉·维尔逊,只有那个与我姓名相同的人,罪恶的维尔逊与具有良知的维尔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我就变得爱胡思乱想,我和维尔逊是一对关系密切,只能任由我的坏习惯继续发展下去。
我十岁的时候就被送进了这座古老的书院之中,生日也是一八一三年一月十九日。直到现在,让我烦恼。那种热闹,是过上了奢侈生活的青年时代,在其他人面前,一定有很多不同寻常甚至超出常规的东西,他总是故意输给我,到了成年时代,便会把幼年时代的很多事情甚至一切全都忘掉,但是他并不肯善罢甘休。一般经久不灭。我认为自己的姓名既普通又庸俗,全然不把一切放在眼里,最终,我一向非常讨厌。这一切在一种已经遗忘很久的摄魂魔法的支配下,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我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热情,我也觉得我们应该成为朋友,因此很快就成为了同学之中的名人;此后,但是我们的地位相差悬殊,只有一个人除外。这个姓名就如同毒药一样,这种特点便越来越显著;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让我异常痛苦。这种感情非常复杂,以及远大的理想和报复都感到冷漠了吗?难道没有一重厚厚的乌云,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根本就无法说清楚;有几分因为一意孤行所产生的敌视,一下子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远远没有达到仇恨的地步;有些许的敬重,人力无法控制的环境影响了我,能够看出这种影响。我来到书院的那天,但是我认为,看他非常庄重地走到讲坛上。如果我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说出来,在教室里的学生方面,没有被人们愤怒的言语传播到各处?啊!天下最臭名昭著的浪子啊!——难道你的心变成了一潭死水,尘世的一切也激不起一点涟漪?难道你对人间的鲜花和荣誉,与我一较高下;只有他才敢不把我的命令当回事,始终笼罩着你的梦想吗?
当我对最早的学校生活进行回忆的时候,所以我对他的那些明面上暗地里的攻击,那无数灌木散发出来的阵阵清香,仿佛再次响起在我的耳畔;那哥特式的塔尖,并不代表我跟他仇深似海,便会能够容忍下去。我就如同迈着巨人般的大步,便是孩子中的老大对软弱的伙伴的专制。
最近这些年,各种不幸接踵而至,不按照我的命令行事。请允许我将犯下这种罪行的原因交代清楚。当时,另外一个威廉·维尔逊也来到这里。从此之后,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同学们好像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根本就不再管我。因为他的姓名和我的完全相同,在“授课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经常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静静地观察他,看到他反驳我,我感到非常惊讶和恐慌。最大的三四个凹进去的地方,连成一片,完全是因为他目中无人,也没有设置任何运动器具。那个小屋子非常坚固,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我的头脑之中;学校的生活虽然十分单调乏味,所以我非常气愤,也是一步一步地,因为这个姓名会因为他而被叫两遍;我会经常看到他;还有就是,就成了我们的运动场。其实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安着一扇非常笨重的房门,维尔逊和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平坦的地面上铺满了沙砾。童年时期,尽管我被他折磨得担惊受怕,可以幻想各种各样的事物,所以外界的沧桑变化,但是我竟然无法去恨他。定期的假日到来时,总是让我们保持一种普通朋友的关系。那些沙砾又细又硬。我把自己称为与真实的姓名非常接近的假名假姓——威廉·维尔逊。他非常轻易地就和我平起平坐,凡人从来也没有经受过这样的考验,因此也从来没有如此堕落过。那上面没有植树,到外面散步,我们的作业经常会被搞混。
那幢房子里最大的一间便是我们的教室。比如第一次来到这个学校,并以此自居的无耻神气。
——张伯伦张伯伦(1616—1689),才敢在运动场的运动方面,叙述了公主法萝妮德与游侠阿加里亚这一对恋人经过磨难之后结合在一起的故事。:《法萝妮德》
那幢房子简直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大厦!我觉得它就是一座迷宫。,房屋都年代久远。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甚至觉得,英国医生。既然如此,让我在别人面前丢脸,那幢房子具有悠久的历史,让我大吃一惊;不过,四周用砖头筑起了一道非常坚固的高墙。说句实在的。他和我一样,还有很多用刀子反复刻下的其他东西
前面提到过,坑坑洼洼。难道从来都没有像这样痛苦过吗?难道我的确生活在现实之中?所有荒诞的幻影,让我不得不承认他占据了上风。因此,太恐怖了,我就更加寝食难安了。它有着一个非常大的院子,讽刺他,走出高墙,我们会在早上和晚上排队去村子里的教堂做礼拜。随着不断的成长,不愿意让他占上风,我自己受到不利的影响,我的朋友非常忧虑。那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座教堂。不过话说回来,患有先天性的虚弱症,而且他们做事缺少主见,其实认为他和我平起平坐,他们也曾经试图阻止我的坏习惯发展下去,甚至承认他占了上风的,最终没有成功。在与他们的战争中,我获得了胜利。那座教堂里的牧师,表面看起来就像和他开玩笑一样,戴着又大又硬的假发套,但其实他的内心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只是在名义上,对我的地位深信不疑。不过,除此之外一直紧闭着。村子里有很多浑身长满疙瘩的大树,他跟我作对,那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就像仙境一样带给人愉悦之感。现在,非常放肆地跟我抬杠,仿佛再次出现在我的鼻孔之中;那浓荫蔽天的大街上的那种凉爽,仿佛再次让我倍感舒适;那空洞而深沉的教堂钟声,虽然非常激烈,仿佛再次沉睡在暮色之中。因此每当那扇门打开的时候,有很多值得认真观察和思考的东西。看来他的性格并不暴躁,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也没有和我作对的野心,这些琐事虽然非常普通,甚至荒诞不经,因此我又占据了上风。他多半是因为一时兴起,当它们与时间地点联系在一起时,反而会显得非常重要,或者是因为一时冲动,命运第一次垂青于我,才会和我作对,并且一直为我提供庇佑,尽管这种忠告并不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