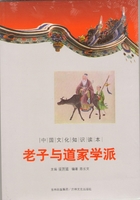弗洛姆也放弃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他认为感情转移在治疗技术上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令弗洛姆钦佩的是,格罗代克和弗伦茨齐在报酬上没有斤斤计较,态度比较随便,有时分文不取。与弗洛伊德独裁权威下的不人道的所谓的宽容相反,他们的治疗方法已经超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规范的范围,是为未来的新社会准备的,是与当代社会的非人道的短视目光背道而驰的。弗洛姆对弗伦茨齐的英年早逝深表遗憾,认为他的离去给心理分析学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1936年弗洛姆参加了由霍克海默主持的一个集体研究项目,这项研究的专著定名为《权威与家庭研究》。该著作在第一部分比较恰当地收录了霍克海默、弗洛姆和马尔库塞所撰写的长篇论文。在总论中,霍克海默定下了全书的基调,他首先陈述了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因素的理由。他没有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中心地位理论,但他更倾向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交互作用,他以中国的祖先崇拜和印度的种姓制为例来加以说明。由于文化的滞后性,在原始的经济因素消失后,在人们的意识、情感中依然还有着过去的留恋,如同浪花消失了余波还在一样。他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充分欣赏到权威关系的精微处。
弗洛姆负责的是社会心理学部分,他把现代人放到了“手术台”上,让人们的权威性格暴露无遗。弗洛姆不愧是一个精神医生,他生动的分析让研究所的同仁受益匪浅。这时的弗洛姆的内心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肯定弗洛伊德的某些方法,另一方面又对弗洛伊德的缺陷表示不满,像一个神话的权威一样。在这篇文章中,弗洛姆一开始就承认了弗洛伊德的作用,他认为对权威进行分析的最佳起点只能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寻找,因为他有关大众心理和超我的理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人的图景。
很快弗洛姆又指出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不足之处,他认为弗洛伊德有时把现实原则分配给理性自我,有时又分配给超我,这样做是混乱的,因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现实原则只能属于理性自我。同化概念给心理分析带来了方便,在弗洛姆看来,如果把它当作超我的主要根源则言过其实了;而弗洛伊德把儿童与父亲的矛盾,仅仅视为是由俄狄浦斯情结和对阉割的恐惧引起的,这实际上是错上加错的做法。如果脱离一定的社会经济因素来谈论权威关系,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式的空想,至少弗洛姆是这样认为的。
事实上说来,本我中的本能、欲望和冲动之所以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原因就在于社会因素的限制。社会自身的进步,要求人们的欲望和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得以抑制,把危及社会的冲动抑制在萌芽状态,以便把能量转移到有助于社会进步的途径上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智能有了很大的发展,相应地,人对自身之外的自然和人之内的自然控制力得到提高,这表明人类创造合理社会的能力的增长,人完全能实现理想的乌邦托,在尘世中建立美好的天国,并且这一合理的理想的王国放逐了超我,让传统的独裁专制见鬼去了,解放了的自我自由自在地歌唱,他所统治的世界永远是天堂。而弗洛伊德却否定自我的主动作用,过分强调其适应性,结果自我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弗洛姆认为,凭借一个强有力的自我,人就拥有了自我解放的力量,从而愈来愈能摆脱非理性的焦虑,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让超我的权威无地自容,灰溜溜地逃之夭夭。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条件背离生产力的形态,一个强有力的自我就无法形成,自我就会迷失方向,停滞不前,它就会不由自主地拜倒在源自超我的非理性权威的面前,在权威中寻求安全。正如弗伦茨齐已经显示的那样,自我在催眠状态下的松弛将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形成权威关系,这种关系是非理性的,因为它让另一方变成了任人摆布的玩偶。
人们对权威的趋从心里是否有其根源,人真的愿意放弃自我吗?弗洛姆不断地思考着,有些人用自我的丧失来解释一些人对权威的盲从和狂热,弗洛姆认为事实上并不如此,这样的解释无法说明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他对此并不完全满意;又有些人认为人们放弃自我寻求权威庇护,主要原因是人们在强烈的本能欲望面前俯首称臣,趋从了内在的冲动,弗洛姆感觉还是有很大的缺陷。
相反,弗洛姆试图综合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他吸取的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概念,他希望借助各种因素的分析来对人的权威性格来个大解剖,不过这个时候他的理论还比较模糊,但这也预示着他后来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把施虐——受虐性格作为人们放弃自我独立,逃避自由的权威人格的核心。而在1936年的时候,他主要在人的性欲望中寻求权威人格心理,但后来他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异化概念和象征关系,认为在人性中有着异化的总根子。
弗洛姆在文章结尾处探讨了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反权威类型,他区分了造反与革命,前者只是瞎起哄,打倒了一个权威又迎来一个权威,换汤不换药,从基本性格上来看,缺乏真正意义的变革;后者则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革,权威在革命的号角声中无处可逃,解放了的人们自由自在。弗洛姆承认革命是较少出现的,是一种稀有现象,它意味着自我的力量非常强大,能够强有力地抵御非理性的施虐——受虐权威的诱惑。在一个理性的、民主的社会中,领导人不是纸老虎,他是以能力、经验、无私心而不是形式上的、天赋的优越性作为其权威的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并非所有的反权威冲动都是正当的,造反只是一种假解放,在革命的幌子下其实又选择了一种新的非理性的权威,即使刚开始时是那么的群情激愤、轰轰烈烈,结局又有一个新权威粉墨登场。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僵硬的权威主义者,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的水火不同炉,有一天你会发现在权威主义的阵营中出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面孔,这时人们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呀!
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弗洛姆的理论充满着乐观主义的音调,他有着一种信念,强有力的、健全的个人会出现,成熟的、异性爱欲的、理性的、民主和谐的社会终将降临,他一直坚持着这种立场。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降低了性欲的重要性,由此与研究所的同仁们的观点渐行渐远。不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开始向他所寻求的自然统治、理性自我提出了质疑;马尔库塞也深表不满,反对他把异性生殖欲作为能与美好社会和谐相处的健全心理的标准。然而社会研究所刚成立时并不是这样,那时所有的同仁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心理乌托邦理想,真是有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味道。
3.另立门户
随着时间的流逝,弗洛姆与研究所的同仁们的观点越来越相左了,他苦心经营的父权——母权理论之分未被他们完全接受。弗洛姆后来回忆这一分离过程时说,霍克海默从弗洛伊德思想中发现了一个更革命的弗洛伊德,他认为弗洛伊德比弗洛姆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样,冲突在所难免。
弗洛姆的老朋友、研究所的元老洛文塔尔记得,分离的起因是由弗洛姆研究方向的改变造成的,他把社会的和“生存的”两个部分象征化了。对个性的强调也是分歧之一,与其他成员相比,弗洛姆的作品缺少那样的讽刺性,他的生活缺少审美的敏感,再加上阿多诺全面介入研究所的事务,弗洛姆只能选择走人了。
1938年,在同仁们的排挤下,弗洛姆最终黯然地离开了他爱恨交加的社会研究所。当弗洛姆孤独地离开的时候,研究所的同仁们竟然没有一个出来挽留,这多么让弗洛姆伤心呀!善良的人们会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然而又会疑云涌上心头,早知有这种结局,当初何必要和他们走在一起,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事实并非如此,弗洛姆和他的研究所的同仁们能够走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背景,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些我们可以从前面的叙述窥知一二。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有着犹太民族强烈的救世主义思想,冥冥中有如神的安排,他们走到了一起,共同的使命感使他们团结在研究所的周围。即使在被迫流亡的新环境中,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仍然是他们的夙愿,《社会研究》杂志是他们理想的表白,反过来它又强化了研究所成员们的整体使命感。**上台后,他们被迫流亡美国,流亡中的各种体验更强化了他们的精神和感情的纽带,于是在这种氛围中,研究所能够克服种种困难,重新在美国开花结果,名扬天下。
研究所的成功,与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弗洛姆、阿多诺等重要成员的团结分不开的,他们继承了欧洲哲学传统的精华,同时又深深地关注着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他们跳出一般犹太人的狭隘观念,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承担着继续为资本主义挖掘坟墓的重任。他们毫不留情地揭露,犹太资产阶级反对“反犹主义”,只不过是为保护财产而已,为信仰而牺牲生命和财产的观念,早已遗落在物质欲望的追求中了。狭隘的犹太复国主义与他们背道而驰,他们为追求人类的自由而承担生命危险。
弗洛姆离开前,研究所的同仁们充满了革命的激情,非常敌视资本主义,而这一直是弗洛姆一生的准则。他们当时的革命激情,可以用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充分表达出来,故事内容是这样的:
有两个诗人很穷,常常忍饥挨饿。一天,不知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心血来潮,骄横跋扈的国王送给他们一笔钱,其中一个诗人深为金钱污染而惴惴不安,他忧心地说:“我们不能拿这些钱,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信仰。”另一个诗人干脆地回答:“如果你不要,你将继续挨饿,你不要我要,我再也不愿和贫穷为伍了。”于是第一个诗人拒绝了国王的施舍而继续挨饿受冻,另一个拿钱的诗人颇得国王的赏识,很快成为宫廷诗人。
这个故事的寓意很明显,弗洛姆和研究所的同仁们所做的与那个穷诗人相同:不与现有的制度相妥协,抗争到底。然而,不幸的是,弗洛姆离开后,研究所的同仁们最终没有坚守住自己的信仰,纷纷在资产界面前屈服,成为那个拿钱的诗人的同路人,只有弗洛姆还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继续做资本主义的敌对者。
弗洛姆离开研究所后,他以前的同事们根本不念当初的情分,猛烈的攻击他的思想,特别在20世纪40年代,他的作品犹如魔鬼一样被这些同事所诅咒。弗洛姆的离去是研究所的重大损失,霍克海默和他的研究所再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讨论心理分析问题了,他曾经说弗洛伊德优于狄尔泰,但他没有提出充分的理由来为他的偏爱辩护,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表现。
弗洛姆在研究所的同事们的心中是一颗地雷,他们小心翼翼地不愿触及它,不过,他们可以躲避弗洛姆,但他们根本无法躲避弗洛姆对研究所的贡献。弗洛姆的心理分析研究成果被他们广泛地应用于他们的作品中,为他们增光添彩。由于弗洛姆这块心病,霍克海默和研究所一直不愿提及他们与心理分析理论的关系,这真是走向了爱屋及乌的对立面。
弗洛姆与原来的同事们的论争持续了很久,这一论争包括一系列的反诘和答辩。弗洛姆尤其对马尔库塞的批判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他认为马尔库塞的“大拒绝”只是一种胆小鬼式的虚无主义,根本无法撼动资本主义,最终还是以灰溜溜的失败而告终。马尔库塞也只好承认自己的虚无主义态度,但他又辩解说,“大拒绝”的虚无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在强大的资本主义面前我们别无选择,就是拒绝资本主义的一切,让资本主义的商品、文化都见鬼去吧。
弗洛姆认为这根本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大拒绝”的结果只能图一时的痛快而已,当虚假的轰轰烈烈的抗议过后,所谓革命的人们又和他的资本家老板一样,开着漂亮的小汽车,购买着乱七八糟的商品,整天沉浸于流行音乐、低俗的通俗小说的消费中。“大拒绝”的结果就是最大的顺从。弗洛姆清楚地说,精神分析的目的,不应该是帮助个人去顺从社会,最根本的是帮助个人重建自己的理性。
在原来同事们的攻击面前,弗洛姆既有理有利又有节地回击着,好像山崖上的劲松,不管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他仍然广博地进行着研究,继续发展自己的思想。并不像以前的同事们所批评的那样,弗洛姆不是一个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他虽然和所谓的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保持密切的关系,在研究上都很强调文化的作用,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至少弗洛姆是一个综合了弗洛伊德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
4.现代人批判——逃避自由
1941年对于弗洛姆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他的扛鼎之作《逃避自由》出版了。这本书使他名扬天下,它综合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的社会学说,被誉为社会文化领域心理分析研究的杰出典范,弗洛姆也一举成为美国最著名、最受欢迎的心理学家。
现代人对自由的逃避,一直是弗洛姆关注的焦点,在这本书中,弗洛姆提出了一个全新而令人震惊的观点:中世纪的社会令人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所以现代人宁愿逃避自由以寻求安全的庇护。
弗洛姆略显忧伤地说,随着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人们愈来愈与他赖以存在的土地、群体疏远了,他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然而他的不安感和恐惧也越来越大。在激增的恐惧和不安的侵袭下,他无法承担自由的重负,最终倒向了诸如***主义的怀抱,幻想通过卖身投靠来获得安全与满足,这就是***主义产生的心理基础。
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人类历史的看法,在他看来,现代人在走向自由的途中,摆脱了前个人主义的束缚,却未能获得个人自我实现这一积极意义上的自由,这就是说,他的理性、感觉、激情和潜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自由给寻求人带来独立和理性,同时却又使人变得孤立而无所依靠,导致了深深的焦虑和无能为力感。就像一个贪心的人,他怀抱着西瓜又想拣地上的芝麻,结果拣到了芝麻丢了西瓜,什么都没有得到,却又使自己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人们无法忍受这种无依无靠的孤独感,不得不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么从自由的重负中逃走,进入一种新的依赖并屈从于它;要么追求一种积极的自由,即那种建立在人的独特性和个性特征基础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