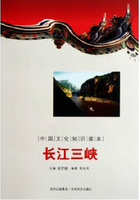有天早晨,我划着皮船出海,准备从科得角的法尔毛斯划35英里到南塔基岛,中途在玛莎葡萄园停靠一下。我感觉自己滴水不漏,浮力甚大,轻便易行,船上有睡袋,还有供四天食用的食物。那是一个可爱的早晨,但我的心态早已经处在灿烂的状态下了,我知道为了划船到达南塔基,并在中途停靠露营,我可能得侵入别人的领地,可能要违法。
对我来说,最好的旅行总是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侵入行为。这样的风险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召唤。销售冒险似乎是旅行业的一个主题,而很多次旅行都成为了战利品。有钱的人花很多钱让人用绳子把自己拉上珠峰,或者划着筏子在恒河里进行白水漂流,或者去战乱频仍的卢旺达冒死跟猩猩一起拍照片。在这类旅行当中可以找到的艰难因素要么为人所忽略,要么就是根本不予理睬。尽管如此,风险因素依然很高,这些冒险的旅游者经常会受伤,甚至死在路上。
冒险之旅似乎总暗示着去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但是,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冒险可能更加惊险,因为没有哪个地方比靠近家乡的某个地方更吓人,因为人们一再警告不要去那些地方。你可以把一些无知的意见抛在一边——“非洲很危险!”或“印度很肮脏!”——但是,如果有你十分熟悉的一个人谈到靠近家乡的某个地方时说“不要去那里”,听起来那些话里面就含有某种经验教训的意思。但是,这一般来说不会让我打退堂鼓。重要的是要想出去那里的方法,比如1853年,理查德·伯顿爵士就去学了阿拉伯方言,蓄了胡须,把皮肤弄黑,并改名为墨萨·阿布杜拉,说他的职业是“托钵僧”,为的是让自己作为土生穆斯林的麦加朝圣行为不被人看做是异教徒的举动。
对于科得角四周的海洋环境而发出的种种警告特别吓人。但是,如果你接受人们所有的劝告,并听从人们发出的种种警告,因为那些怪兽制造者发出的种种警告而屈服,那你哪里也去不成。很多发出警告的人都不能替你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他们把自己的担心强加在你的头上,当他们说家乡附近的某个名声不佳的地方时,他们有可能是故意欺侮你的。如果是附近的某种可怕的事情,那就没有比它更可怕的事情了。隐约熟悉的东西可能比完全不知道的东西更为可怕,因为有很多目击证人可以提供各色各样的细节来,那是具体可感的一些致命细节最可怕的确定,潜伏在你心中的一个念头是,如果你去那里,要么会死,要么会失望到极点。
因为有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因此,这样的旅行又是十分刺激的,越是不应该去做的事情越是要去做,这会让人产生渴望。人人都告诉我不要划船去南塔基岛,某某人的兄弟就喜欢划船,也去了,但结果如何如何。我听他们说完,然后,到了那天早晨,天不亮我就起床,听听那天的科得角最新的天气预报,还有那个岛的天气预报,接着就准备好皮船,开始我决意要进行的越海划船行动。
大海也是一个地方,而且大海也不是空无一物的地方。大海里面包含明确的地域,有浅滩,有岩石,有浮标,有铁罐,有纺锤形浮标——还有露出海面的遇难船只,跟教堂尖顶一样耸立海面,威严可怕,也有裸露在外的唱诗班一样的杂物。在西安尼斯波特防波堤上面南而坐的钓鱼人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水,可是,在南塔基海湾,海图上的诸多细节跟附近的西安尼斯波特区不相上下。这里不仅仅是众多船难的发生地,而且还有众多难以忘记和声音宏亮的地名。从法尔毛斯出发,横过葡萄园,你必须经过“人帝沙洲”、“篱栅”(很长的一段狭窄的沙洲),还有“南瓜草地”,如果你从那里到艾德加镇,那你就必须经过许多有名字的岩石。海流的速度和方向都在不断变化,那是另一个必须认真考虑的事情,水深从几英寸到一百多英尺不等。但是,如果因为大海是一个地方,因此就很完全,也很好客,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梭罗的《科得角》一书当中,他写道:“大海是一片荒原,比孟加拉的丛林还要野,里面有很多怪兽。”
天气恶劣的时候,在科得角海岸你是看不见葡萄园的,哪怕在最晴朗的日子里,你也看不到南塔基。对划船者提出的挑战不仅仅是毫无遮拦的海水,还有湍急和不断改变方向的水流,常年不断的狂风,散布于各地的沙洲,这样的沙洲会激起滔天巨浪。南塔基海湾有吞没海船的悠久历史,是海洋当中任何一片水域当中最拥挤的坟场之一。19世纪的时候,经常看到有捕鲸船离开南塔基海湾,在世界各地航行两年多时间,跨过南部的海洋,环绕海角,穿过咆哮西风带,结果眼看着就要到达海港了,却在南塔基海湾的岩石或浅滩上裂成碎片。
众人的警告反倒令我兴奋不已。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想划过海湾,划着自己的船,越过惊涛骇浪直奔南塔基,要利用航位推测法安然无恙地到达那里。我备好了一张海图,一个指南针,根据自己估计的船速调整航向。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南塔基远在地平线以下的地方,到了晚上,从葡萄园最近的地方看去,只有它的“流光”——港口灯光在天空中闪出的晕轮才能指引方向。
每当我谈到想去那边划船的时候,人们总是想办法让我推迟计划。他们是一些吃水5英尺的大船上的水手,或者是一些快艇手,从来都没有在看不见陆地的海上航行过,或者是一些旅游者和喜欢搞晚会的人,他们只是从西安尼斯渡口坐船经过漫长和寒冷的摆渡之行才了解海上的航线的。
我的梦想是划着小船在汪洋大海上渡过荒原,这也是我得到童子军最高军衔后的梦想(当时我在第24军)。一个人在外国旅行过足够长的时间,在拥挤和完全温顺的一个地方旅行过,坐飞机在无聊和得不到睡眠的旅途中进行漫长的旅行,在经历过别的旅行者闹哄哄的干扰之后,他就梦想有这样的一次旅行。我最近去过西藏、波利尼西亚,苏格兰南部,还有新西兰南部的岛屿,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单独去的。旅游者已经挤满了最偏远的地区,深入到了世界上最蛮荒的部分。有一篇文章是我情愿不去写的,那就是关于旅游者的分布情况,如果写出来,这篇文章的标题可能就是“他们无处不在”。
他们不在马斯克格特海峡。我知道自己一路上不会碰到任何人。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任何人做过横跨马斯克格特海峡的壮举,甚至也没有听说有任何人愿意这么尝试一下。针对小船的警告经常有。《艾尔德里支潮汐及航行表》显示,马斯克格特海峡的某些地方有四节半的海流,如果有大风和潮汐,流速将比这个速度大得多。总体来说,在任何一个外岛上露营是违法行为。那是危险的,不合法的,有勇无谋的,被禁止的。
这就是猫薄荷,我想。谁不愿意划着小船去南塔基呢?
我从法尔毛斯东边的绿塘海港出发,划着我的可折叠式克莱普皮船,这种船跟因纽特人划的皮船最为接近。
防波堤上有一个亚洲男子和妇女在捕鱼。也许为了逗那个女的开心,那个男子对我大喊:“你永远也划不过去的!”
我拿这话掂量了一下,但继续朝海湾的外围划去。克莱普皮船有很多好处,其中一个是它特别适合于海上航行,特别稳定,重量很轻,储藏空间很大,而且易于搬运——可以在约一刻钟内拆卸完毕,然后装进两只袋子里。翻船不太容易,而且假如翻了,你可以再爬进去,这在其他的皮船当中都是不容易实现的功能。
那是9月初最漂亮的一个早晨,正好是劳工节之后,当时,科得角看上去光线明亮,空无一人——没有大量车流,没有多少行人,没有游泳的人,水面上也没有钓鱼的船。天空明澈,风很小;因为有一层低低的薄雾,葡萄园看得不是很清楚。我准备直奔东浪灯塔,在海岸边继续划几英里,在橡树崖下的海滩上吃午餐。下午的计划取决于风力和天气情况,但总体来说前景不错。
跨过南塔基海湾是科得角的水手们的第一道心理障碍,越过南塔基海湾之前,我曾在这个海湾里划过船,而且也划过了整个海湾,但是,用单桨划船只是这三者当中最简单的一种。海湾对任何一种规模的船只都有可能产生危险。1992年8月20号,我从绿塘划向橡树崖,看见一只定期客轮在东浪处抛锚。我朝它划过去,因为潮水在上涨,而且朝东边流,给人一个错觉,以为那条船是在慢慢朝西开。事实上,我是被那条抛锚的客轮拖着走的。接近客轮之后,我看到主甲板跟20层的楼房一样高,划过其船尾时,我看到伊丽莎白女王二号一南安普顿的字样。旅客被运到了橡树崖的岸上,离船有一英里半,都是用捕鲸船运过去的。我划到舷侧门处,跟一名助手聊起来。
“我从来没有在这里见过伊丽莎白女王二号。”
“我们每隔几年才来这里一趟。”
“你们准备开往哪里?”
“纽约市。我们今晚就出发。”
“我刚刚从科得角划过来的,过了好几个沙洲。我知道那边还有好多。这么大一条船怎么开过去?”
“没有问题。我们总能开过去的。”
当天晚上,伊丽莎白女王二号在海湾西侧撞上了一块没有标记出来的巨石,就是靠近母猪岩的那几块石头,造成船体数百万美元的损失。旅客都从客轮上运下来,然后运到了纽贝福德,再用汽车送到纽约去。修理客轮花了一年时间,之后才重新投入使用。
潮汐也可能会构成问题。我靠航位推测法出发的那天早晨,潮汐就不利于我——我知道情形会是那样的,因为当天下午我需要潮汐帮我的忙。潮流会造成最为奇特的效果。划出绿塘湾一英里后,出现了一个潮激浪,一大片尖钉一般的白浪将我吸往大浪跟前,让我无法留在平静水域内。这时候,能做的事情就是坐直身体。我从浪中通过,过不久之后,我发现已经离海岸很远了,更靠近西浪口而不是东浪口(这是葡萄园港口不同的两个分支,各支都有一大片激浪区)。我冲着急流划,感觉自己是在逆流而上,离开科得角约一个半小时后,我就到了葡萄园海岸。再过三十分钟后,我就躺在橡树崖下的海滩上了,一边喝着中国茶,一边吃奶酪三明治。
在这里,作为餐后读书活动,我看了看《潮汐与导航表》,发现一切都有利于我:潮汐刚刚返回,我会得到全力合作的潮汐的帮助,引导我到达爱德加镇和卡塔玛海湾。如果我躲开了巡逻队,并在查帕奎迪克岛南端的海滩上露营,第二天早上便会有仁爱有加的潮流带我直达南塔基湾。也就是说,它会带我安全地朝东北方向前进。但是,这样的潮汐并不会仁慈个没完。如果我延误了时机,或者划行的速度不够快,我会在潮流到上午返回时被冲进大西洋。
人人都跟我提到的最担心的事情是马斯克格特海峡,那是一种丰富的排水系统,能够将任何一个船只冲进大西洋里。没有船胆敢这么做。他们怎么做得到呢?如果水流没有冲到你,沙洲和岩石也一定会逮住你。但是,皮船的吃水才几个英寸。任何人都明白,这个海峡的危险必须跟它的优势相提并论,那只是8英里的一段跨海距离,离最近的陆地也就是这么长,那就是没有人烟的马斯克格特岛,如果天气碰巧变坏,我可以勉强违法登上去休息一阵子。引诱我横跨这个海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见到过的,讲过话的人都没有这么做过,也没有听说有谁做过。这意味着我也许是第一个靠双臂划船独自一个完成跨海行动的非印第安人。我也许会发现,这样的跨海行动一点也不危险。
旅行者从骨子里来说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乐观主义精神划了整整一下午的,一直往南划向爱德加镇。这是世界上最可爱,也最暖和的港口之一,这里有整齐的市镇,全都是色调明快、稍显傲慢的房子以及砖墙和林阴浓郁的街道。海港对岸就是查帕奎迪克,那里有低矮的林地和沙洲以及昂贵的人看上去十分隐密的房子,大部分是纽约人一年四季神出鬼没的休息之所。
我把皮船划到一处公用着陆处,然后走进爱德加镇去买些啤酒,确认明天的天气预报(晴天,有太阳,散云,风很小,流速10到15节)。我考虑了一下找一家旅馆过夜的事情,但是,那会使我的旅行复杂起来。我希望从海岸上最有利的位置尽早出发,因此,我就按事先设计好的露营地准备露营:瓦斯克波因特,就在岛的东南角上。
因此,尽管我一直划了将近七个多小时,但还是回到了皮船上,继续划了一个小时到达对面的卡塔玛湾。太阳正在西沉,气温慢慢降下来了。等我到达那个沙嘴时,已经是天色微暗,稍露寒意了。我累得不行,装满了东西的皮船我已经没有力气搬上岸了。我坐了下来休息一会儿,看着一些捞牡蛎的人紧张兮兮地在那里发出哗哗的声音,之后,我捞起一大把粘乎乎的海草铺在沙地上,再把皮船通过这道滑溜溜的斜坡道拖上沙洲。
一些四轮驱动的交通工具——打鱼人——正在离开海滩,有一辆茶色的“野马”牌汽车,车门上写着巡逻骑兵几个字。我在沙洲上随意走动,一直到日落时分,然后,我把皮船侧过来,铺开地膜和睡袋。我喝了一杯啤酒,在布满星星但没有月亮的黑暗中吃了晚餐。海浪单调地冲刷着沙滩,拍打着沙滩,发出像是有人在叹息的声音。我希望自己处在看不见的状态下,因此没有点堆火。回去睡觉之前,我去海边上查看了一下,用望远镜看了看东边和东南方向,因此看到了南塔基港上空的光晕。没有陆地,但有确切的灯光,跟雷电微暗的闪动和大海远处的火光闪耀出来的暗淡光芒一样。
之后,我躺在自己的睡袋里,轻轻吟咏:
啊上帝,请让吃饱了星星的
古老的天空之毯更小一点吧,
我好围在身边睡个安稳觉。
夜里我经常醒来,听海浪,听风在海草间吹过,在沙粒间吹过——我感觉自己像个原始人,跟原始人一样很容易就被弄走了,跟他一样毫无遮拦,跟他一样易于受到攻击。我躺在那里,就跟一条狗蹲在地毯上一样。我暴露在外,但是,我自在一个空旷之地,没有挡住任何人的道。除开渔民之外,没有人会来这里,但渔民要等太阳出来以后才来这里。到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带的食物不错,我躺在贵重的睡袋里,靠在我那不会沉没的皮船旁边,9月初的黎明破晓时,我一点也没有感觉自己是在过苦日子。这就是一种古怪的豪华奢侈:我感觉非常舒服,我一个人呆在这里,我成功地踏上了禁地。
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如同庞大的一堆红彤彤的东西从海里喷出来,它不停地朝各个方向吐出炫耀的光芒,将红色铺呈在海面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就如同一枚挤破的血橘一样。如同卷作一团的动物一样的一块云很快挡住了明亮的光线,大海变成了脱脂乳一样的蓝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