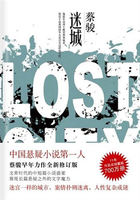于之恒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回到省城金沙的,只依稀记得一路上不少人向自己投来的惊疑的眼光。是呀,在这种雨天,一个人背着一个包既不打伞也不穿雨衣,就那么踽踽而行,一身的泥、一身的水,人长得漂亮,举止又反常,别人还以为是个神经病呢。
回到宿舍,已经是黄昏。
陈柏宏见了于之恒,如同见了鬼魅,惊叫不已。正因为陈柏宏的惊叫,于之恒才清醒了一些。他冲着陈柏宏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赶紧洗澡,而陈柏宏惟恐出什么差错,赶紧打电话给范文宽、冯青青两个死党。范文宽、冯青青打的火速赶来,于之恒见了莫名其妙。
得知于之恒尚没吃饭,陈柏宏又去街市猎取。四兄弟围坐下来,才慢慢谈起主题。听于之恒哽咽着讲了姜甸村下村被淹的悲惨情景,冯青青等人无不拍案骂娘,大家发泄了一顿,又来劝于之恒。于之恒说:“你们放心,我不会悲观到自杀的地步。”
范、冯走后,陈、于也各自回房,于之恒没有心思去洗衣服,他本来是一个具有优良生活习惯的人。平时信奉当天的事当天完成决不拖到第二天,无论洗衣服还是干其他的事,今天却破例了。
将自己囚在房内,独坐灯下。于之恒忽然觉得这世界是如此的小,小到如同这个房间。那叩窗的细雨,如同隔世的琴声,可闻而不可及。望着电灯,于之恒心想:什么时候停电?都说人死如灯灭,姜甸村一下子死了一百多人,是不是就像某个大车间一下子烧坏了一百多只灯泡?想起那么多熟人在同一天与自己阴阳相隔,于之恒不禁眼角簇泪。原来,在巨大的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如此地脆弱!
想起两个月前的采访,仿佛就在昨天。想起姜甸村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仿佛就在身边。人生啊,真的如梦、如幻!再想起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镜溪稿进了印刷厂都被撤下来,于之恒心中愤怒万分。他想:假设稿子没有撤下来,省委书记、省长等领导看了之后作出批示并派相关部门的人下去督办,市县抓紧落实,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了……而今,撤稿也成为历史,悲剧也成为事实,事实和历史都是不能假设的。
可怜的姜甸村百姓啊!
可怜全天下苦难的农民啊!
人们常说脚踏实地能明辨是非,为什么我于之恒看到的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景象呢?二三十年前,人们谈虎色变,都害怕毒蛇猛兽,而今老虎几近绝迹,人已成为地球上最可怕的动物。人类,不仅在灭绝其他动物,也开始灭绝自己。像镜溪污染和姜甸村这样的灾害都是人为灾害,都是人类自灭的例征。当一些地方领导漠视百姓的生命以致灾难发生时,他们是否还记得自己同样是人同样只有一条命?当一个政党离群众越来越远时,已是否还记得当初对人民的承诺并以此为动力以史为鉴来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时间在嘀嗒嘀嗒地流逝,于之恒脑子里仍一片很乱,许多奇思怪想在交织碰撞,他感觉到脑子就要爆炸。
人生一世、白驹过隙。姜甸村那一百多人未做任何准备就匆匆而去,自己却为了功名在忙个不停。相比之下是何等可笑!唉,这世上有太多太多令人费解的东西,或许真要来一个换位思维。
于之恒走到窗前,推开虚掩的另一扇门,使个整个窗户全部洞开。窗前的大树遮掩着前面的房子局部。夜深了,附近楼房虽然没有灯光,不过外面雨帘之中房屋之上隐隐约约映有城市的灯光,如同城市闪闪的泪光。
一阵风、一阵雨。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雨水,于之恒心想:如果我倒过来,脚踏蓝天,像戴草帽一样头顶大地,会不会也有雨水一样飞坠的感觉呢?想到这里,于之恒仿佛看见一缕灵魂从室内飘然而出。沥沥细雨顿时变成了自己的满头长发,于之恒脚踏蓝天自由漫步,真是妙不可言。他俯首看地球上的生命,如同人俯着欣赏小小的蚂蚁。他看见了地球的脊梁喜马拉雅山脉,他看见了原江看见了故乡,还看见了清清的镜溪。镜溪之底有一百多姜甸村村民在向自己频频招手。他们每招一次手,于之恒就感到自己的头发跌落数根。头发跌多了,头皮就痒,用手去搔,万万没想到竟搔出一个大洞。于之恒忽然感到自己的头发变成一根根输血管,脑汁还有一生的意念正沿着输液管从太空往地球往原江往镜溪上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