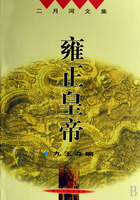从长春再往北接近哈尔滨的地方,有一个全国的产粮大县——榆树。榆树产粮,产酒,产干豆腐,是个安逸富裕的地方。产粮的地方禽畜多,牛羊驴马骡,猪狗鸡鸭鹅,样样齐全,所以,榆树除了产粮,产酒,产干豆腐,还多兽医。最有名的姓孟,上溯三代,至今能让老百姓随口报出名号的就有十几个。
我的朋友姓周,他的妹妹就嫁到了孟家,耳濡目染,也能为禽畜诊些小病,可见孟氏家传之盛。
周家妹妹的公爹就是一位名兽医,可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死于脑溢血,在世四十一年,可谓英年早逝。老孟先生走,三乡五镇都震惊了,供销社关门,银行停业,几个公社的农民都放下手里的锄头,从四面八方拥向孟家的灵棚。送葬的队伍黑压压排了几里地,有官有民,无不叹息哭泣。
老孟先生仁义。
你说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没有,但每一户农民都念着他的好,这说来就不易。
如果你问那些当年当过大队书记、小队队长的人,他们会说:“老孟大夫好,无论什么时候,你去请他给牲畜看病,他都是起身就走,绝无二话。吃饭呢,撂下饭碗;躺下了,马上穿衣服,从没耽搁过。医术高那就不用说了,还有二里地呢,听听牲畜叫,就知道得了什么病;一百来米呢,看一眼骡马,药方已经开好了。最绝的一点是,老孟大夫一辈子没端过咱们的饭碗,看完病,收拾家什就回,咋留也留不住。”如果你问老百姓,他们会说:“老孟大夫好,春秋两季往诊,家里的畜禽有了毛病,你只要吱一声就行,来了就看,看完就洗手,连个‘谢谢’都不容你说。”他们会说:“一个鸡蛋七分钱,一斤咸盐一毛二,劁一头猪七毛,想想,啥比价,可是,老孟大夫没收过咱们一分钱。”他们还会说:“我家的猪有病,老孟大夫给打吊瓶,在猪圈里守了一夜。”就是这几番话,大都如此。
老孟先生死了,许多人自发地去送葬,可谁也没想到,送葬的队伍里还有一匹马——三岁口,一身的纯红色。那马跟在人群的后边走,一直到了坟场,老孟先生入葬了,人群渐渐散去,只有那匹马还站在春风里,一脸的悲戚,久久不肯离去。
起初,人们没有注意到它,后来,有人注意到它了,惊得大叫:“这不是老孟大夫救过的那匹儿马吗?”认识它的人细看,可不是!
它来干什么呢?人们恍然大悟,它也是来送老孟大夫的,于是又有人哭起来,拍着马说:“义马呀,义马呀!”三年前的冬天,整个榆树地界下起了大烟泡雪,半天的工夫,沟满壕平,大道上的雪都没了膝盖了,车马难行。半夜里,老马要下驹子,可是偏偏赶上这驹子淘气,胎位不正,老马几经折腾,眼看就要死了,生产队的人急得直哭,想一想,那个年头,一死二命,生产队要遭受多大的损失呀。
有人说:“要是孟大夫在就好了。”有人说:“这大雪泡天的,门都出不去,孟大夫能来?除非他是神仙。”这话音还没落呢,门就被拍得啪啪山响。有人手快,费劲巴力地去开门,折腾半天把门打开了,发现外边站着一个雪人。风雪大,说话声根本听不清,就不由分说往屋里拽,待除了帽子,原来是老孟先生。
大家伙都愣住了。
老孟先生说:“还瞅啥呀,快给我端热水来。”大家伙七手八脚地伺候着。
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小马驹子终于给接下来了,大家伙这才松了一口气。屋子里静悄悄的,突然,生产队长“哇”的一声哭了,他这一哭,屋里所有的人都哭了,哭够了,痛快了,却说不出哭的缘由,再看老孟先生,已经躺在炕头呼呼睡着了。
这件事被神传起来。
可是,老孟先生就一句话:“这马性子烈,知道它快生了,不放心,就过来看看。”这一看,救了母子两条命!
老孟先生死了,当地的农民却没忘了他的恩情。红马驹所在的生产队每年冬天都要给老孟先生家送点烧柴,装上车不用车老板子,红马驹自己就能去,去了自己还能回来。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都是这样。包产到户后,这匹马分到了周家,周家也没改这个习惯,只是后来不送烧柴了,送一些过年吃的黏干粮。
曾有两年,榆树地界盗马贼猖獗,但是这匹马独来独往,没有人打它的主意。
1999年,这匹马病死了,周家的人征得孟家人的同意,把它葬到了老孟先生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