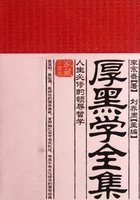因为宁静,所以致远;因为博大,所以容纳。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一个人,随着时光的渐渐远去,慢慢变得充实、醇厚,像千仞之高山,雍容之海洋,那么,这个人,不是智者,也是贤者,最起码,也是一个旷达者。不幸或者忧伤,都像时光里渐行渐远的河流,波澜与奔腾,终将归于沉寂;人生的林林总总,都会在生命的内在升华里,慢慢射出光芒。面对人生的沧桑或者无奈、社会的残酷或者野蛮,常常用自我特有的方式,悄然消解。然后,把一个博大坚韧或者饱经风霜的背影,碑石一样立在苍天大地之中。
这类人,在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个或几个共同点:善良、悲悯、宽容、正直、纯粹。对苦难,充满了深深的感悟;对黑暗,充满了深深的悲悯。
当我在阅读契诃夫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些。这个面对世界微笑,背对世界流泪的大师,悲悯心已在他的血液里,像俄罗斯大地奔涌的伏尔加河。当社会的畸形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的变态总是不自觉地展现出来。而这时,作为在苦难中绝望的人,总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了结与这个世界的恩怨。而作为内在坚韧、旷达雍容之人,可能就会采取另外的方式。我知道人有许多种,心灵也有许多种。实质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关键是,这个世界的天空究竟有多大?
特别是作为一个内在相对完整的人,悲悯心究竟有多少?当年的耶稣,就是从悲悯的世界中走出来,想独自一人承担人类所有的邪恶与罪过。实质上,耶稣一个人是无法承担这份过于庞大、又过于沉重的罪过的。人类自身的邪恶,不是耶稣一个人所能承担和所能拯救的。人类所谓的忏悔实质上只是一个借口,一个为了获得瞬间安慰的借口。人类实质上就是在暴力、谎言和借口中繁衍下来的。正是如此,契诃夫面临社会的这种苍凉,或者说这种邪恶,开始在黑暗中流出苍茫的泪水,然后转过身去,背对人类,用悲悯的心,写出了《变色龙》《套中人》,揭示出那个时代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人性的扭曲与自我的堕落;写出了《小公务员之死》《苦恼》《带阁楼的房子》
《农民》《第六病室》《万卡》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让我们泪如泉涌的作品。在我的理解中,生命的存在是时光深深的悲悯,是上帝给我们的残酷与慈祥。生命无论怎样坚韧,也无论怎样忧伤,都会在不断的远去之中,获得自我的有机整合,这种整合过程的完成,常常通过一种迫不得已的方式:死亡。
当我必须在阳光下行走的时候,我总是尽量保持沉默,像尘土那样沉默。我知道沉默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呐喊的代价或许更大。自我作为一种基本的生物存在,是不需要智慧的,我只要求每天像我一样的生物,能够生存下去,这就是我,生命的幸福全部——生存,一种沉默的生存。维特根斯坦说:
“凡是不可言说的,对它就必须沉默。”我不否认沉默是好东西。让人能够在沉默中死去,则当然更好。沉默的大多数之所以只能沉默,他们对有些事物的确不可言说,或者无法言说。虽然沉默有时是万分可怕的。他们只知道生命艰难的奔走,只知道生命沉默的苦难,只知道上帝不是很看顾他们。换句话说,只知道单一地生存。有了这种认知前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那块特有的土地上,用他一方面充满了嘲笑的眼神,一方面又充满了悲悯的内心,撕开了俄罗斯大地上的黑暗伪善,用特有的典型形象,展现了生命,特别是卑贱的生命无可奈何的悲剧存在、无可奈何的悲剧沉默。我在阅读他的《被凌辱与被损害的》的时候,在阅读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时候,在阅读他的《白痴》的时候,在阅读他的《罪与罚》的时候,我总是被迫沉默。耶稣在被本·丢·彼拉多的军队押上骷髅地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时间迟早总要到来。耶稣抬头看了看远方,黄沙飞扬的远方,那里,阳光正在迷乱。五月或者六月的风,正像发情或者绝望的狼群,狂野奔跑。耶稣心想,能在这里被迫“圆寂”,也不算枉度此生。当他与另外三个不明不白的玩意儿挂在一起的时候,我却无法理解耶稣此时的内心,史书上也没有这个方面的记载,即使有,我也没有看见。
沉默,就成为了我在阳光世界与黑暗世界的唯一希望。拉斯科利尼科夫,《罪与罚》里那个沉默的男主角,生命的唯一存在目的就是为了扼杀一个沉默的老太婆。沉默的老太婆实际上只是拉斯科利尼科夫沉默存在的道具。老太婆的沉默被斧头砸破,也就不存在了。同样,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在社会上东游西荡了。实际上,这是陀氏的残酷,也是他的悲悯,生命以这种方式打破平衡,谁能说这是一种苦难,或者不是一种苦难呢?社会生存本身的残酷性,导致社会不可避免的悲剧走向。虽然,拉斯科利尼科夫总是喋喋不休,并在心里演绎了无数次的这种沉默话剧,直到那个老太婆的出现,才打破拉斯科利尼科夫内心的平衡。虽然那个放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婆一直在沉默之中。在沉默中死去,这是生命的一种归宿,更是生存完结的一种幸运。老太婆一生的幸运等待,就是为了遇上了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是为了遇上拉斯科利尼科夫坚决而又猥琐地举起那把漂亮迷人的小斧头。而拉斯科利尼科夫,却在作家的笔下变得神秘虚幻。故意让主人公处于混乱的临界,这是陀氏的招数。在这里,沉默变得流畅而又生涩,悲悯变得冷漠而又温柔。当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想让人说点什么,却又让人必须沉默的小说的时候,主人公内心的温暖照耀着黑暗的最后游走,主人公偈语般的沉默,在幽默与荒诞的外衣下,打破了沉默的内外观照,打破了唯一的法律枷锁。在陀氏笔下,拉斯科利尼科夫竟然成为了黑暗中一道迷人风景。实际上,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沉默与残酷总是孪生的,悲悯与冷漠也是孪生的。这种情结在海明威和博尔赫斯那里存在,在托尔斯泰那里存在,在凡·高和莱辛那里存在,在巴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那里也同样存在。
生命总在移动,也总在消失。面对这个沉默的社会,我无话可说时,我总是这样想。无论怎样的生存,总是充满了苦难。不是物质上,就是精神上的苦难。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苦难,才有了它没有退路的另一面:博大,或者坚韧。在《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里,这种苦难与博大体现得淋漓尽致。
库切,这朵好望角上开出的灿烂花朵,以他最深沉的色彩,涂抹了那个表面繁荣,实质上苦难的时代。在库切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值得悲悯的,一切都是可以撕裂的。库切以他最伟大的悲悯,展现了人性苦难的沉默与博大的坚韧。迈克尔,南非土地上一个蝼蚁一般的生命,一生中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到远方去,到没有战争的远方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迈克尔作出了种种艰辛异常的努力。库切也在流着眼泪中,满足了迈克尔的临界要求,或者说,满足了人类内在精神的基本悲悯。迈克尔带着母亲,从战乱的城市出发,从一个园丁向最后的流浪汉出发。在一个闷热的中午或者下午,总之是个白天,迈克尔开始了肉体与灵魂的远征。这个有着兔唇的男人,怀着最后的深情看了看这个城市:刺刀在阳光下闪烁着明亮逼人的光斑,枪支在天光下跳动着处女一般燃烧的幽光,全副武装的军队在各个路口,温文尔雅,又气势汹汹,架起路障,搜查行人。还有各种来来往往,随时可以剿灭生命尊严的机器。亮亮的白光里、湛湛的青天下,随时跳动着死亡那美丽迷人的阴影。迈克尔一边用独轮车推着母亲,一边在心里做出了最沉默的打算。向远方,向着遥远的远方,迈克尔开始了他生命里最黑暗,又最满怀希望的第一步。小说在这里,切入了库切的基本思想:战争,特别是种族与内战之争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与此同时,库切的残酷性也体现了出来,无论如何,也要让迈克尔一无所有,要让迈克尔的愿望成为齑粉。库切先是让迈克尔的母亲死去,然后是迈克尔自身,全面被洗劫。最后,迈克尔捧着母亲的骨灰,开始在逃亡路上,四处逃窜,像一只被砍掉了尾巴的老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经历了无数的残酷和磨难之后,迈克尔终于到了一个不毛之地,在那里,战争好像已经冬眠了,迈克尔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最基本生存打算。
这个长着兔唇的男人,从食品结构开始,不自觉地,就进入了物种退化的基本过程,先以南瓜花为食,然后是蚂蚁,最后是甲虫。迈克尔一边嚼着生涩的节支类昆虫,一边望着湛蓝悠远的天空,内心深处在风起云涌之后,归于寂静的沉默。库切看到迈克尔流落到了这里,忍不住停顿了一下。想让另外的事物——悲悯出场,却始终没有成功,残酷与沉默在此时变成了唯一。迈克尔在这里,把生命的坚守退到了人类以外。在这个故事中,库切要告诉我们的是,人是可以退化到昆虫的,人实际上就是昆虫的变体。
在《耻》中,库切转换了叙述视觉,把触须伸到了人性灵魂与社会构架的层面。卢里作为大学教授,知识只是一件外衣,本能导致卢里教授从思想层面走到了生物层面。与一个女生发生了肉体纠缠之后,卢里教授开始了意想不到的自我纠缠:身败名裂与灵魂的无可奈何的退守。当卢里教授退守到女儿庄园的时候,却遭受到来自灵魂永远也无法解脱的困扰。女儿被当地黑人强奸,却又拒绝报警。最后父女关系破裂,卢里教授又从庄园退守到城市。当卢里教授回到城市之后,等待他的将是一无所有,不仅失去了事业,还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
而卢里教授的女儿,最后居然嫁给了强奸者之一,成为他的第二或者第三任妻子。生存是残酷的,库切在这里沉默地说。灵魂上的距离是不可能接近的,库切望着茫茫的天空,在南非那块土地上,像一颗燃烧之后,又冷却下来的沉默陨石。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看待这种生存意志,或者是生命状态。人类的苦难无时不在,而苦难的前提却常常是沉默。沉默就是尘土,就是尘埃。尘土的沉默有谁会在意?当然,与沉默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这就是爱。沉默的爱比张扬的爱,更有魅力。爱让我们学会了宽容,学会了悲悯。在《复活》中,随着玛丝洛娃在审判所的出场,涅赫留朵夫的内心开始煎熬。
这种煎熬实质上就是悲悯的出场,也是爱的再一次被唤醒。最后的涅赫留朵夫无论如何要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复活,是爱的复活,是深深的悲悯在上帝天光照耀下的复活。当玛丝洛娃面对涅赫留朵夫,一直叫骂,“我讨厌你,我讨厌你的胖脸,我讨厌你胖脸上的眼镜”,到最后却噙着泪水,看着这茫茫的人生道路,看着涅赫留朵夫来自灵魂深处的忏悔。那颗受伤的心,在悲悯和爱中,渐渐温暖起来。在此,托尔斯泰用他最基本的人文主义情怀,用基督深深的悲悯观照,给我们展示了人类生命的另一面:生命的行走无论多么艰难,只要有爱的支撑,就能达到生命的圆满。托尔斯泰如此,哈代也是如此。在《苔丝》中,哈代给我们展示的却是生命的遭遇。苔丝没有玛丝洛娃这种幸运。苔丝面临的只有自我,只有家庭的无穷无尽的苦难,这种苦难使尊严低下头来。
为了改变这种苦难,苔丝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了人生的更大屈辱。苔丝为了缓解这种屈辱,不得不退守到自己最后的港湾——家。表面看似平静的苔丝,人的内在尊严却并没有半点屈服。她要让那个毁坏她青春的家伙付出代价。当然,这是在她碰上真正的爱情之后。哈代在这里,给我们展示了生命的遭遇。这种遭遇实际上是人类的遭遇,带有原罪的成分。哈代还有一种暗示:再也没有什么比生命的遭遇更让生命感动的了。
在此,哈代开始设置陷阱。他想通过这个形象,把人类的理念推入这个陷阱之中:苦难源自生命,生命源自爱。因爱而苦难,这是耶稣的一部分;因爱而毁灭,完全是摩西出埃及的手法。把心爱的生命亲手毁灭,这不仅仅是一种残酷,更是一种大悲悯。苔丝被所谓的堂兄或者表兄强暴,完成了性格和生命意义上的全面转轨;克莱尔的出现,导致了苔丝的内在煎熬,因爱而受伤害,因爱而必须躲避。两者的斗争让苔丝彻夜不宁。哈代让克莱尔出走,来加重苔丝的精神灾难,苔丝为了结束这魔鬼附身一样的精神交战,不得不走上充满杀机的道路。
最后,克莱尔再次出场时,苔丝已经完成了杀人的使命,终于因爱而走上了最后的毁灭。因爱而毁灭,在战争中是可以理解的。战争就是对人性的毁灭。而在和平时期,哈代以这种方式结束苔丝的命运,不得不让人感到疼痛。好在哈代最后安排了一个宗教献礼般的结局。这种结局,对于苔丝,对于我们,都是一种安慰。只是有一点,这种心理的疼痛,还会持续。这就是哈代。生命的坚守意味着另一种放弃,生命的沉默意味着另一种风暴。苔丝,在自我的挣扎中,结束了自我生命的苦难。
哈代在这里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常常想,基督的悲悯,其内在动机究竟在哪里?大师们看待这个社会,其内在动机又在哪里?人世的沧桑在大师们的笔下,总是变得扑朔迷离。社会太多的苍凉,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悲悯,而人生的苦难又使他们流出了过多的泪水。
当这些形诸文字,就成为了人类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了我们血液流动的一部分。在今天纷攘的尘世中,再阅读他们,或许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善良、悲悯、宽容、正直、纯粹;我们仍然需要爱,不论这爱是喧嚣,还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