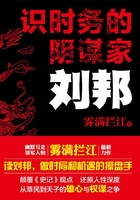就在这个当口,他听到快捷的脚步声由下面传过来,然后便认出是一个同事。他是一个健壮的青年,留着大胡子,也戴一顶军帽,但是他那粗糙的手里握着的并不是戟,而是一根大松木棍。他挥动着那木棍较粗的一头,愉快地向他打招呼。“安得烈,”他走得够近时,这样说。“今晚的情形如何?要不要我陪你守卫。我注意到你同那个意大利人有麻烦。你知道他是不会忘记的,一定会邀更多的帮手再来。你看,我这里有个东西,可以让那些狗扫兴。”然后,他从皮夹克的胸袋里掏出一只手枪,然后扳起枪来。“不啦,谢谢你,高必烈。”安得烈说。“那意大利人非常懦弱,他一定不敢单独来。要是有一群人来,我们俩对抗他们就力量薄弱了。等他们来我会给你一个信号,叫别的同事一块来。那玩意儿,”他指指那把手枪:“不要用它。在黑暗的地方,那东西没什么用,只会打中葡萄藤。但是,我们要是捉住一个,他身上所挨的许多拳头,比皮肉上的一个洞要好多了。因为,那样一来,他就可以提出作证,对我们是不利的。”
“那就随你吧。”那青年回答。“我是说必要时可以用用。但是,但愿他们会再来。我要找他们算账。汉斯也急于要教训教训这些流氓。我们要痛痛快快的揍他们一顿!”
安得烈默默不语。那有胡子的守卫人简短向他打个招呼,又走下去了。大家都习以为常不去干扰这沉默寡言的人,绝不勉强他。
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但是,还要再过几小时,黑夜才能接管。原来,在右方,由温池高山发射到下面伊芬格河边上的日光仍然占优势。因此,河面上形成一层蓝兮兮的云雾。太阳的光线由云雾的几个地方穿过,悄悄地照到峭壁后面的山谷。牧羊人在下面牧场上赶着羊群,所有通往村子的路都聚集着在下面吃了一天草的美丽的黄牛。但是在南方,垂安廷山和美丽的孟德尔峰,雄伟的俯瞰着谷里的景物,却让非洲热风吹到谷里的潮湿雾气笼罩着。
只有到很晚的时候,才有一条窄窄的银色月光出现,摇摇不定地照着这静静的深谷,不久,便在缓慢地飘到山里的云雾中消失了。在城里,大家很早就停工了。所以,城里最后的繁嚣声,和远近谷处最后的声响都停止了。惟有山中的溪水,迅速呼啸而过。由远处而来的南风嗡嗡吹过,把路上的灰尘卷起一阵阵漩涡,并且吹得秋天的落叶沙沙作响。到了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这声音也停了。现在,一动不动的黑夜笼罩大地,给人以潮湿而温暖的感觉。没有星星,没有一丝风,把催眠的露水倾注到千千万万人的眼睛上。
葡萄园的守卫人都没有睡。他们知道是为了什么。那些蛮横的贼趁着无月之夜闯入葡萄园,造成严重的损害。这并不是第一次。在山上,他坐在那玉蜀黍秆子搭的小屋旁边吸烟斗,偶尔将主人送来的那罐酒倒出来喝喝。大雨点由叶子构成的屋顶穿过,滴在他的浓发上,可是,他几乎没有感觉到。他注意地听城里那方向的动静。等到钟敲过十一下时,他慢慢站起来,悄悄越过街道,来到藤荫的一个地方。那里筑了一个嘹望台,是用南瓜叶搭成的,还有一面突出的小墙。他在这里躲在岩石后面,把戟放在身旁便于抓到的地方,然后,燃起烟斗。他身上的血液不像白天那样沸腾了。现在有点事做,对他是很有益的。因为,这样他才可以借着一件危险的事发泄他的不安情绪。因为,他确信那个意大利人不会让这一夜白白度过而不采取报复行为的。
但是敌人不慌不忙;他似乎希望使海浪平息,让人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他可以听到钟楼上敲出的午夜钟声,可是仍然没有动静。隔壁葡萄园的守卫人在巡查途中经过安得烈身旁,他说:“他们今晚不会来了。如果发生什么事,你只消吹口哨好了。”安得烈低声说:“再见!”他的同僚想去睡,他很高兴。因为,他更喜欢独自对付那意大利人:一个对
又过了半小时。什么声音?那孤独的守卫人突然竖起耳朵听。离他不远的地方,在两个葡萄园之间,有个倚山而建的农舍。那里传出一阵很大的吼叫声。紧接着这个声音,出现了一个漆黑的影子,不像是人形,在一阵剧烈的围栏破裂声中,横冲直撞地奔出。听到这些声响的人连忙跳起来,他的心怦怦跳,不自觉地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同前面的藤荫路之间,有个阶梯和墙隔着。转眼间他便站在墙边,身子倚着他的戟,向贴邻的领域窥视,因为那些声音是由此传来的。那吼声愈来愈近,像是沙漠中让猎入射中的动物,愤怒的悄悄走近猎人。现在前面的墙间传出隐隐的沙沙声,石头崩碎,哗啦啦滚下台阶。那神秘的怪物由缺口跌落到楼台下面的台阶,力量极大,以至于安得烈倚靠的那面墙像是有地震似的,不住抖动。
霎时间,完全静下来了。只有一阵微弱的呻吟声由下面那个重东西崩溃的地方传到守卫人的耳鼓。那青年再也不疑惑了!那是邻园的一只牛,因为他们的马底就在附近。他忽然心生猜疑,不觉勃然大怒。他用手指放在口中,吹出两声尖锐的口哨,然后跳下来,越过墙壁,来到大路上。
那个击倒的动物躺在路边,半个身子栽入那些石块当中,两只角陷入地下,四只脚乱踢。虽然如此,现在没有方才由藤荫路上跌落时那样痛苦了,只不时的发出隐隐的叫声,仿佛是在求救。安得烈走过来的时候,那个动物躺在那里,乖乖的,忍着痛楚。
四百个其他的青年守卫现在也从各方面走过来,彼此低声地交换几句激动的话,然后,去扶那个动物起来。安得烈正在静静地检查它周围的地上,突然,他用戟的铁头由地上挑起一个发光的东西。“对了!”他说,“我走下来的时候闻到这东西的气味,那时就这样想:这是他们的诡计。你们看!”
他拿过来一块火种。那火种虽然受了潮,仍在燃烧。“无耻的禽兽!”他怒声地说。“他们把这东西放到这无害的动物耳朵里,想要激怒它。它要是没有跌倒,这火种可能燃烧到它的脑袋,现在也许准备屠宰了。它把这火种摇掉了,可以说是幸运极了。我要是在这里遇到那家伙,啊,圣十字架——”
高必烈扳上手枪的扳机说:“你一块来,好不好,安得烈?”
“不,不要用那东西。”安得烈坚强地说。“把牛扶起来,带它回去。我要独自去。”
他且跳且跑的,迈开大步,不声不响的穿过另一边的柳林,越过牧野和沼泽。他心中有一阵猛烈的争斗欲望燃烧着,使他的感官都变得更加敏锐。现在雨正在无声无响地不住落下,风的呼啸声也比以前大些。虽然如此,他走近城门时,听到下面柳林中远远传来脚步声。现在,他可以辨认出前面远远的有两个人正在逃走。忽然他高兴得几乎忍耐不住。原来,他认出了他所憎恨的敌人的白夹克。再走不到一百米,他们就会到达城门了。但是,他们走得很慢。他现在已经走得近些,可以看得清楚了。其中一人仗着他的同伴扶持,一拐一拐,很吃力地走着。那头牛也许用它锋利的角自卫。他们一路走一路在谈他们那个恶作剧的行动。那走路一拐一拐的家伙哈哈大笑。那腔调,这个复仇者记得清楚,就是早上那个人的声音。但是,那笑声突然变成一声恐怖的叫喊。原来,那可怜虫受到戟的猛烈一击,已经跪在地上,哭着求饶了。于是又一击,就将其击倒在地,再也发不出声了。他的同伴,正要跑过来救他,现在让两只铁拳抓住。于是,在黑暗之中,开始了一场猛烈的争斗,谁也不出一声。激怒的敌手咬牙切齿,彼此报以白眼。后来,那丘八看出自己的优势,把敌人推到山沟边缘,使他的脚在潮湿的地上一滑,跌了个倒栽葱。他还来不及爬起时,那丘八便跑了。安得烈一个人站在那意大利人旁边,任他怎样叫,怎样摇他,他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没有丝毫活着的迹象。
“他死了!”那没生命的躯体由他手中再滑落地上时,那青年大声地自言自语。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颤。霍然间,他的脑海里出现一个画面,他这凄惨的一生又历历如在目前。
他的良心很痛苦地受到压力,但并不是那杀人的行为。他们在深夜里闯入葡萄园,简直像残忍的强盗一样。他们所遭受的,不过是对他们恶毒行为的报复。在他面前躺着的,那个脑壳破裂,面孔浴在自己一滩鲜血中的人,如果是另外一个逃走的,素不相识的人,这件事便不会使他很难过。可是,偏偏是这一个人。这个他所恨的人。他恨他,因为丫头同他交朋友——他的妹妹呀!他现在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自己被天罚的命运。这是多残酷的事!这时候,他的血似乎已经凝结成冰块了。整整一天,还有经过半个夜晚,他都在路旁藏着,想报复,想杀人。偷葡萄,害死那个无害的动物,这些罪行与他有何相干?他这样报复是犯了一个大不相同的罪。因为这个蛮横的家伙同他的妹妹调情,因为她听到他的笑话哈哈大笑,因为她见她哥哥生气,曾经卫护他。这就是他应该抵偿的罪。这就是他如今静躺在自己鲜血中的原因。那个站在他面前的人并不是卫护法律的人,而是凶手,被自己良心判罪的人。
高必烈现在走过来了。他的脚步声惊醒了那正在沉思的青年。他对另外那个人的问话没有回答。他只默默地对他做手势,意思是:他们应该把死者抬到托钵僧的修道院。那修道院可以在梅仑城门看到,在城墙的那一边。在修道院门口,他们把死者放在门里面。这时候,安得烈呆呆地说:“高必烈,按门铃。等他们开门。你可以告诉他们是我干的。愿主保佑你。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说完,他猛然转过身来,便消失在黑暗的街道上。
他不急于实行他的计划,但是,他只能慢慢地拖着步子。往前走,因为他心事重重,使他变麻木了。他到达长藤亭巷黑暗的拱门,才有遮雨的地方。这时候,他坐在石凳上,将沉重的头靠在柱子上。在白天,那老妇人在她的炭炉上烤栗子。现在地上仍摊满了栗子壳。安得烈的钉靴子踩在上面劈啪作响。他记得,他由于自尊心很强,不肯向他母亲要东西吃的时候,他有多少次都是来到这里设法充饥!那一边,再走过几幢房屋,就是那个糖果店。丫头曾经将她节省下来的零钱带到那里。他如今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心形的蛋糕,那是她平生第一次自己花钱买的甜点心。她要他同她分而食之。当他拒绝的时候,她把那蛋糕扔到帕西叶河里。不过她是非常想吃的,因为她扔的时候哭了。即使现在,他回想到那幼稚的眼泪时,他会感到一种胜利的快乐,因为他有力量驾驭那个轻率的,生性倔犟的小女孩。同时,他由于这种快乐而感到害怕。于是,他又激动地跳起来,在那荒凉的拱门路上往前摸索而行,一直来到“十点钟弥撒教士”住的地方。前门没上锁。那个有古老的、有棱角楼梯的门廊非常暗,因此,一个不熟悉的闯入者有跌断头颈的危险。安得烈蹑手蹑脚走上楼。他每个台阶都很熟悉。他走到顶楼的时候,蝙蝠惊得飞出来。牧师就住在这里。他在门前站了一会,倾听室内是否有呼吸声。然后,他决定走进去。
但是屋内空无一人。在他小时候住的那个隔壁的小屋,他也找不到那位教士。现在,他仿佛更加感觉到自己已让主和世人遗忘了。他在那无人打扰的床上坐下来,重新想到那些以往的岁月,又默想他所面临的,必须坚强地痛下决心的局面。
那只猫,就是“十点钟弥撒教士”的女管家,轻轻地爬过来,因为它已经认出他来,在他身边喵喵的叫着,向他讨好。然后,它跳到他的膝上,靠着他的胸,磨擦它那柔软的背。如今,他不觉热泪盈眶,把面孔埋藏在这亲爱的老友光滑的背上。他以这种方式得到宽慰以后,便轻轻地将猫由膝上抱起来,站起身来,摸索着走下那个摇摇晃晃的楼梯。因为外面的钟已敲打一下,他要是想成功地施行他的计划,他就不敢耽搁。
他沿着他那教会朋友早上要走的路径,一直往上,到希慈住的城堡。那里,“十点钟弥撒教士”特别受欢迎。他也许同安娜姑姑谈论一些教会的事情而不得分身,或者是因为品评葡萄酒而耽搁,准备在那里住一夜。至少,他们会知道他到那里去了。因此,这个亡命徒便走过藤亭巷和帕西叶门。现在,他走得比较自在些。这里有一条石子路横越波涛汹涌的帕西叶河。他由这条石子路走过。如今雨已经小一些,云也变得比较轻盈些。由东北方吹来的风很强,把空中的云吹开一条缝,因此,微弱的太阳光线便临到峡谷里冒出泡沫的波浪上。上山往西走,走了大约十五分钟,他要是注意看,就可以看到那个窗户。在那窗户后面,就睡着他的妹妹。在这里,他如果做最后的祷告,迅速跳过那个石头胸壁,他就可以摆脱一切尘世间的痛苦。但是,面临着这两个诱惑,他仿佛感觉到同样的恐怖。他现在匆匆走过桥上发出回响的石板,到达奥伯麦斯山另一边的斜坡。这时候,他揩揩额上的汗。
他爬过街道和小路时,守卫问他口令。他同他们交换了暗号,但是对他们进一步的问话,没有答复。他愈来愈没耐性地不住往高山顶上望。那古堡就在上面向他召唤。那是一座黑色的,一堆不匀称的石块筑成的古堡,附近栗子树顶发出呼啸的声音,周围的河水流过葡萄园,又流到下面的山谷。安得烈自从七岁以后就没走过这条路。有一次,他到山上去看希慈的孩子们,暗暗希望见到他那性情温柔,面孔苍白,眼睛美丽的教母——他的安娜姑姑。那时候,希慈用苛刻的话将他逐出农场,并且禁止他以后再在那里露面。他咬牙切齿地走了,发誓:世上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再迈过那个门槛。但是,他现在的痛苦使他忘掉了旧怨。
他很吃力地前进,在岩石路上迷了路之后,他到达了山顶。到这时候他才忽然想到,他不认得这迷宫似的城堡中的途径。他无奈地在通往下面庭院的拱形入口站了片刻。他看到城垛旁依垛而建的木楼梯,上面没有遮拦,可以望见天空。你必须爬上那楼梯才能到达那些尚可住人的房间。他要是惊醒那些敌视他的人,而又找不到教士,人家对他又有何看法?他要如何解释才能叫人谅解他这次夜访?他感到自己的头脑空洞得很,很难将混乱的局面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后来,他已经差不多要转回身来回去了,忽然听到楼梯顶上墙洞中的守夜狗大叫,这才解除了他的困难。
那只老狗多年来已经变得太懒,不肯离开那个墙洞,可是它睡得很警觉,庭院中只要有陌生人的脚步声,它都听得见。它独自暴躁地叫了几分钟以后,它睡的地方附近那扇小门开了,上面楼梯台上露出一个女人的身影。安得烈听到她向狗说话。她骂它不好好睡觉,声音会惊醒梦中的安娜姑姑。他叫她:“露馨!”那女孩吃了一惊,退回门廊,她倾听片刻,那狗也不叫了。她听到有人再叫她的名字时,她向前走了几步,凭栏窥视一下。“下面是谁?”她声音发抖地说。“是你吗?安得烈?”
“是我。”那青年回答。“十点钟弥撒教士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