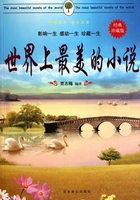四月二日
星期六
下午二时三十分
万斯仔细地看了一眼字条上的内容,又有条不紊地取出单眼镜片。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此时他正抑制着自己对这件事满腔的好奇,戴好眼镜后,万斯又认真地看了一次字条,然后,把它递给了亚乃逊。
“也许,这在你的方程式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万斯用嘲弄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亚乃逊。
亚乃逊接过字条,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然后苦着脸把它放在桌子上。
“我想这张字条和主嫌犯没多大关系,这位同伙的头脑好像并不灵光,这个‘主教’嘛……”亚乃逊低下头说,“我可不认识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而且在我的算术中,无法接受这个护符。”
“如果是这样,亚乃逊。”万斯认真起来,“我想你的方程式对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而这张神秘的字条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对于方程式我们的确是门外汉,但恕我直言,这张字条也许是到目前为止,与这一连串事件关系最紧密的线索,是它使我们跳出追究这个案子只是个意外的窠臼。换句话说,它是控制整个方程式的恒数。”
希兹厌恶地盯着桌子上那张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条。
“简直是疯子,万斯先生!”警官愤怒地说。
“确实是疯子,警官。”万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你们不觉得这个疯子疯得很特别吗?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他对整个情况了如指掌这一点——你们看,他知道罗宾的名字是寇克,还知道罗宾是被弓箭射杀的,而且他还晓得罗宾死时,史柏林就在附近,等等。他真是个‘万能通’,同时他也具备一些作案常识。这张字条一定是在你和你的部下还没有抵达这里之前,就已经打好投入信箱了。”
“还有可能,”希兹不甘示弱地说,“这家伙是一个好事者,一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立马写出了这么一张莫名其妙的字条,趁着警察不注意的时候,放入信箱的。”
“那就是说他得先跑回家,然后仔细地用打字机把字打好,再放回来?”万斯无奈地笑了笑,接着说,“抱歉,警官,很抱歉你的推理无法成立。”
“那请问你是怎么想的呢?”希兹恼怒地问万斯。
“现在我根本什么都没有想到。”万斯起身打了个呵欠说,“喂,马克汉,我们也坐得太久了,现在去看看碧杜儿厌恶的德拉卡先生吧!”
“什么?德拉卡?”亚乃逊吃惊地叫起来,“跟他也有关系吗?”
“是的,德拉卡,”马克汉向他解释道,“今天早上他曾来这里找过你,也许他曾和罗宾、史柏林碰过面。”说完这句话,马克汉犹豫了一下说,“那现在我们一起去吧!”
“不,我可不去。”亚乃逊弹了弹烟斗上的烟灰说,“我还有一大堆的学生作业要批改,不过,你们可以带蓓儿去,那个五月夫人有些怪怪的……”
“谁?五月夫人?”
“啊,抱歉,我忘了介绍,你们肯定还不知道这个人,我们叫她五月夫人,这是尊称!五月夫人是德拉卡的母亲,脾气非常古怪。”席加特意味深长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她很少来这里,几乎没来过,一个个性很倔,成见很深的女人,一天到晚都把心思放在德拉卡身上,好像德拉卡是一个婴儿似的,她那样照顾人,真让人伤脑筋……你们带着蓓儿一起去吧,她比较喜欢蓓儿。”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万斯说道,“那么现在请你去问问蓓儿小姐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去?”
“可以。”亚乃逊微笑着和我们道别,他的微笑里带着一点嘲讽,他转身爬上了二楼,两分钟后,迪拉特小姐就与我们同行了。
“我听席加特说你们要去看看阿尔道夫,他倒没什么大碍,可怜他的母亲,一点小事情,都会惊吓到她……”
“我们一定会小心不吓到她的。”万斯保证似的说,“德拉卡今天早晨来过,女佣说,她曾听到他和罗宾,还有史柏林他们在射击室里谈话,也许能从他那儿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也说不定。”
“但愿如此,”蓓儿字斟句酌地答道,“但,请你们一定要小心五月夫人。”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恳求,好像她要保护五月夫人似的,万斯疑惑地看着蓓儿。
“她很可怜,”蓓儿连忙解释说,“她以前是著名的歌星——不是那些混饭吃的艺人,她天赋过人,有着光明的前途。后来她和维也纳一流的评论家欧特·德拉卡结了婚,婚后生下阿尔道夫。当孩子两岁的时候,一天,她带着他在公园玩,结果她不小心把孩子摔了下来,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阿尔道夫的脊椎骨严重受伤,成了残疾。五月夫人格外悲伤,她认为孩子的不幸都是她造成的,于是她舍弃了原有的事业,专心地照顾阿尔道夫。第二年,丈夫也去世了,五月夫人带着阿尔道夫来到她少女时待过的美国,买了房子定居在那里,她的生活完全围绕着阿尔道夫,阿尔道夫长大后变成了驼子,她为了他,牺牲自己的全部,她全心全意地照顾阿尔道夫……”说到这里,蓓儿的脸颊显出了阴暗的神色,“我知道你们都这样想——夫人还把阿尔道夫当成孩子一样看待,这一点正是她病态的地方。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母爱啊,温柔体贴的爱,爱的精神病——我叔叔是这么说的。最近几个月来,她变了,她经常小声地唱着德国古老的童谣,然后两手交叠放在胸前,就好像——哦,是的,好像神明那样,看起来很可怕——她似乎抱着娃娃。而且,她对于阿尔道夫的事情有强烈的愤恨,她憎恨所有的男人,上个礼拜我和史柏林去看她——我经常带别人看望这个寂寞不幸的老人——她却用厌恶又残酷的眼神看着史柏林说:‘你怎么没有残废呢’……”
蓓儿环顾了一下我们每个人,停止了说话。
“所以,希望大家多留意一点——五月夫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是去欺侮阿尔道夫的。”
“好的,我们尽量不给夫人添加困扰。”万斯同情地向蓓儿保证。我们一起走出去,万斯突然问了蓓儿一个问题:“德拉卡夫人的房间在哪里?”我这时才想起万斯刚刚注视德拉卡家好一会儿了。
蓓儿先是被万斯突然提出的问题吓了一跳,她讶异地看着万斯,然后回答说:“在房子的西边——她的阳台就在射箭场的上方。”
“哦?”万斯从兜里取出了香烟盒,点上一支烟问,“夫人常常坐在阳台的窗边吗?”
“是的。夫人常常坐在那里看我们练习射箭——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看着我们的动作,会让她更加痛苦地回忆过去。阿尔道夫的身体非常差,只射了两三箭就会疲劳无力,然后就不再玩了。”
“真是值得同情,她看着你们练箭而想到某些痛苦的过去,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啊。”万斯充满怜悯地说,“也许……”当我们正拉开地下室的门,走到射箭场上时,万斯突然说,“我们应该先拜访德拉卡夫人。向她说明我们的来意,这样她会放心。可是,我们怎么才能不让德拉卡知道而直接进入夫人的房间呢?”
“有办法。”蓓儿似乎很喜欢这个提议,“我们从后门进去吧,阿尔道夫的书房靠近正门。”
当我们恭敬地造访时,德拉卡夫人正斜靠着枕头坐在古式长椅上,她靠着窗边沉思着。迪拉特小姐像对待母亲那样亲热地和她打招呼,而且屈膝亲吻她的额头。
“伯母,我都不知道怎么向你说起,今天早上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蓓儿说,“现在我带着这些先生们来拜访你。”
德拉卡夫人的脸苍白又悲戚,在我们刚进门的时候,她曾躲起来,现在则充满恐惧地望着我们。她的个子很高,面容憔悴,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地抓着椅把,手上的青筋都凸起来了。她的脸上皱纹很深,因而看起来很丑陋。而眼睛则炯炯有神,鼻子坚挺而威严,年纪一定已经超过六十岁了,发色斑白。
在我们进入房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动也不动,也不开口说话,只是嘴唇轻轻嚅动着。
“有什么事吗?”夫人低沉地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