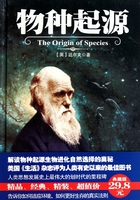我跟上尉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这位老兄虽然上了年纪,可还是显得很高贵。他也是我的好伙伴。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离开这个家,会走下坡路,可是,这天还是来到了。当时我不在场,后来我从别人口中知道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上尉跟杰里送一群人去大火车站,途中经过伦敦桥。回来的时候,路过伦敦桥和纪念碑之间的某个地方,杰里看见两匹强壮的马拉着一辆酿酒商的平板四轮大车朝他们驶过来。赶车的人用马鞭狠狠地抽打那两匹马。因为马车上没有装东西,车身很轻,所以车轮飞快地朝前滚动,那人根本没法控制马车。有个小女孩不小心被撞倒,还被车从身上碾了过去。一眨眼,他们就撞到杰里的出租马车上,车轮被撞得散了架,马车也摔倒了。上尉被马车拖倒在地,车辕裂成碎片,有一片正好刺中他的肋部。杰里也从车上摔了出去,还好只是擦伤了点皮。没人知道他是怎么逃脱的,他自己老说那是个奇迹。可怜的上尉站起来的时候,人们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地方被割伤、划破了。杰里牵着他慢慢地走回家,一路上他的血浸透了白色的皮毛,从两肋和肩膀上滴下来,真是悲惨的一幕啊。后来证实,赶车的那个人当时已经喝醉了,他还被罚了款。酿酒商不得不对我们的主人做出赔偿,可是有谁能弥补可怜的上尉受到的伤害。
兽医和杰里尽力给上尉减轻痛苦,让他觉得舒服些。马车得修理一下,于是我好几天没有出去拉车,杰里一分钱都没赚到。这次意外发生以后,我们第一次回到停靠点的时候,管理员过来打听上尉的情况。
“他不可能好起来了。”杰里说,“至少没法给我拉车了,这是兽医今天早上说的。他说,上尉或许还可以干点运货之类的活儿。这让我很生气。拉货车!我在伦敦到处都可以看见拉货车的马最后被折磨成什么样子。我真希望把所有的酒鬼都关进疯人院,免得他们撞到清醒的人。他们要是摔断了自己的骨头,撞碎了自己的马车,弄瘸了自己的马,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管不着。可我觉得,往往是那些无辜的人受到伤害,而他们只要做出赔偿就行了。他们不可能弥补一切——他们没法弥补所有的麻烦和烦恼,没法弥补浪费的时间,也没法弥补失去一匹好马的痛苦,他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现在再说赔偿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真想看到那些酒鬼被打到地狱的最底层。”
“我说,杰里,”管理员说,“要知道,你无意中冒犯了我。我做人并不像你那么好,这让我很惭愧,我希望自己能跟你一样。”
“嘿!”杰里说,“那你为什么不戒酒呢,管理员?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应该成为酒的奴隶。”
“我是个大傻瓜,杰里。我试过两天时间不喝酒,当时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花了几个礼拜,很辛苦才把它戒掉。你瞧,我以前从没喝醉过,可我发现很难管住自己。酒瘾上来的时候,我很难对自己说个‘不’字。我知道两个当中必须有一个被打倒——要么是酒鬼,要么是杰里·巴克。我说,倒下的不应该是杰里·巴克,有上帝在帮我。我挣扎了很长时间,我想得到所有的帮助,直到我想改掉这个坏习惯的时候,我才知道它有多顽固。珀丽耐心地照顾我,给我吃好吃的东西。酒瘾上来的时候,就给我喝杯咖啡,吃点薄荷,或是读会儿书,那对我很有用。有时候,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你是要戒酒呢,还是要失掉自己的灵魂?是要戒酒呢,还是要伤珀丽的心?’感谢上帝,还有我亲爱的老婆,我终于甩掉了我的枷锁。十年来我从没碰过一滴酒,也从没想喝过。”
“我要下决心试试看。”格朗特说,“要是连自己都管不住,那真是够可怜的。”
“那就试试吧,管理员,试试吧。你决不会后悔的。我们车队那几个可怜的家伙要是看见你戒酒,也会受到影响。我知道,要是办得到的话,有两三个家伙正想远离酒馆呢。”
一开始,上尉恢复得挺好,可他毕竟老了。以前也只是靠他惊人的体质,加上杰里的悉心照顾,他才拉了这么久的出租马车。现在他的状态不比以前了。兽医说,他治好了以后还可以卖上几英镑。可是杰里不答应!为了几个钱,把这么好的老伙计卖去干重活,让他活受罪,会玷污他以后赚的每一个钱。他觉得,为了这么好的伙计,自己所能做的最仁慈的事,就是把子弹准确地打进他的胸口,让他永远不再受苦。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让他安度晚年。
第二天这事就定下来了,哈里把我带到铁匠铺去换上新的铁蹄。等我回来的时候,上尉已经不在了。我和杰里一家都感到非常难过。
杰里现在不得不到处打听有没有合适的马儿。很快,他从一个熟人那儿打听到消息,那人在一个贵族的马房里做下等马夫。他说那是一匹很值钱的马。上街的时候,他到处乱跑,撞到了另一辆马车,把他的主人摔下了车。他自己也擦伤了很多地方,不适合待在那位绅士的马房里了。马夫按照主人的吩咐,想找个买主,把马卖掉。
“我很乐意买下他。”杰里说,“要是这匹马没什么缺点,嘴巴也没有变硬就行。”
“这马没什么缺点。”那人说,“他的嘴巴也很娇嫩,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才闯下大祸的。你瞧,他脾气本来就很急,最近天气又这么坏,他没机会出去活动。所以出门的时候,他就像个气球一样跑得飞快。我们的管理员(我是指那个马夫)给他戴上马具,尽量系得又紧又牢,还有马颌缰、勒马缰绳和一个尖锐的马衔,缰绳是系在最底下的衔铁上。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马儿才会发疯。他的嘴巴太娇嫩,脾气又太急了。”
“很有可能。我会过去看看。”杰里说。
第二天,急性子——那匹马的名字——来到杰里家中。他是匹漂亮的棕色马,浑身上下没有一根白毛,个子有上尉那么高,脑袋长得相当漂亮,才只有五岁。我友好地欢迎他的到来,想跟他拉近距离,可我没问他任何问题。第一天晚上,他很不老实,没法躺下来睡觉。他猛拉穿过马笼头的绳子,乱撞靠着饲料槽的木块,弄得我没法睡觉。可到了第二天,拉了五六个小时的出租马车以后,他回来的时候明显就很安静了。杰里拍拍他,跟他说了一大堆好话,于是他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了。杰里说,给他一个舒服的马嚼子,让他有足够的活干,他就跟羊羔一样温顺。世上没有绝对的坏事。尽管那位老爷失去了价值一百多尼的心爱之物,可一个出租马车夫却得到了一匹强壮的好马。
急性子觉得自己沦落到拉出租马车的地步很没面子,他讨厌站在停靠点排队等客人。可到了这个周末,他承认,能让嘴巴舒服一些,让四肢轻松一点,确实不错。毕竟,比起把马儿的头和尾巴紧紧地拴在马鞍上,干这活儿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丢脸。实际上,他干得挺不错,杰里很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