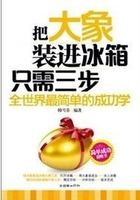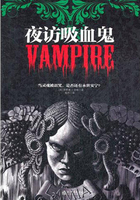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
七七事变,不只是公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的枪声。它是狡黠的日本军人政府预谋已久的一个阴谋。
1937年的6月,与北平几乎同一纬度的日本东京,在军政要人中间,悄悄地传递着这样一条消息: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为了搞清楚这个消息,1937年6月26日,在北平,出现了一场特别的会晤。
日本要人口中的柳条湖事件,是中华儿女心中永远的伤痛。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1年9月18日夜,精锐的日军主力——关东军,自己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贼喊捉贼的关东军当局,反而把污水泼到了无辜的中国军人的身上。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柳条湖事件,成为吞并东北的序幕。1932年2月,东北重镇哈尔滨沦陷。短短四个月,整个东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人的占领地。而日本当局,为了掩人耳目,扶植了溥仪,“伪满洲国”破壳而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颗毒瘤。
九一八,由此成为改写中国近代史的一天。柳条湖,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地方,却成为亿万国人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一幕。每年的9月18日,东三省都要拉响警笛,警世后人。
警笛响起后,人们仿佛重温了历史上的灾难。东三省丢失了,张学良将军一生背负上沉重的历史债务。将军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依旧难忘昔日的耻辱。而在东瀛日本,右翼政客却企图篡改历史教科书。难道柳条湖一幕要在北平再次重现吗?日本人真的能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流吗?北平会有第二个张学良吗?
让我们把历史的摄像机对准1937年初夏闷热的北平。
北平城内的达官贵人依旧是歌舞升平,霓虹灯下的俊男靓女依旧沉溺于甜蜜之中,街头的黄包车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
而实际上,善良的北平人不知道,一场改变他们生活的惊雷就要炸响。我们从电视剧《大宅门》的白府的诸位老少爷们与往日无二的悠闲生活上,看不出他们生活中的任何波澜。
6月26日,北平前门。这里依旧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作为北平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前门永远是北平城的一张名片。
一位气度不凡的高僧,带着一行人马,悄无声息地下榻到前门六国饭店。
能住进北平最豪华的六国饭店,自然不是一般的小和尚。这位高僧,便是日本佛教中最大的宗派之一——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法主大谷光瑞。
僧俗本两界,似乎不应过问红尘中芸芸纷扰。大谷光瑞缘何不甘寂寞?
在中国,僧人介入政治,自古就为大忌。近代中国,惟西藏的藏传佛教,宗教领袖可以成为政府官员。在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列岛,佛教在民众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日本佛教虽然最初发源于中国,但在它被移植到日本这块土壤上之后,经受异国历史文化和习俗的日照雨淋,不断地深入扎根发育成长,最后发展为日本民族的佛教。在奈良时代,佛教成为了国教。各个郡都建立了官方性质的佛学院,而且每个佛学院都建造有佛寺。着名的本愿寺建于1602年,为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之总寺,派下拥有9,000所寺庙及信徒1,000万人,为日本最大佛教教团之一,奉祀阿弥陀佛。
东本愿寺是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的大本营,坐落于京都最主要的街道乌丸通,可说是观光客到京都的必游之地。站在乌丸通大道上向东本愿寺望去,最能感受到东本愿寺的豪壮气势。东本愿寺的御影堂,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里面供奉着净土真宗的创教人“亲鸾上人”。
关于东本愿寺的兴建,有着一段传奇的历史。寺中走廊陈列着“毛纲”,是当时建筑寺院时,为搬运建筑用材,因欠缺绳索,女性信徒乃将美丽象征的长发捐出,将其编织成为粗大绳索,以作为搬运建材之用。毛纲直径40公分,长110公尺,重一吨,堪称当代一绝。
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势力日益扩张,在政府的支持下介入政治,大有政教合一的趋势。净土真宗在明治时期,就为日本帝国进行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效劳。日本净土真宗的创教人亲鸾,他宣扬只要口诵“南无阿弥陀佛”的念佛,就能到“净土”往生,但往生或不往生在于“信”,只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这人就可以往生成佛了。日本净土真宗的主要派系,有西本愿寺的本派和东本愿寺的大谷派。这些佛教的宗派,在明治政府发动甲午战争前后,都从事对日军的慰问和布教活动。
不甘寂寞的日本佛教,也希望在日本的对外战争中有一番作为。对于向中国大陆的布教活动,东本愿寺的大谷派比西本院寺的本派更积极,急不可耐。东本院寺的长老石川舜台,在明治初年即向真宗大谷派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莹倡议,要尽早在中国大陆开展布教活动。其布教的动机,固然说是为宗教上的信念,但这些口颂佛经的和尚们的胸中,也附和帝国政府的野心。他们怀抱着日本要向东亚雄飞的“大志”,决心先教化中国和朝鲜的民心,以使中朝两国的芸芸众生,都听命于日本僧人的说教。
明治维新开始不久,1873年,大谷光莹法主即派东本愿寺僧侣小栗栖香顶和谷了然等人,远赴中国大陆探路,为东本愿寺日后在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地方开设布教所或学堂打前哨。
经过一番筹备,1876年,日本侵略军向朝鲜投石问路的同年,东本愿寺首先来到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在虹口河南路设立了“东本愿寺上海别院”。上海,成为日本佛教界在中国“开拓疆土”这趟列车的始发站。
而日本佛教其他各宗各派,也蜂拥而来,纷纷登陆中国这片他们心中的“乐土”。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宗教机构,积极推行日本佛教独有的教义。日本僧人改造了日本佛教,使其为武士道教精神麻醉的军人政府服务。东、西本愿寺派在华开教的基本目的,便是所谓的“使中华归我真宗”,野心可见一斑。
到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东本愿寺已经在华设立了几百个宗教机构,中国各地布满了各类传教所。这些日本在华佛教机构积极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帮助在华日军与日侨打击中国人。如上海的“日本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无论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1932年的一二八战役,还是在1937年以后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都积极参与支持与慰问在华日军,多次到停泊在吴淞口的日本海军第3舰队上去做慰问道场,甘作***的帮凶。
大谷光瑞何许人也?他是净土真宗本派第二十三代法主。20世纪初日俄战争之际,日本佛教界积极为战争效劳。大谷光瑞为了战争需要在东本愿寺设置了“临时部”,命其弟大谷光朋以及其他许多僧侣担任军队的布教师,从事对日本军队的慰问、布教和葬仪工作。
大谷光瑞本人,也是位不甘寂寞的僧人。在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前的1899年,他便远赴中国西北敦煌石窟等地,取得中国佛教至宝《贝叶经》。义和团事件后的1902年,他率领西本愿寺留学僧,组织西域和印度探险队,调查印度佛迹,总共为三次西域探险队的教团事业出资而负债数百万日元。他以佛教为基柱的国家主义思想,为昭和时期日本帝国侵略亚洲的政策制造理论。
大谷光瑞担任东本愿寺派法主期间,也正是日本军政要人疾呼“西进”时期。其弟大谷尊由1937年担任近卫内阁的拓务大臣后,大谷光瑞感到了几分荣幸,更加积极活动,穿针引线,经常来往于中国大陆、台湾及南洋各地。
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助理的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大谷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满洲、台湾、中国、马来亚、爪哇等地进行周期性的巡回旅行。他对日本的对外发展政策,具有透彻的见解。中日战争爆发后,大谷光瑞担任了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委员,同时就任近卫内阁的参议、顾问。在日本战败的1945年8月15日,他滞留大连,直到1947年才回到日本。
像东条英机等战俘在战后受到了国际法庭的审判,而大光谷瑞这样披着宗教外衣的战争帮凶,却安然无恙。不知道这是不是这场引人注目的国际审判的一个遗憾。
1936年二·二六政变之后,日本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广田弘毅、林铣十郎两届内阁,皆以短命而告终。1937年6月4日,被日本国民认为具有新鲜的魅力而寄予希望的“青年宰相”近卫文,经过短暂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之后,终于沐猴而冠,登上了日本最高政治舞台。
近卫文上任后,日本政府这条“万吨巨轮”,急速“右”转。
6月26日,大谷光瑞正是听说北平有爆发不测事件的可能,故急来到北平打探消息。
大谷光瑞到达北京的翌日,即邀请今井武夫到六国饭店密谈。
寒暄一阵之后,双方即进入正题。
大谷光瑞显得忧心忡忡:日华两国的关系一年比一年险恶,长年纠缠,不得解决。我总希望能有些什么办法来打开这些险恶的局面,现在幸好成立了近卫内阁。近卫家,自从上一代的霞山公以来,比任何人都更关心大陆,作为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那是有深远的来由的:自从近卫当家以后,在他身边又增加了新的大陆问题研究家,他的手下也就有了一个网罗了所谓新旧中国通的智囊团。因此,我想,如果日本政府有意要改变日华关系的话,除了现内阁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说到这里,大谷光瑞脸上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次,我的弟弟尊由入阁担任拓务大臣,我认为这才是实现我的愿望的好机会。我这次来到此地旅行,也无非是想对国策有所贡献而已!
大谷光瑞以一种谦逊的口吻问:不知道金井先生有何高见?
今井武夫吐了烟圈后,徐徐地分析了今春以来北平的形势,说明当地中国人的群众运动的险恶形势。今井武夫分析道:对这种事态放任不管的话,发展下去必然有爆发不幸事件的可能,日本驻军早已不耐烦了,欲有所动作。如果日本真的想避免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对现行的日本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在华北过急地提出经济权益的要求,实有重新加以考虑的必要。
大谷光瑞听后十分着急,认为驻华日军的这种谋略,完全违背和干扰了日本中央统帅部的意图,说:武官先生无论如何回去一趟,把刚才提到的意见向内阁总理大臣议及所有的阁员讲一讲。具体由我来安排。
大谷光瑞就这样立刻离开北平,遂匆匆经由通州和青岛回国。
当大谷光瑞到达东京向陆相松山报告时,正好是战争爆发的7月7日。
这难道是历史的一种巧合吗?
就在大谷光瑞刚刚回国之时,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也被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部长兼陆军省军事课长石原莞尔派来华北。
石原莞尔对于华北的形势颇感不安,要冈本奉命向日本的中国驻屯军传达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坚决按中央意图与命令办事,严令不许搞谋略活动。
冈本来到中国后,找到今井武夫调查情况。
今井武夫对他复述了对大谷光瑞的同样担心与当前华北紧张的局势。
冈本也谈到石原莞尔要他到华北“预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湖事件”。而他在北平、天津旅行一周后,回到东京再向上级报告,却完全违背了事实的真相,乐观地说:“在华北的日本军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来讲,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
当时担任陆军省军务课政策班班长的佐藤贤了也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他在《大东亚战争回顾录》中谈到:当时东京流传着“第二个柳条湖事件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
据今井武夫回忆:那时候,在东京盛传着这样的谣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对此大吃一惊的军部和政府的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似乎就不约而同地派出各自的视察人员。
事实上,这个消息已经流传开来。即使是在华的日本人中,也已经有不少人听到了这个消息。7月1日,正在华北旅行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社长松本治重即访问了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探问此事真相。
桥本群回答说:“我们日本方面多少有些问题。浪人们和一些企图趟浑水捞一票的商人们,唯恐天下不乱。现在天津是谣言飞舞,甚至有人说在7月7日就会出事。”
尽管桥本群将责任推给了日本浪人和商人,但却承认确有问题存在。
华北日本驻屯军磨刀霍霍的同时,中国军人岂能毫无察觉?俗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7月6日,也就是七七事变的前一天,今井武夫到中国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陈子庚的家中赴宴。冀东保安司令石友三知道今井武夫出席,便不邀自来,似乎特地前来打探什么。
筵席在一片欢乐气氛中开始,似乎战争还很遥远。宾客们纷纷举起酒杯,而石友三则显得心神不宁,坐卧不安。他举着酒杯走到今井武夫面前,一番寒暄之后,终于接触到核心话题: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3时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武官知道这个情况吗?
老谋深算的今井武夫摇了摇头,矢口否认: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万一有那样重大的事件发生,日本军是不会不通知我的。
今井武夫很敏感,询问石友三这一消息的来源。
但石友三似乎要对线人保密,无论今井武夫如何询问,就是不肯说出消息的来源。石友三所关心的只是保存实力,他向今井武夫表示:即使日华两国突然发生全面战争,我在北平东郊黄寺的部下,对于日本军队是不会有作战意图的,请你务必设法不要去攻击他们。
今井武夫后来回忆道:石友三的话,就在事件爆发的前一天,从时间上来说是提早了一天,但好像预见到卢沟桥事件似的,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他的话和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中流传的谣言,只是单纯的巧合吗?
石友三何许人也?石友三,吉林长春人。幼年家境贫寒,父亲靠给地主家赶大车维生。石友三早年入伍当兵,后在冯玉祥手下任营长,1924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便提升石友三为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防包头,任包头镇守使。
1926年3月,冯玉祥离开包头赴苏联考察,石友三在晋军的拉拢下投靠了晋军,编为十四师,仍驻包头。同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组成国民军联军,参加国民革命。石友三因背叛冯玉祥投靠晋军,害怕得到报复,乘车前往五原赔罪。一见冯玉祥,石友三马上就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冯玉祥很大度:过去的事,一概不谈,过两天我就到包头去!
10月8日,国民军联军总部迁至包头,石友三脱离晋军编入国民军联军。11月24日,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撤离包头赴陕西,石友三担任了援陕第五路总指挥。但石友三迟迟不动,直到奉军万福麟部逼近包头,他才率部离开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