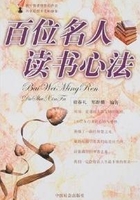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头脑特别清醒。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的同伴想必也和我一样,被悄无声息地送回到他俩合住的舱房里。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和我一样一无所知。想要揭开这个秘密,只能指望将来的偶然机遇了。
我打算离开自己的房间。我盘算着是重新获得自由,还是仍然是一名囚犯?我是完全自由的。我打开房门,穿过通道,登上中央铁梯,昨夜关闭的舱口现在敞开着,我来到潜艇的平台上。
尼德·兰和康塞尔正在平台上等我。我问了问他们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昏昏沉沉地睡着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醒来时惊奇地发现自己又躺在舱房里。
至于“鹦鹉螺”号,在我们看来,还是像往常一样安静,一样神秘。“鹦鹉螺”号正以缓慢的速度行驶在大海洋面上。艇上好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尼德·兰用他那锐利无比的眼睛注视着大海,海上一片荒凉。加拿大人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海面上既没有船只,也看不到陆地的影子。西风呼啸,大风掀起阵阵长浪,使得潜艇明显地摇摆晃动起来。
更换空气后,“鹦鹉螺”号一直行驶在平均深度为15米的水中,这样,潜艇就能迅速地浮上水面。这种不同以往的航行方式,在1月19日这一天进行了好几次。潜艇上的大副此时也登上平台,那句常说的话又在船舱里回响起来。
至于尼摩艇长,没有见到他露面。潜艇所有的人员中,我只见到那位面无表情的侍者,仍旧像往常一样,不声不响地按时给我送饭。
2点10分,我正在客厅里忙着整理笔记。尼摩艇长打开门,走了进来。我向他打了个招呼。尼摩艇长还了我一个几乎是察觉不出来的致意,一句话也没说。我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心里却期望尼摩艇长能对昨夜发生的事做些解释,可他一声不吭。我注意地看了看尼摩艇长,看到他面容疲惫,两眼发红,显然是因为昨晚没有很好睡觉;他的脸上流露出深沉的忧伤,一种真正的痛苦。尼摩艇长不停地来回走动,坐下去又站起来,随意拿起一本书又随手扔在一边,看看仪器也不像平时那样做记录,如此这般,他是一分钟都不能安定下来。
最后,尼摩艇长径直朝我走来,并问我:
“您是医生吗,阿罗纳克斯先生?”
我没有料到尼摩艇长会问我这个问题,以至于我盯着他看了许久,都没有作答。
“您是医生吗?”尼摩艇长再一次问,“您有好几位同事都曾经学过医,比如格拉第奥莱法国生理学家。、摩甘·唐东,以及其他一些人。”
“是的,”我说,“我是多家医院的大夫和住院医师,在我进博物馆工作之前,曾经行医数年。”
“很好,先生。”
显然,我的回答使尼摩艇长感到很满意。但是,我不明白尼摩艇长提这个问题的真实意图,所以等着他提出新的问题,以便根据情况再做回答。
“阿罗纳克斯先生,”艇长又对我说,“您愿意给一名船员治病吗?”
“您这儿有病人?”
“是的。”
“我这就跟您去。”
“请吧。”
我得承认,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位船员的病同昨晚发生的事件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昨天夜里的事至少跟这病人的情况一样,在困扰着我的身心。
尼摩艇长领着我来到“鹦鹉螺”号的艏部,把我带进位于水手舱隔壁的一间船舱。
在这间舱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躺在床上,外貌刚毅,一个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人。
我俯身察看,才发现这个人不光是有病,而且还有伤。他的头部缠着渗满鲜血的棉布,下面垫着两个枕头。我小心地给他解开绷带,这位伤员用那双目光呆滞的大眼睛看着我,任我解开绷带,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伤口非常吓人,病人的头盖骨被钝器给敲碎了,脑髓都裸露在外,脑质也受到了极度的摩擦,流出的鲜血已经凝结成血块,溢出颜色如酒渍。他的脑子不但受到了震荡,还受到了挫伤。病人呼吸微弱而缓慢,时不时的痉挛使他的脸部肌肉扭曲。整个大脑发炎,伤者已失去行动和表达感情的能力。
我为伤者把了把脉。伤者的脉搏已是时有时无,有的身体部位已经变冷,我看他将不久于人世,无药可救。包扎好这个不幸的船员之后,我还为他调整了一下头上的绷带,然后我转身问尼摩艇长:
“他是怎么受的伤?”
“这无关紧要!”艇长支支吾吾地回答,“‘鹦鹉螺’号发生了一次碰撞,撞断了机器上的一根操纵杆,正好砸在这名船员的头上。您觉得他的伤势如何?”
我迟疑着没有说话。
“您尽管讲吧,”艇长对我说,“这个人不懂法语。”
我朝伤者又看了一眼,然后回答:
“最多只能活两个小时。”
“没有救治的办法?”
“没有。”
尼摩艇长的手颤抖起来,几滴泪珠从眼眶里流下来,我原来还以为他生来就不会掉眼泪。
我又观察了一会儿这个生命垂危的人,生命之火正在逐渐熄灭。在笼罩病榻的电光照射下,他的脸色显得愈发苍白。我看见他智慧的额头上过早地刻下了一些皱纹,这大概就是长期以来遭受不幸或贫困所留下的印记。我希望从他两片嘴唇间吐出的临终遗言,能意外地发现有关他一生的秘密。
“您可以离开了,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艇长对我说。
我让尼摩艇长独自留在这奄奄一息的病人舱房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为方才见到的情形深深感动着。整整一天,我始终因某些不祥预感而躁动不安。夜里,我睡得很不好,几次从睡梦中惊醒,仿佛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叹息声和哀歌声,犹如阵阵哀乐。这难道是用那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在低声诉说着对死者的祷词?
第二日早晨,我登上平台。尼摩艇长早已在那里了。他一看见我,就朝我走来。
“教授先生,”尼摩艇长对我说,“今天,您愿意去海底漫游吗?”
“和我的同伴一起去吗?”我问。
“只要他们愿意。”
“我们听从您的吩咐,艇长。”
“那就请你们去换上潜水服吧。”
艇长只字未提那个垂死的船员,或者已经死去的船员的消息。我来到尼德·兰和康塞尔的房舱,把尼摩艇长的建议告诉他们。康塞尔急忙表示同意,这回,加拿大人也爽快地表示愿意同我们一起去。
这时正值早晨8点。8时30分,我们已经穿好海底漫步的衣服,佩带了探照灯和呼吸器。那座双重门已经打开,尼摩艇长以及紧随其后的十来个船员一齐走了出来。这时,“鹦鹉螺”号停泊在海平面以下10米深的地方,我们的双脚踏上了这一深度的海底。
一道平坦的斜坡之后是一处高低不平的洼地。这处洼地大约有15法寻深,与我上次在太平洋海底下散步时见到的情景完全不同。在这个地方,既没有细沙,也没有海底草地,更没有海底树林。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尼摩艇长那天许诺过要带我们去的神奇地方。这便是珊瑚王国。
在植形动物门和海鸡冠纲中,包括了柳珊瑚目,这一目又含有柳珊瑚、木贼和珊瑚三科。珊瑚属于最后一科,这种奇怪的物质先被归入矿物界,然后被归入植物界,最后才被归入动物界。古人将珊瑚当成良药,近代人将珊瑚视为珍宝,只是到了1694年,马赛科人贝桑耐尔才将其明确归入动物界。
珊瑚是聚集在生性易碎、石质珊瑚骨上的微小生物群落。这类珊瑚虫具有独特的繁殖能力,通过芽生来繁衍后代。珊瑚虫既有自身的生命力,又有着彼此共同的生命,可以说它们实行的是自然社会主义。我了解有关这种奇怪的植形动物的最新研究结果。根据博物学家进行的非常正确的观察,这类动物在矿化的同时,还能形成树枝状的结晶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参观大自然在海底培植的石化森林更加令人感兴趣。
我们打开兰可夫探照灯,沿着正在形成的珊瑚礁走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珊瑚礁总有一天会封住印度洋的一部分海面。路旁长满了一些杂乱无章的小珊瑚树丛,上面布满闪烁的星形小花朵。与陆地上植物的生长规律相反,这类扎根于岩石上的珊瑚树杈是从上往下地生长。
灯光照射到色彩艳丽的珊瑚树的树叶上,处处在摇曳生辉,生出万千迷人的景象。我仿佛看见这些圆柱形薄膜细管,在水波底下荡漾。薄膜细管的花冠上带有纤细、娇嫩的触须,我真想采摘几瓣触须娇嫩的新鲜花冠,这些花冠有的刚刚开放,有的则在含苞欲放。这时,体态轻盈的鱼儿迅速地摆动着双鳍,犹如飞鱼一般从花旁一掠而过。当我的手稍微靠近这些有生命的花朵,挨近这类活脱脱的含羞草的时候,花丛便会立即发出警报,白色的花冠就缩进红色的花套里,花朵随即在我眼前消失,珊瑚丛则变成一团圆形的石丘。
这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亲眼目睹植形动物中最为珍贵的品种。这类珊瑚足以同地中海、法国、意大利和巴巴利中世纪至19世纪初指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国。海岸打捞上来的珊瑚相媲美。这类珊瑚中间最漂亮的几个品种,因色泽艳丽,在贸易市场中赢得“血红花”和“血沫”这类富有诗意的美誉。这种珊瑚石一公斤能卖到500法郎。而在这一带海域蕴藏着无数珊瑚打捞者的财富。这种珍贵的物质常常与其他珊瑚骨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名为“马西奥达”的质地密实的珊瑚,在这上面,我也看到一些奇妙的玫瑰珊瑚品种。
没走多久,珊瑚丛变得越来越紧密,珊瑚的结晶体树枝越发粗壮起来。随着我们前进的脚步,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些真正的石质丛林,以及婀娜多姿、千姿百态的长珊瑚枝。尼摩艇长带着我们走进一条阴暗的长廊,平缓的斜坡将我们引向100米深的海底。我们的蛇形玻璃管的灯光,照射在表面粗糙、凹凸不平的天然拱门上面,像分支吊灯一样分布的、火花闪烁的穹隅上面,不时地产生魔幻般的效果。在珊瑚灌木丛中,我还观察到另外一些很有意思的珊瑚虫,如海虱形珊瑚、节肢蝶形珊瑚,还有几簇珊瑚藻,这珊瑚藻有绿的,有红的,外面包裹着一层石灰盐的真正海药,博物学家经过长期争论之后,最终将其归入植物界。然而,根据一位思想家的话来说,“生命正默默无闻地从无知觉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可是并没有脱离其艰难的起点,这大概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行走了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一处海洋深度约300米深的海底,那是珊瑚开始形成的极限深度。这里的珊瑚丛再也不是形单影只、孤零零的珊瑚灌木丛,也不再是不显眼的低矮乔林丛木,而是阔大的森林,又高又大的矿化草木,变成了化石的参天大树。珊瑚同一些漂亮的羽毛花彩状植物汇集在一起,而这类海洋藤本植物,披上各种各样颜色的盛装之后,显得格外煜煜生辉。我们在它们那隐没于海水阴暗之中的高大树林底下自由自在地穿行,我们的双脚踩在由管形珊瑚、脑珊瑚、星形贝、菌状贝、石竹形珊瑚等铺就的金光闪烁的鲜花地毯上。
多么难以描绘的景致啊!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要是我们能够彼此交流各自的感受,该有多好!我们为什么要被禁锢在这具由玻璃与金属制作的头盔里面?为什么我们彼此之间不能用语言进行交流?我多么希望,至少能过上与在水中繁殖的鱼类一样的生活,或者更加理想,过上两栖动物一样的生活,可以长时间的随意往来于陆地上面以及海洋之中,那该有多好!
这时,尼摩艇长停了下来。我和同伴也停止了前进。我回过头来,看见船员围在他们首领的身旁,形成一个半圆形状态。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其中四个人的肩膀上扛着一个长方体的东西。
我们站在一块宽阔的林中空地的中心地带,四周被海底森林的高大树木所环抱。我们探照灯的光束照射在这片林中空地上,折射出混沌的光亮,将投射在地上的阴影拉得特别长。越到空地尽头,灯光越是昏暗,只有几缕微光映照在珊瑚石的棱角上泛出丁点闪光。
尼德·兰和康塞尔靠在我身旁。我们都出神地观看着,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不久,我们将看到一个奇特的场面。我观察着海洋地面,发现有些地方微微鼓起,外面包裹着一层石灰石沉淀物。这种鼓起的小堆排列得很有规律,显然是人工所为。
在林中空地的中央,在一处胡乱堆砌的岩石基座上面,竖起一个珊瑚制作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横档仿佛是用石化血珊瑚制成的。
尼摩艇长做了个手势,其中的一个船员走上前来,在离十字架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下来,并用从腰间取下来的铁锨开始挖坑。
我完全明白了!这林中空地原来是墓地,这个坑就是墓穴,那长方体的东西就是夜间死去的那个船员的尸体!尼摩艇长和他的船员把死去的同伴都埋葬在这处与世隔绝的海底公共墓地。
不!我的内心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震撼!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念头涌入我的脑际!我真不愿意看到眼前所见的一切!
墓穴挖得很慢,惊动了鱼群,鱼儿慌忙四处逃窜离去。我听见铁锨挖掘石灰质地面发出的响声,有时碰着掉在水底的火石,还溅起了火星。墓穴逐渐变长、变宽,不久之后,其深度很快就可以容得下那个尸体了。
那些抬尸人走进墓穴。用白色足丝包裹着的尸体被放进了湿润的墓穴之中,尼摩艇长双臂呈十字形放在胸前,所有被死者爱过的朋友都双膝跪地,做着祈祷……我的两个同伴和我,也都虔诚地鞠了躬,向死者默哀。
坟墓用刚才从地上挖出的碎石块盖了起来,微微地隆起一个坟包。
坟头做好之后,尼摩艇长和船员站起身来。接着,大家又走到坟前,屈膝伸臂,做最后的告别……
葬礼完毕,送葬队伍抄原路返回“鹦鹉螺”号。我们在森林的门拱之下,在那矮树丛中间,沿着珊瑚丛,迎着斜坡一直往上走。
终于,我们能看到潜艇的灯光。那道长长的光线一直将我们引向“鹦鹉螺”号所在的地方。1点钟,我们回到了潜艇。
我刚换好衣服,便立刻登上了潜艇的平台,走到探照灯旁坐下。我脑子里萦绕着许多可怕的念头。
尼摩艇长走到我的身旁。我站起身来,问他: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那人是夜间死去的?”
“是的,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艇长回答。
“现在,他就在那块珊瑚墓地里,长眠在同伴的身旁?”
“是的,他们会被一切人所忘记,但是,我们却除外!我们挖好了坟墓,而珊瑚虫会尽职尽责地将我们的死者永远封闭在里面!”
接着,尼摩艇长用颤抖的双手把脸捂住,但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不禁哭泣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尼摩艇长补充说:
“那里,海洋波涛下几百英尺深的地方,就是我们安静的墓地!”
“艇长,您那些死去的同伴,起码可以安安稳稳地长眠在那里,免受鲨鱼的伤害!”
“是的,先生,”尼摩艇长神情严肃地说,“免受鲨鱼和人类的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