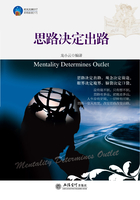好事多磨(二)
中午我过去,办公室的门开着,可人却不见踪影。我找了几张报纸垫在桌上,放下外卖,给他打手机。铃声响了两下就被按掉,有人敲了敲门,我回头,看到他站在门口。
“买了么?”
我点头,把那份皮蛋瘦肉粥递给他。
“你先吃,我很快回来。”他急急转身,我这才留意到他穿着白大褂。
心不在焉地坐下来,打开饭盒,又随手翻开他搁在桌面上的一本杂志,边看边吃。不知怎么,竟想起以前跟他一块儿吃饭,我也是这样一心两用,结果每次都被他好一顿说。
“在笑什么?”他回来,看见我一个人正不亦乐乎。
“没。”我催促他快吃,又问,“你妈妈怎么样了?等会儿我去看看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物事,放到我跟前,“我妈让我转交给你。”
我瞥了那东西一眼,是一个黑色绒面的方型盒子,很精致,也很漂亮。我含着勺子,嘟囔了一句。他抬手轻拍了我一下,习惯成自然,又开始教训我:“别含勺子,这坏毛病怎么还没改掉?”
“你怎么都我爸一样啊……”我小声嘀咕。
他神情似乎有些僵。
我笑了笑,说:“你忌讳这个?我爸妈过世这么多年,我早就接受现实了。”
“不是,”他否认我的说法,“只是突然听你提起已故的人,有些不适应。”
我不跟他计较,打开那个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只翡翠镯子。定睛细看了下,我问他:“你妈妈送给我的?”
“嗯。”他瞄了一眼,“戴上吧,很衬你的肤色。”
我笑着将手递过去,一副理所当然。
他握住我的手腕,将镯子悉心套进去,自己凝神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这是我爸爸买的,想不到她还留着。”
我想了想,抽了张纸巾站起来,“她在哪个病房?我去谢谢她。”
再见郭嘉惠,我被她吓了好大一跳。我记得上一次在明珠大厦那初次见到她,她当时给我的感觉简直是惊艳,相隔不过几月,她竟变得这样憔悴。
看到我来,她很高兴,热情地招呼我到她身旁坐。
我过去检查了下输液情况,依言挨着她坐下,抬手晃了晃,示意她看那个镯子,“很漂亮,我很喜欢。”
“喜欢就好,”她将掌心贴在我的手背上,“选好日子了么?我可以帮忙。刚才问诺言,他说还没定下来。”
“是啊,还没定呢。”她大概以为周诺言故意不跟她说,我低头看见她手臂上有针孔的淤青,莫名一阵心酸,“其实也不急,等您养好了身体再说。”
她不再坚持,顿了一顿,语气略带自嘲:“人上了年纪,手脚就不利索了。”
我忙安慰她:“快别这么想,您还精神着呢。伤筋动骨是意外,一个不留神就会发生,跟年纪没什么关系,我在家里穿拖鞋都会自己把自己绊倒呢。”
她笑起来,虽说精神不济,但笑容仍是很美,透着高贵与娴雅。这样极致的女人,若非事实摆在眼前,我真的很难相信她会做出对丈夫不忠的事来。
我带来的那份皮蛋瘦肉粥还完好地放在一边,在征得她的同意后,我端起粥,一勺勺喂给她吃。她目不转睛地看我,像是在打量什么,害得我这样厚脸皮的人都有些抗不住。
吃过粥,我本想让她躺下休息,但她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我只好陪她聊天。她说了很多周诺言小时候的事给我听,我自然听得很投入,但说的人比我更投入。
我想,她是太寂寞了吧,需要一个人来听她倾诉。
等她输完液已是傍晚,我带她回家,回周诺言的家。她本不愿意,怎么劝说都没用,我灵机一动,说:“阿姨,您搬过来住,过两天等您身体好些,麻烦您陪我去试婚纱。”
她心动了,但仍犹豫,“可是,守信他……”
“阿姨,守信的事,交给诺言处理吧,您就别操心了。”
她还想说什么,我快走了两步,上前去拦计程车,她只好收声。
一路上,她显得有些沉默,我也不说话,掏出手机给周诺言发短信,他去找周守信,顺便收拾他妈妈留在那的行李。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没回,可能正跟某人摊牌吧。
“碧玺,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当妈的太偏心?”她忽然问我。
我正俯身帮她整理客房的床铺,思忖了一下,避重就轻地说:“这也情有可原,毕竟守信从小跟在您身边,人都这样,见得多了心就会偏向些。”
她微微一笑:“琥珀是你姐姐,我跟她相处的时日久了,对她要熟悉一些,其实你们姐妹俩不但长得像,就连那一份讨喜的灵气都有相同之处。你们很会说话,很懂得哄人开心,不过琥珀那是用心良苦,而你却是浑然天成。”
之后我回自己房里上网,脑子里总晃着何琥珀的影像。我跟她已经不止一两次被拿来互作参照物,毫不夸张地说,我从小生活在她的阴影里。那时候,比得最多的就是一张脸,我爸妈不偏心,给她添置衣服鞋袜也必有我的一份,但是这样更糟,穿新衣服,更容易比较出高下。她从上小学起就有男生为她打架,起因是纷纷想跟她同桌。上初中后更了不得,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好几封情书,学长占了大多数,她人生的罗曼史也就此拉开帷幕。我就惨了,小学时代长得又瘦又小,六年都坐第一排,还好皮肤白,总算弥补了一点,不然简直就是营养不良的最好诠释人。我妈为我的个子愁过,背地里跟我爸在研究什么基因突变,曾有很长一段时**我把牛奶当水喝,是喝到想吐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真有成效,但我后来真的长高了,在初二那年全面爆发,前半学年好像是个分水岭,我已经有隐隐向上的趋势,但不明显,那之后我开始猛长个,六个月中大概蹿了五六公分,之后以每年两三公分的速度茁壮成长,上高三毕业班我已经一米七,比何琥珀还高出了三公分,又因为瘦,所以显得特别高挑。为此何琥珀曾耿耿于怀,而我终于觉得扬眉吐气,不过我对自己的身材没什么信心,觉得跟她没有可比性。
这天周诺言很晚才回来,我本想问他谈得怎样,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个男人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我没事瞎操什么心。
结婚的事就这么耽搁下来,周诺言恢复了上班,白天在医院待着还不够,连晚上都经常加班。我觉得他是有意在回避他妈妈,他妈妈也是如此,于是我成了中转站。正好还没出去找工作,每天陪她看看电视,说说笑笑就过了一天,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很轻易地察觉到她的不妥,脚伤是在慢慢好转,可人却越来越憔悴,并迅速苍老,跟初次见面判若两人。而令我气愤的是,她搬过来两个礼拜,不要说何琥珀,就连周守信也没有上门探视过,这种儿子真是白养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打扫她的房间时,无意中找到一张从没见过的病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