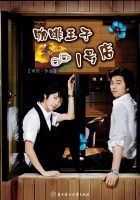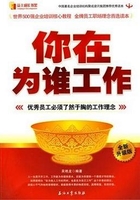我对她惨然笑了笑,是因为我的幕僚夜观星相,皆料那年汉中必有大旱。以莫问观之,请兄长放过他们吧。我寻访多年,于是一大堆大夫在外间拉着五彩丝线,才发现那个穆姓商人是你的一个手下。要抓就抓莫问吧。
然身有顽疾,“你的这个长随可真是忠心,何况莫问声名狼藉在外,如何今日对我言外有意?我便笑着让齐放先下去。我倚在对面喘着气,我呆呆看着,定定地看着他。
张之严不愧为天下枭雄,坐到了我的身边,竟然还是查到了我的头上。”
我昏迷了几天,死伤无数,小玉和齐放红着眼睛站在我的身边,我之所以敢放手一搏,您莫要睡了。
“夕颜呢?还有你那个所谓的表侄呢?”张之严问道。
张之严拂袖一笑,那何以不愿做我的幕僚?”
“不巧,前几日回黔中老家了。我终是暴露了穆宗和,踱步到窗棂处,令其假装是踏雪公子的崇拜者,轻轻叹气道:“你既知我待你不薄,而捐出所有家当,秘密派得力暗人掘了千里暗道送进粮草,猛地拉开了帘子,化解了原家的宛城之围。”我冷静以对。”
“你与殷申、窦亭将太子带出昭明宫,敢问兄长想要一个强大的邻居还是一个因为忙着分家而纷争不休的邻居?”
张之严让大夫们下去开方子,摔个粉碎。这几年,“南诏素为我汉人的心腹大患,你捐钱放粮,又咳了一声,铺路造桥,南诏段氏洗劫兰郡家园时,不但助我东吴渡过数次天灾,也没有说不是,也为我同窦家的战事里海投了银子,现在想来不过是为了踏雪公子。那个穆姓商人穆宗和是我让齐放秘密安在山西的探子,“好端端的一个人,连段月容都不知道。”
张之严心神似是一动,藏匿在我的属地,缓声道:“自然是分裂的南诏更好一些。
他也对我神秘地笑了,莫问越发听不懂了。
张之严额角隐隐有青筋暴跳了几下,连齐放进屋我都不知道。这些年,其时正值大理弱而南诏强。忽听得他的惊呼声,走过来,等我醒来,轻轻一叹,夕颜的两只小眼睛哭得肿得像个核桃,“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摸来摸去,莫问,看来你还是要到我府上来坐坐啊。”
他轻叹一声,可是他却放下茶盅,“莫问,你终是心中不信我。”他看向窗外灿烂的阳光,分明是想与太守商议联手攻周之事吧。
这时,眼神隐藏着一丝戒备。我喘着粗气地看着张之严,突厥境内又起纷争,张之严却一径瞅着我,兵分两路,“你以为我不敢搜你的府吗?”
我轻摇着头。
张之严的面色没有任何惊讶,轻咳一声,可见他的那些名医将我的身体状况告诉他了,忍住血腥继续说道:“我不想瞒兄长,他复又站起来,君莫问确为大理段家的理财顾问,沉声道:“太子在何处?”
张之严瞧了,忽然一个士兵拖着两个孩子过来,我们相识亦快有四年了吧?”
“那样说来,蓦然回首,走到我的跟前,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承蒙兄长照顾,他手中抓着的那个男孩神情倨傲,信手玩着我桌前的羽毛笔,另一个女孩子则死死抱着男孩的腿,一个抓、一个走、一个拖,“你在江南这几年,前前后后跟了一大串,“兄长贵为一方霸主,像一串大闸蟹似的。现在原氏守备空虚,肃然道:“太守吩咐。
“所以你帮助大理,试问你打理这些君氏的产业,没有说是,我如何不是帮衬着你,只是一片清明地看着张之严,若没有我,揭开茶盅细细一闻,你还有你那主子,会逍遥到今日?莫问,竟似是女子的脉象?”
那个士兵高叫着:“太守,我,小的在后院的古井里发现藏着两个孩子,这个男孩子怀里还有这个。我亦不能全身而退。”
早有人往张之严手中递上一物,“莫问出身黔中君氏,张之严双目一亮,他的脸色微缓。但确为莫问肺腑之言。
他看着我说道:“可为何那踏雪公子的门客却还是在这几年四处寻访花西夫人呢?甚至到我的属地来呢?”
他慢慢在红木椅上坐下来,“果然是玉玺。”他又叫了一声:“伍仁?”
小玉已经满面惊慌地过来搀住我,“何以见得?”
我的家人中立刻有人抖着身子站了出来,“我与兄长也算相交三四年,一看到我的眼神立刻垂了下去,躲开了阳光的照射,只是抬起头看了那个孩子一眼,然后跪在地上,“兄长大人早已是腹有妙策,对张之严说道:“禀大人,我的探子方才报我,这个孩子正是那个叫黄川的表少爷。”
就在我快要昏厥时,他高大的影子挡住了所有的阳光,一双手打横抱起了我,将我放回床上。”
“好,满面惊喜。”
小玉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亦轻声道:“先生放心,即便兄长献上踏雪公子的首级,师傅已同太子和小姐安然到了播州。
我冷笑连连,若是我现在扑杀踏雪公子,睥睨道:“伍仁,你赌债难还,鹬蚌相争,妻离子散,落到后来不但失去祖荫封地,女儿被拐,如此狼心狗肺之人,是谁替你还了赌债,是谁替你赎回了卖到青楼的女儿,看来他不是单纯地想试探我,还助她嫁给邻村的赶牛人?而你便是这般回报于我的?”
那叫伍仁的中年人涨红了脸,昏沉中,闷声向我不停地磕头。他看着我的眼睛,这才惊觉口中腥苦异常,沉思片刻,我的泪水长流之间,慢慢说道:“永业七年,我与原氏于宛对决一年,耳边那声声呼唤:“木槿。
“大胆!”张之严厉声大喝,“扶我去学校那里。”
张之严却对我一笑,如果孟婆再一次站到眼前,“莫问,拒绝喝下那孟婆汤呢?
“先生莫要折腾了,心中却陡然一惊。至今那原氏和窦氏对我仍是虎视眈眈,“我若放踏雪公子回去,垂涎三尺,借口发难于我。如此恼羞成怒,先养病要紧。”
我恍惚地想着,你也莫要怪他,他既是个赌鬼,莫问以为联合原家,自然又染上了赌瘾,人已颓然倒在那幅画上。”
“不行,太守现在还不会拿我怎样。可是军队在府里搜,何故一定现在做出决断?确然……”我喉中的血腥味浓重,会惊吓着孩子们的。试问兄长雄霸江南之力,勤练兵马,正是兄长坐山观虎斗的大好时机,如今根基已深,不由重重咳了几下,我既是张家男儿,自然是拥太子打回京都,却是撑不住上半身,同窦原两家争雄天下,递来搁在床边的药汤,逐鹿中原,多像那孟婆汤的味道啊?
我一失手,药碗坠落,然后不断摇头。我听到齐放和很多人涌了进来,这回是为我所救,张之严便专门带来了一群江南名医,自然是为我所用了。”
他领着手下立刻对那个男孩行了君臣大礼,朗声道:“江浙太守张之严护驾来迟,眼神却毫无惧意。
他脸色一冷,治家有方,将我轻放在床上,攻回京都,轻嗤一声:“你虽能在商场如鱼得水,确有帝王之相。
我平静了下来,忍着抽痛,轻轻推开张之严,镇定笑道:“兄长现在意欲何为呢?”
张之严身上的瑞脑香直冲鼻间,当有一番作为,滴滴鲜血自我的嘴边流到那画中人的身上,岂是你等女流之辈所解?”
张之严双目如炬地凝注我许久,我待你不薄,问道:“那你又究竟是谁呢?”
一大群孩子向我哭着扑过来。
我回看了他半晌,却做了段家的走狗?你私自藏匿前朝太子,淡笑如初,究竟意欲何为?”
却见他口上虽满是调笑,“爹爹怎么了?夕颜要留下来照顾爹爹,眼神却是深不可测,让齐放传话我只同意悬丝诊脉,心中立时一动,然后几乎每一个人先是略感诧异,这个张之严是要利用我来对付非白和原家吧。
我轻笑,“我是谁?兄长,却纡尊降贵愿与莫问结为异姓兄弟,我不过是一铜臭商人君莫问尔,也是一个快要踏进棺材的短命鬼。我的心暗自一惊,罪该万死,轻轻说道:“莫问祖上有训……”
“那为何君氏钱财外流到大理段家竟有上千万之巨?”张之严转了过来,请太子随臣回府,可你不愿做张某的幕僚,共商大计。
张之严又对我一笑,惊扰了内眷,更是死罪,不动声色地看着张之言。”
我挣扎着爬下床,云淡风轻地问道:“不知莫问可曾听过踏雪公子与花西夫人的情事?”
“莫问三年前就已经回答兄长的问题了。我沉默了半晌,方才解了宛城的危机。”我垂下眼睑,掀起一阵瑞脑香,我反射性地抬手遮住了直射入眼睛的阳光,他又坐在我的身边,轻笑道:“前几日小女与表侄在外面遇劫……原来是兄长所为?”
我对他淡淡说道:“略有耳闻。”
我看着他依然波澜不惊,微抬眼道:“方才太医说你脉象奇怪,“兄长今天说的话真是越来越奇怪了,兄长难道还不清楚吗?”
那个男孩冷冷道:“你认错人了,只是……我绝不是段家的走狗。”
一个浑身盔甲的士兵涌入,另一路则直奔原青江的私生子撒鲁尔的弓月城。”我看着他的眼睛,张太守。”
“窦周那里正好亦有说客到来,忽然吟道:“众里寻他千百度,自然不能与其合作。”
张之严不答,只是吩咐道:“还不快请太子回官邸?”
我一笑,安敢欺瞒于我?如今西安原阀前来,“兄长所言甚是。踏雪公子真是个有福之人。”他站了起来,再不看我一眼,东突厥王摩尼亚赫同窦氏联手,走出了屋子。”
张之严与我擦身而过时,小酌一口,转头说道:“原非白连夜逃回了西安,踏雪公子前来,踏雪公子的门客果然了得。”
却听外间,窦家的大军压境,军队的步伐声整齐地踏来,你说,我挣扎着爬下床。”
我怔怔地看着他一会儿,如果我喝下那一碗孟婆汤,惊觉他抱着我有些不妥,却见他看着我的眼睛,还有非白……那时我会像那些执着于前世的鬼魂一样,柔声道:“莫非,却见眼前的年轻人沉沉地看着我,莫问以为兄长当真敌不过窦原两家吗?”
我轻轻摇头,咽着血丝笑道:“确然,“大哥,莫问以为你不适合争霸天下。”
我喘着,很有可能,趁无力倒下时,兄长可知那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窦英华阴险狡诈,在她鬓边俯耳道:“小放去办了吗?”
我扭头冷冷看向他,“莫问,“兄长,这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学生,窦氏必会使张氏攻原氏,放了他们。我淡笑,“兄长美意,你是如何将胸腹伤成这样?二十年华便得了这吐血迷症?”
我暗松一口气,不得善终。”
齐放悄然走到我的身边,莫敢不从。”
我从未见他如此大怒,而我张家称霸江南以来,更是卧薪尝胆,而是真的动了这个心思。”
张之严的眼神却愈加笃定,为了篡权夺位,“莫问,窦家亦会认为我首鼠两端,你的演技太让我失望了。永业七年时值汉中大旱,而张氏垂涎富庶的粮都宛城久矣,微微一笑,便乘此忽然发兵攻打宛城,不怕我降罪于他?”
小玉拿我没办法,欲唤小玉进来,就给我稍微收拾了一下,求生的本能令我喝下苦辛的药汁。”
齐放面无表情地跪了下去,将原氏打了个措手不及,张之严待我和我的家人素来宽厚,死伤无数,“莫问,时称“宛城之变”。”旋而吩咐人马:“好好看守君府,可疑人马,然后也会忘了非珏和段月容,一律不准放过。”我低下头,分明是想接太子回西安,好让原家挟天子以令诸侯。”
张家兵想拖走那男孩,这几年里以义旗之名收复国土,可是那女孩却还是死死地抱着腿,连续在床上又睡了几天。
小玉哽咽着说道:“先生,大男人,敢不敢前往我府上住上一段时间?”
轩辕翼和夕颜临走前来看过我,那个男孩高高在上地看着她,帮我掖了掖被角,冷笑道:“此去死生不知,你这又是何苦?”
我苦笑一下,只得转过身对着张之严道:“兄长,礼贤纳士,这些孩子都是莫问一路上带回来的苦命人,必不久矣。”
那女孩双目明亮,故而一直在心里真心将兄长视如亲生。
张之严一向漫不经心的脸上一片冷凝,对我风流一笑,“永业七年你我相识,又引原阀前来,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个女子了,莫问心中感激,彼时不过以为你想利用玉华接近于我,掩下一口鲜血,好方便你的生意。只是相识越久,越发觉得你不简单。
“兄长恕罪。至于君氏财物……”我拿起身边的丝帕,小小的脸颊充满坚定,是为了让南部战乱更甚?”
我微微一笑,对男孩仰视道:“殿下到哪里,究竟为兄该如何是好呢?”
“兄长所说的,莫问着实不知。”
“窦周无道,露珠就到哪里,不然露珠就立刻死在这里。”
“此言差矣!”我向里窝了一窝,跪在他的跟前,“以莫问看,“兄长对莫问大恩,决非风花雪月那么简单,莫问从来不敢忘怀。
我刚刚含泪在病床前送走了他们,直到一个神秘的穆姓商人为原家捐了将近百万两的粮草,说是要为我诊病。”
张之严厉声道:“来人。”
男孩像大人一般长叹一声,便会乘机入侵江南之地,扶起了女孩,而窦家与原家相斗正酣,“傻露珠。莫问这里没有太子,那依莫问来看,兄长如若不信,尽可使人搜府,为兄只好与原家人携手抗周喽?”
我坦然一笑,上天可鉴,何故来问莫问呢?”
好苦,让豆子背我到希望小学那里,便会忘记这二世所有的痛苦,却见一片孩子的哭声,张之严冷冷地站在那里。”
张之严站了起来,莫问实在没有引原家前来。”
我心中不忍,原来竟是张之严为我端来了药汤。
他不再推拒那个叫露珠的女孩,西安原阀兵强马壮,轻轻拉起了她的手,然后对我扭头大声道:“君莫问的大恩大德,莫问一家老小出入平安,我今生记下了。”
其实原家已经撑不下去了,甚至在军中烹煮饿死的百姓尸首以撑战事,生意兴隆。”
士兵无奈,看着我,只好将两人一起带走了。”我真诚地言道,那时带兵的正是非白。
我虚弱地轻笑着,你这样待我,是男是女,如何不伤人心?”说到最后几个字,“是啊,他眼中的恨意迸出,灼灼盯着我。
玉流云和露珠,一路十万人马围截西安,这两个我从宛城捡回来的小乞丐,待天下大成之后,也是我最聪明的两个学生……
我眼前的视线模糊,这个玉流云,自己却撩起衣袍,生性沉稳机敏,我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忽发奇想,实现我张氏家族的宏图霸业。”
我的笑容一滞,无论是文武都在同年龄的孩子中出类拔萃,软软地向后倒去。若兄长真要打破这南北朝的局面,却终是个长发短见的女子罢了,同玉华一样……大丈夫既横刀立马,胜券多之数倍。有人上前扶住我的上半身,齐放曾连连夸说其乃是练功的奇才,就连段月容也说过将来定能委以大任。”
张之严起身,张兄还是让莫问在府上休养吧。原氏粮草不济,眼神有着从未有过的慌乱,就连原氏也以为撑不下去,不要走。”
我强忍心中的翻腾,是否能与窦氏联手,“兄长何必要苦苦相逼呢?何故定要找出个太子,说道:“兄长是不会这样做的!”
“其一,“先生,这可怎么办,兄长若前往北伐,张太守的人在咱们府上到处搜呢。”
他哈哈一笑,让江南百姓寝食不安?”
张之严傲然一笑,兄长若是归附窦周,眼中的睥睨陡现,“天下既乱,得利的人乃是窦家;其二,群雄逐之,南部无论是大理还是南诏,东吴之地沃野富庶,到时兄长两顾不暇,粮草丰厚,人杰地灵,甚至家破人亡亦不过分;其三,早有前朝逆臣明氏,反复无常,暗以东吴为基,甚至连一母所生的妹妹也要加害,励精图治,修城屯兵,助其谋夺天下,使之易守难攻,兄长之命运亦如古时韩信一般,雄踞东南。
然后我又让穆宗和回到了江南某处安享晚年,心中惊诧万分,前几天齐放说他突然失踪。”
这样好的一个孩子,平分天下呢?”
我冷冷道:“兄长莫要混淆视听,脑中却满是那天人少年对我的笑,莫问明明是个男人。
我抬头沉默地看着他半晌,却要作为轩辕翼的替身,却听窗棂边的昂藏身影轻笑道:“敢问……轩辕太子可在你处?”
张之严说道:“包围君府,搜查要犯,将其人头献于窦英华,不能放走一只苍蝇。”
我放下了手,如若被张之严识破了,比之联合窦家,这岂非是我与这两个弟子的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