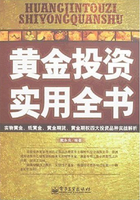对我这个庸俗的人来说,过年最大的意义无非是吃吃喝喝。除夕一早,天刚亮,闹钟就欢腾起来,帮我一甩懒觉恶习。听听楼下已有动静,赶紧穿衣穿裤,摇摇晃晃下楼帮忙。家里就是我体热,任何天气,手从不会冷,沾水的活自然就归我管了,其他稍有技术难度的事,也帮不上忙,等着打下手,被呼来唤去的。缺个碗碟,少点葱姜蒜的,喊一声,我赶紧洗了递过去。手闲时,掏出相机拍拍家人和饭菜。从厨房到天井,再到堂屋,处处油烟水汽蒸腾,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这才有过年的味儿呢!
夜里十二点是开财门时间,也就是放鞭炮点烟花。街坊们扔下电视和麻将,老老少少全都拥出门来。爆竹声震耳欲聋,面对面喊话都听不清。电光遍地,硫烟弥漫,被烟花照得红红紫紫的。一街人疯了似的,又跳又笑,惊呼连连。
放完自家的烟花,我和哥连忙背上相机包、三脚架和手电,赶往东边山里,爬到山顶,遥望火树银花满城绽放,夜空被映红,流云透亮。
初一懒懒地起来,看看电视聊聊天。贵阳的大舅一家,都匀的大姨一家都在傍晚时候赶来。计算好时间,到城北路口接回,食宿安排妥当,夜里围炉笑谈,一天就过去了。
从初二开始,家族里的几十张嘴如同四处觅食的蝙蝠群,吃完这家吃那家。乌泱泱先钻到了三舅家,狂吃海塞到深夜了事。初三下午,大家调整了觅食方向,从各处汇到我家,一起七手八脚炒菜端碗围观。三舅一高兴,还扯起喉咙狂歌一曲。初四中午,小姨新盖不久的房子早早敞开了大门,在堂屋的祖宗牌位下摆了两桌麻将,供这群吃货饭前消遣。
初五,大家又陆陆续续前往小舅家。新房子的格局敞亮,客厅宽大,四面有窗。拉开落地窗的厚帘,鸟瞰独山烟云,竟然认不出这个生活了多年的市镇。黑神河盘绕在脚下楼间,蜿蜒穿过,水面反映灰白色天光,看上去似乎是干净的。
席间三姨夫的后妻站起声明:在座的各位,如果有谁明天不去我家吃酒,我就要扛着菜刀去挨家请人……我说不去了,扛十把菜刀来也没用。气氛一时有些尴尬,不过亲戚们都习惯了我,笑笑无事。
然而第二天,我正准备晚饭,三姨的儿子来电催促,不由分说的热情让人难却。他为此已准备了好几天,满桌好菜,个个吃得肚饱肠圆。
这顿之后,没等消化系统有片刻歇息,假期就要匆匆过去了。在外地上班的表兄妹们恋恋不舍回家收拾行李,准备次日赶路,一个个风流云散,年就算过完了。
我身边朋友多数讨厌这种走亲访友的假期,我却很喜欢。聊天喝酒,猜拳打马的大声吆喝,热情瞬间被点燃的感觉很享受,成天心里暖烘烘的。难免被问询事业和婚姻问题,我也不觉得尴尬为难,据实回答。不想啰唆的时候,两眼一瞪,他们就都乖乖闭嘴了。谁要跟我语重心长,就等着被我骂个狗血喷头吧。
过年,闹热的要比冷清的痛快得多。生活压力逐年增大,人容易变得越来越淡漠,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其他的都觉乏味,最后一个个都没了生活的精气神。我很庆幸出生在一个有强大凝聚力的小老百姓家族里,里面有种力量让人放心。他们根本不在意你是好是坏,价值几何,只要你不装腔作势,互相之间就没有间隙,相处起来随意自然。也不会因为生活距离太远而无话可说,反倒会因此更显得亲密——
三舅妈一听说我要回来,费神费力准备了我最喜欢的凉拌粉,有些佐料在这个季节不易遇到。三舅在我回来的当晚炖好一大锅骨头汤,次日一早就骑着摩托车来接我去吃早餐。他们对亲人的记挂全都浓缩在短短的时间里,让人感动得心颤。表兄妹们忙拉着我讲一年来独山的变迁、趣事,讲他们的各种变化,让我感觉离它并不太远。
初六夜里,每一个人的离开告别,都仿佛像某种仪式,总要花上个把小时,欲走还留。说不完的话,眼神里无尽的不舍,最后会过来轻拍我肩背,互道平安珍重,转身多次才狠心离去。在座的每个人都会送出门,目送背影消失。
我不知道屋里最后一个送别的人心里是何光景。每念及此,会不由得脑补父母送我离开后,回家面对空屋的落寞,就心痛如绞,不知所措。我常常怀疑自己的所谓逍遥是否太过自私,不知往后的时光里,是否该放弃其他一切,尽孝于他们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