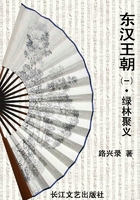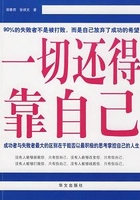陈冰决定这学期只修这两门课,这样既不紧张又有时间打工赚钱。第二天他先去学校重新注册了那两门课,然后去餐馆打工。一进门就看到京姐穿得花枝招展的和鲍勃站在柜台边。京姐说,这小伙子真帅,一双眼就在陈冰身上开掘起来。陈冰本是个大咧咧的男孩儿,竟在京姐眼神下变得不自在。京姐笑得银铃似的,说你来多久了,陈冰说半年。京姐说现在干什么呢,陈冰说上学呗。京姐扬一扬下巴,说,读书很辛苦的,我就读不来。鲍勃笑,说你是什么脑袋,他们是什么脑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京姐笑道,你来时还不是玻璃脑袋,现在也糨糊了。然后问以后有什么打算,陈冰说读完再说,不行就回去了。
京姐说傻孩子,回去干什么?在这里有吃有喝的。熬几年,怎么也出头了。读书能出人头地,打工赚钱,也能有好生活。
其实过什么样的日子,陈冰无所谓。母亲把房子卖了,把
我送到国外,是不是真的替我着想?他想起母亲送他走时脸上放射出的动人光芒。母亲是个不甘寂寞永不满足的女人。
母亲的婚姻是因为一句玩笑。那时母亲还年轻,红润的脸庞,一脑子的理想。下了乡,就高呼口号,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乡里的小伙子恶作剧,说你能真的与我们结合吗?母亲的脸就更红了,她申辩说她是真心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小伙子们就把老实巴交的陈银根推上来,说,你若真结合,就嫁给他,不然,就是假结合。
母亲急得面红耳赤。母亲后来说,她是为理想而结婚的,而那个理想时过境迁,打碎之后不过是一地碎片。
母亲把对婚姻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所有希望,都放在陈冰的身上。换言之,陈冰的身上,负担着两种命运,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母亲的。
“京姐最近又买了个楼。”阿雷一边颠勺,一边对炉尾大声说,是老板的钱吧?炉尾不怀好意地笑着。这是个庸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猜忌、暧昧,幸灾乐祸膜拜金钱。我只是个小蚂蚁,陈冰悲哀地想,一边用悲哀的双手机械地包着春卷。母亲把他送到这里,与其说渴望他学业有成,不如说渴望他尽快安顿下来,把她接过来。身份是最重要的,她说。其实读书也是为了留下来。从这点上,妈妈不同于那些望子成龙
的家长。妈妈是个商人,她对人生的认识不同于酸文假醋的知识分子,她直接,她只看目的,不择手段。一人移民全家移民。这就看你有多大本事。她一边说,一边热切地看着儿子,那眼光灼热而珍贵。在那个眼光中,陈冰不能肯定那是母亲对儿子的爱,还是他只是她达到目的的桥梁。
陈冰在这样的眼神中心中发冷。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字:逃离。
在失落了青春时光之后,母亲的鬓角开始变白,但她的背影却始终挺拔着。陈冰知道支撑挺拔的是什么。在这个不大的城里,很少有她这样的预见。当年母亲是知青队长,因为生病,错过了高考的机会。但她不想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终老一生。她当年的战友,后来上了大学,出了国。她去看过那个幸运儿,红白圆润。她叹息着,眼里充满嫉妒和失落。想当年她在知青点,又瘦又小,像一只永远长不大的灰麻雀。如今麻雀变凤凰。母亲不能容忍的是小麻雀的雍容气质,那是这个小城里的女人身上没有的。母亲没有别的路可走。那个遥远的世界,过去的麻雀如今的凤凰居住的世界,对她来说,充满诱惑。母亲不是一个幻想家,而是一个实干家,就像当年她要扎根农村与农民相结合,就义无反顾地嫁给父亲,就像她想把他送出国,就辞了工作去经商,她是个敢想敢干的实干家。
他肩负的,不只是自己的使命,还在为上一代人偿还某种宿愿,这是不是很讽刺的人生?你从出生开始,就不是你自己。你是五千年文化的独生子,你是希望,你是未来,你是传薪人。
对陈冰来说,加拿大的生活,就像他闯入的一片丛林,或者说,青春就是一片丛林。远离故乡进入另一种新的生活状态的丛林,歧路无穷,也机会无穷。有首诗说得好,森林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结果有了不同的命运。当时陈冰并不知道自己的愿望,其实在某种情况下并不是他的愿望。因为那些愿望和目的,好像都与他的内心无关,他只是母亲想要抵达的目的地一个长梯。但这些对陈冰也无所谓,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以挥霍的,就是青春,而陈冰,有的就是青春。
所以惠子出现在陈冰面前恰好是时候。陈冰不懂爱情。或者说他还不知道真正爱情的滋味。对他来说,女孩子就是那样一种动物,好玩,漂亮,娇气,爱美。但对李亚这样的,他没见过。李亚像个男孩子。你是我哥们儿。他开玩笑地说。李亚也不回答,黑黑的眼睛深潭一样看着他。
那天陈冰喝醉了。于连带九威来试工,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回来的路上,他们搭于连的车走,他和惠子坐在后排,还有九威。车行半路,陈冰能感到惠子的身子一直向他躲过来。他就在黑暗中冷笑一声。他不用看就知道九威的小动作。他就是想吃惠子的豆腐。都结婚了还胡扯什么?陈冰对这种男人充满不屑。很无耻是不是?好,我就让你看看。陈冰伸出一只胳膊,一下子就把惠子搂在怀里。
惠子虽然没想到,居然也没躲闪,就顺从的偎在陈冰的怀里。一瞬间车内很静,九威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突然有人横刀夺爱,看陈冰面带冷峻,目光里夹带着明显的挑衅,心里暗暗盘算一下,论个头,他绝不是陈冰的对手,更主要的,是陈冰眼中那股子杀气,让他明白这小子不是等闲之辈。只好讪讪地缩回手来。一路无话。
于连从后视镜里看到这一幕,心里很是赞叹陈冰的仗义。他其实也把路线计划好了,第一就送走了九威。
惠子下车时,小声对陈冰说,给我打电话。
陈冰回家就睡了。睡得很踏实,根本就没想这件事。倒是惠子,没睡安稳,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就去买菜,然后认真地做起菜来。然后给陈冰打电话,说要给陈冰送饭去。
当中午他们坐在学校的餐厅吃饭时,惠子问陈冰,你怎么没给我打电话?陈冰只是笑笑。窗外的街上车水马龙,惠子却只管望着陈冰的侧影看,陈冰的眼睛在与她相对了一刹那,马
上就躲开了。
如果是在国内,陈冰想都不想就会拒绝。惠子不是他喜欢的那种女孩儿。
但是,这次,陈冰没有拒绝惠子的示爱。
按照于连说,惠子是一个潜在的移民。惠子19岁只身来到蒙特利尔,如今三载,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明年,她大学毕业,就可以申请移民了。
如果和惠子结婚,陈冰就可以留在这里。这是妈妈的愿望,也是她的计划。陈冰知道如果妈妈知道会笑开花,这可比她预计的来得早啊。
只是,陈冰爱惠子吗?
有天惠子问他今后的打算,陈冰说不知道。惠子就说,你若愿意,我可以帮你留在这里,陈冰在惠子的眼里看到一种复杂的情愫。他知道,惠子是爱他的,也知道他并不爱惠子。惠子这样说,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好像原本柔软的衣服里突然生出不知名的物件,硌得他坐卧不宁。但他没有拒绝。
惠子把钥匙给陈冰时,陈冰很游移。
不安——陈冰后来回想那段日子,试图用某种概念来解释这种感觉时,他最早想到的就是这个词。其实在他遇到了惠子之后,他就生活在不安里。这种不安,有田峰失踪后想要忘记却一直压在他心中的隐隐作痛,还有如何对待惠子感情的不安。我应该如何对待这个女人?她为什么钟情于我?如果我不爱她而同她在一起,是不是在出卖自己?对面这个女人,对我是一种异性的吸引,还是某种看得见的施舍可以让她感到优越?
谣言和传言纷至沓来,有人说遇见了田峰的老乡,老乡说有人在田峰的老家看到了田峰,有人说田峰落魄了,也有人说他发达了。至于田峰为什么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跑回中国,就像侦探小说的悬念,不得而知。陈冰不相信这样的谣言。田峰是个按部就班老实本分的人,如果没有人所不知的原因,他为什么不辞而别?不过,当人们这样说时,陈冰从不插嘴,更不争辩,从心里,陈冰很希望真的如此。这件事很蹊跷,不能往深里想。你想,如果田峰没有回国,就是还在加拿大;如果还在加拿大,警察就应该找到他,如果警察没找到他,他就凶多吉少。可是,谁会愿意往凶的地方想呢?
后来传言越来越多。有人说也许田峰欠了大耳窟的赌债,跟着黑社会跑了,也许他在那一夜遇见一个有钱人,那人愿意带田峰周游列国。或者,田峰在那夜遇见一个心仪美女,满心伤痛,田峰怜其所悲,两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抱头痛哭一场之后,决定隐姓埋名,从此浪迹天涯。
陈冰听了这些,有时会嬉笑,有时会冷笑,有时心里竟顿生羡慕。想象无论田峰周游列国也好,浪迹天涯也罢,倒是摆脱了俗世的烦恼,一门清静去了。
这样想着,就感到自己身陷囹圄不能自拔。惠子对他越是深情款款,陈冰的心理负担越大。走在街上,惠子主动去拉他的手时,他下意识地躲一躲,惠子就看他一眼,眼神很复杂,有点幽怨,更多的却是不屑,那眼神陈冰读得懂,好像说,你搞清楚,是谁求谁。
求别人,还用这种方式。陈冰有好几次,都想独自走掉。
有天他梦见自己跪在尘埃里,惠子高高在上,像电视里卖奶酪的胖女人一样,伏下身把奶酪给他,眼里含着对儿童的施舍。而他在惠子施舍的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呀呀学语的孩童,陈冰醒过来满头大汗。
陈冰回过身,看到惠子睡在他身边。平日因为比他矮一头,他只能看到惠子扬起的脸。这时他却突然发现,惠子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上额窄小,脸颊宽大,鼻子里发出粗重的呼吸。他正望着,惠子竟打出闷声闷气的呼噜。陈冰转过身去,还是能听到那呼噜的时高时低。这可太不像陈冰心目中的弱女子了。陈冰坐起来,惠子毫无知觉。陈冰站起来,站在地中间,茫然四顾。困意依然袭来,他就坐在椅子上,半张着睡眼,望着惠子的脸。后来他闭上眼睛,他想就这样睡吧,不用看任何人,不用等待任何事。只要闭上眼,睡着了,生活就进入了黑暗状态,所有的东西都隐没在黑暗中,包括所有的愿望、欲望、要求,还有不知所措或无所适从。
四
改变陈冰生活轨迹的,是父亲陈银根的电话。陈银根说你妈妈好像有问题了。陈冰说什么问题,陈银根说你走后,她就经常不在家了。陈冰在父亲的话里听出了不祥。陈银根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与妈妈好像是所有东西的两端。如果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妈妈大概已经离家出走了。
那是个寒冷的冬夜,陈银根一觉醒来,发现爱丽走了。陈银根就披衣下了楼,在楼道里昏黄的灯光下,长久地伫立。他的一双眼睛,在愤怒的火焰中充满无尽的悲哀。他站了一会儿,走出门来,在茫茫大雪里疾行,一直走到公交车站。车站没有人,雪花打在路灯上,像一群群绝望的、挣扎着的飞蛾,慢慢地融化着,融化成一滴晶莹的泪水。他想她已经走了,也许有人接她走,也许刚刚过了一辆公交车,她就那样上了车,没有回头。他站在雪地里,让寒风吹透他单薄的衣着,寒冷好像从大地深处生发出来,顺着他的脚,他的腿,一直向上漫延,一直漫延到他的心,他的眼睛,他的头顶。他不知自己冻了多久,只能感到他正变成一桩冰冷的石像。
这时有个过路的老女人突然停下来,望着他说,小伙子,你没事吧?这样冻着会生病的。
开始他甚至没反应过来。小伙子,他以为这是在叫别人。这称呼离他实在太远了。他专注地望一望对面的老人,一条厚厚的羊毛头巾,把她的面孔包得很温暖,他突然想起了他的妈妈。他已经很少与妈妈沟通了。妈妈中风后说话很慢,他的内心越来越没有耐性。有时妈妈还没说完,他就失去了耐性。他显得很粗鲁,而妈妈只是笑笑,笑里有无奈,有时叹一口气。
可是,在这个孤寂的寒冷的冬夜,这个散发着母性气息的老女人,让他感到这世界上好像还有一棵可以抓住的稻草。他冲那老女人点点头,转身沿来路往回走,转身的时候,有两颗冷冷的硬东西从脸上掉下来,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他的眼泪。
那一夜,这座北方的城市,零下30度。
这是一种让人窒息的背叛,这种背叛最早来源于爱丽的夜归。自从儿子去了加拿大,这个家突然空荡起来。陈银根有点不敢在家,家里冷冰冰的。爱丽不在家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长。
在爱情中不能自拔的人其实就是走在一条自己都看不清的不归路上。这条路幽深而绵长,让行走的人们看不到也看不清方向。他曾想过许多种方法,想让妻子回心转意,他自我责备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我对她关心不够。他本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但在这本不浪漫的时刻,突然想到也许用一种浪漫的方法可以解救自己的婚姻。于是他给爱丽买了一枚老玉手镯,那枚手镯动用了他用心栽培的股票的本钱。然后他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好像所有事情都可能有转机,昨天的一切只是一场恶梦。当爱丽见到手镯的一瞬间,脸上的敌意就会烟消云散,他则又过起过去20年来循规蹈矩的生活,安稳平静,自在悠闲。他真的不明白爱丽在这样的生活里有什么不满。他甚至想,她是不是被人害了,下了迷药,或有什么难言之隐?
爱丽手里捧着这枚手镯时笑了一下。她想一枚手镯你就想买我的自由了?然而那枚手镯温润古雅,精美动人,她就把手镯戴在手腕上,自我欣赏了一会儿,想起一句古诗,皓腕凝霜雪。王爱丽那年已经50岁,却坚信自己还很漂亮。当她抬起头来看到他的眼睛时,她心里已经明白他的意图。
好像为了给他示好一个答案,爱丽这一晚没有回来。他打电话给她,电话那边很安静,爱丽很不耐烦地说,今晚我们中学同学聚会,大家都不回去了,在一个同学的别墅里玩儿呢,你先睡吧。
陈银根没再说话就挂了。他知道再说也没用,他已经厌倦了这种谎言与欺骗。不说谎行吗?不欺骗行不行?他珍惜的是20年的婚姻,但现在他感到,这种珍惜被利用了。
思前想后,他决定再找爱丽正式谈一次。这次要控制住自己的怒火,开诚布公,摆事实讲道理,还要把道理说透。他想做一个计划,和她约一个优雅的咖啡座或茶室——那地方他从未去过,每次走过时内心还很好奇——环境好气氛自然就会好些。要温柔要体贴,要劝诱。他甚至把要说的话都想好了,他像一个溺在水里挣扎着的人一样挥舞着急促的手臂,既没章法,也没意义,但他挥舞着一种向别人示意的手势,做最后的挣扎。
还有儿子。儿子的归来,是家庭挽回的最后希望了。陈银根本来是咬牙不告诉儿子的,异国求学不容易,陈银根一生没上大学,他把上大学看得很神圣,只要能不打扰儿子,他就不去打扰——但是现在不行了,他撑不住了,他不能让自己妻离子散。
陈冰决定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