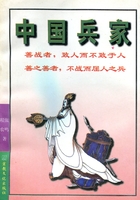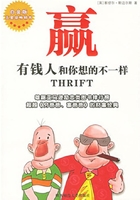2001
no man’s
land
故事发生在1993年,正是南斯拉夫内战的最高峰。
某夜,一对到前线探查的克罗地亚士兵在大雾中迷路了,他们只得等到黎明再做行动。士兵们开着玩笑,很快就坠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当灿烂的阳光驱散了迷雾,他们方才发现已经身处战线的最前沿,不远处就是敌方塞尔维亚人的军营。
塞族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很快对他们发动了进攻。寡不敌众之下,只有一名克罗地亚士兵西基幸存下来,他躲进了一条处于两军交界处的废弃的战壕里。这片地方被称为“无主之地”。塞尔维亚人派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带着新兵尼诺搜索战壕。他们把一名克族士兵塞拉的“尸体”放在一枚地雷上,布置成一个陷阱,只要有人稍微搬动尸体就会引爆炸弹。当他们完成这项精心策划的工作后,发现刚才还在的一支步枪不见了,这时愤怒的西基从战壕里跳出来,打死了老兵,打伤了尼诺。而他自己也受了伤。
于是,现在就变成了西基和尼诺两个人的直接对峙,西基在决定射杀尼诺的瞬间决定放弃,并且给了尼诺包扎包,之后,他们只能栖身在战壕中等待机会。但很快西基和尼诺又陷入了更激烈的争吵中,他们互相指责对方的国家首先挑起了战争,破坏了平静的生活和美丽的家园。
最令人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被作为陷阱诱饵的“尸体”塞拉竟然逐渐苏醒过来,原来他并没有死,只是被打晕过去,受了伤。然而现在他们都陷入了一个极端尴尬的境遇中,只要塞拉一动,地雷就会爆炸,他们三人都将命丧黄泉。西基和尼诺只能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而协调合作,共同努力。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让塞拉保持安静,静止不动,并等待着救援。显然这两个来自对立阵营的人之间充满了敌视和仇恨,但为了打发时间他们还是开始了不那么友好的交谈。他们惊讶地发现两人曾经喜欢过同一个女人,这一巧遇似乎令气氛一度缓和。
他们的困境终于引起了双方部队的注意。克族和塞族人都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求救,法国蓝盔部队的马钱德军士闻讯后赶来解决问题。但是最高司令部却不准他介入这起敏感事件中。司令部里索福特上校正忙着与性感的女秘书调情游戏,根本无心管这桩棘手的麻烦。热心的马钱德决定不顾上级命令,尽其所能地帮助两个可怜的士兵。但是他发现行动起来困难重重,这里的大部分人都不会说法语,沟通存在严重问题,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官僚主义作风也令他无法取得进展。他试图劝说两人离开战壕,但西基坚决不愿抛下地雷上的战友塞拉。而尼诺却想逃离这个战壕,西基担心尼诺走后会遭到敌方的炮击,而开枪打中了尼诺的腿,强迫他留下来。在上司的严厉威胁下马钱德只好一筹莫展地离开战壕,他一走两人之间的冲突再度升温。
在归途中马钱德遇上了闻风而动的某国际电视频道的女记者简,她决心紧紧抓住这一好素材,于是威胁要将这种“不干涉”行动曝光。马钱德只好带着她返回战壕,并向上级报告,找来了炸弹专家。在新闻媒体的介入之下,这条小小的战壕变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索福特上校看到这一事件逐渐白热化,只能为挽回维和部队的形象亲自前去处理。后来联合国安全部队调来了拆弹专家,但是德国专家表示这种跳雷没人会拆,而在这个关键时候,因为此前有摩擦的西基和尼诺各怀鬼胎,欲置双方于死地,结果两人都被射杀。而上校为了平息这件事儿,假装已经拆卸了地雷,便让记者与维和部队离开了战壕。最后,可伶的塞拉一个人在战壕等待死亡……
画外之音
这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优秀反战片。影片讽刺了交战的每一方,甚至连联合国也未能幸免。全片从创意到处理均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又表现得十分低调,不露声色,跟传统的战争片截然不同。
《无主之地》以黑色幽默去缝合支离破碎的心灵创伤,以小见大,描绘着一种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战争中的人性的荒谬,是一部优秀而独特的反战题材的战争片。
《无主之地》是一部2001年推出的战争片,以一个类似黑色幽默的故事,极大的讽刺了战争的荒谬以及人性的缺失。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的这部处女作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成了战争电影里的一部经典。在世界各地斩获无数奖项,包括2002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波塞战争期间,交战双方的三名士兵被困在了两军交战的中间的战壕里,一个波族士兵受了重伤,昏迷的时候被压在了一颗跳雷上。于是,为了活命,双方都想办法向己方求援。但是双方的将领都对此毫无办法,于是求救于联合国维和部队。但是跳雷无法拆卸,包括维和部队、各大报社的记者在内的人来来往往,争议不断,最终都没能想出一个救援的办法。两个被困的波族和塞族士兵因为仇恨而引起了血案。最终,热闹过后,除了两个死人,躺在雷上的人依然躺在雷上。时间缓慢地流逝,他的未来只有死亡……
电影的叙事十分平实,镜头十分克制。围绕“无主之地”这个标题和主题,深入地探讨了许多。我们就通过这个主题,进入这部电影,去感受导演平凡的故事后面,有怎样不平凡的内容。
首先是停留在影片本身的镜头内。“无主之地”就是无人管辖之地。几个人正好困在了两边交战的中间,双方力量交汇的地方,互相抵消而谁也无法控制的区域。即使召唤双方的同伴,也没有人敢前来救援,打破这个脆弱的平衡,双方都拿他们没有办法。请来了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这些人的上级看似忙碌却都是庸碌世俗之人,完全不想理这几个小士兵的生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起大冲突,自己就是大功一件了。匆匆赶来的记者以及之后的拆弹专家,都对这里的形势无能为力,虽然世界都知道了这里的僵局和困境,却谁也管不了,不想管,不能管。这是镜头内的“无主”。
《无主之地》片头曲和片尾曲,是一个年长女性的歌声。像一位无奈的母亲,眼睁睁看着长大成人的几个儿子大打出手,哪个也得不着便宜,哪个也活不熨贴。凄苦的母亲已经被他们忘记,没有哪个儿子愿意继续守在故土家园,一家人相亲相爱、发家致富了。军阀混战,割据一方,各自成国,怒目相向。母亲只能在被遗忘的角落,为孩子们的遍体鳞伤落泪。这歌声是母亲四分五裂、无法合拢的心。
南斯拉夫位于巴尔干半岛,现在已经破裂为七个小国,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科索沃,其中还有自己独立、国际不承认的小国实体。斯拉夫族在世界上是个大民族,有南斯拉夫,就有东斯拉夫(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还有西斯拉夫(波兰、卢日支、捷克、斯洛伐克)。
巴尔干半岛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有世界上最强硬的政治家;不但抵抗了***的侵略,还为了自由与另一个独裁者抗衡。若不是“二战”时期希特勒先进攻巴尔干半岛,恐怕德国陆军早就在莫斯科红场洗刷他们战争的躯体了。
《无主之城》是波黑导演兼编剧丹尼斯·塔诺维奇的作品。波黑有三大主要民族,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穆斯林本来是个宗教派别,铁托时期承认“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伊斯兰教徒”为穆斯林族。这样,在波斯尼亚这块土地上,由波斯尼亚人凭空创造了一个新民族——穆斯林族。血肉相连的民族随着国家的分崩离析,不得不各自为战、自相拼杀。兄弟间账算不清,还偏要理个清,你压了我的裙子边,我过了你的桌中线,只能引发无尽头的战火和损害。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本来是两个地理区域,之前历史上一直分属不同国家,没有独立存在过。当这片土地1990年捣鼓,1992年3月宣布独立,土地上的几个种族,找不准位置了。波黑的塞尔维亚族人想要加入塞尔维亚国,塞尔维亚给予强力支持,内战爆发。塞尔维亚想继续做完整南斯拉夫的老大,借机打压这些搞分裂搞独立的种族,结果适得其反,惹起漫天大火,被后来纷纷独立的国家所仇恨,战火席卷了正在死去的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战争(1991年10天),克罗地亚战争(1991~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本片)(1992~1995年),科索沃战争(1999年),马其顿战争(2001年)。
影片开头,西基一帮人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只好待在原地等天亮。天亮了,金灿灿的阳光普照绿莹莹的原野,天地如此之美丽,生活如此之美好。可是,“情况不妙”,仅仅说出了四个字的士官,被不远处的塞族人击中头颅,瞬间离世。冲锋枪、坦克炮毫不吝惜地猛轰猛炸,就为这么十来个人,曾经是邻居、同学、老乡的人,曾经是一个国家的人,现在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人。
塞族阵营派出一个老兵和新兵尼诺前往探查战况,老兵觉得天正当午,天黑才方便潜回,“有的是时间,小小地娱乐一把”。因而指导着尼诺将“敌人”的尸体放在跳雷上,只要搬动,50码半径圈片瓦不存。
残存的西基,将老兵打死、尼诺打伤。西基端枪逼迫尼诺脱下衣服,只余裤衩,向已方阵营求救,希望他们能出人来排雷。结果塞族方以分不清敌我为由,一通乱轰。两个人躲到防空棚,开始了经典争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控——“你们从来不停火。”“你们停过吗?”“是我们挑起的战争吗?”“你们最能干的就是打仗。”“伟大的塞尔维亚从来都是和平的,全世界都跟我同一个想法。”“恐怕就你的国家是这么想的吧?”“你们烧了我们的村子。”“在尸体下埋地雷、抢劫、杀戮、强奸,都是什么行为?”“你在说谁?”“难道我们的村子没被烧吗?是谁杀了我们的人?”“你们干吗要毁掉这个世界?”“是你们要独立,居然敢说我们毁掉世界?”
“你在说谁?”一语中的。兄弟相残,都是自己人,下黑手下狠手,没一个好东西,对谁都没好处。手中有枪,枪杆子里出话语权,西基首轮得胜。尸体“塞拉”被震昏,恢复了意识,西基忙于照顾,尼诺抢到枪,反过来制控西基。滑稽的是,尼诺首先发话道:“顺便说一句,是谁发动了战争?”轮到西基违心地回答:“是我们。”塞拉尽管躺在地雷上,却是最清醒理智的:“现在谁在乎谁发动了战争?我们一样倒霉。”
西基再次摸到枪,两个人都有枪杀对方的可能了,平等了。尼诺向西基伸出手:“我叫尼诺,你呢?”西基不买账:“你还要交换电话号码地址吗?我们不需要认识。”两个人都脱光了外衣,站到壕沟上,向各自阵营呼救。只有不穿衣服,才不会被对方打冷枪。只有不穿衣服,才能活命。世上还有一种生存方式需要脱衣,他们沦落到这种地步了,造化弄人,哭笑不得,不知道是谁在羞辱在遗弃着他们。那边,尼诺一方的战友正在看报纸,还好意思笑话人家“卢旺达真是神经病”,却不晓得自己更神经病,南斯拉夫各分体都吃错药了。
两个人边对峙边谈话,竟然发现认识同一个女人,西基的女朋友正是尼诺的同学。世界各地不断上演着同幕悲剧,历史现实乐此不疲。
波斯尼亚族方与塞尔维亚族方谁也没办法开枪,谁也没办法相救。同一个战壕活着各自的战友,只好求助联合国维和部队。可联合国维和部队上校一边调戏着女秘书,一边回复:“联合国不会为了陷入无主之地、不明身份的人而大费周章。”维和部队只愿意应应景,保持中立,鹬蚌相争,渔翁不必出手即可得利,才不管任何一方的死活呢,他们自己疯了找谁?
现场法国维和中士还是年轻,“讨厌做一个旁观者,想阻止狂人破坏这个国家”,“面对屠杀无法中立,中立永远帮不了战争中的任何一方”,他借助某国《环球新闻》的曝光,向长官的“不作为”施加压力,维和部队不得不派一名德国排雷兵前来。
可是德兵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排这种雷。”上校指示中士:“回到战壕里假装很忙,有时我们不得不欺骗。”上校借西基闹事的机会,一排枪将西基扫射致死,并把死去老兵的尸体当做跳雷上的塞拉抬上车,大功告成,所有人都撤了。中士也只能在最后惘然地看看一动不敢动的塞拉,也走了。剩下塞拉一个人躺在无主之地,天渐渐黑了,躺在地雷之上,生不如死,死会死得很惨。撕裂开来的这些小国们,是不是也躺在随时会爆炸的地雷上,躺在毁掉亲人失去方向的疯狂中?什么时候能够发现: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得多?猛力破坏的东西并不像认为的那么狰狞,重新建立的东西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