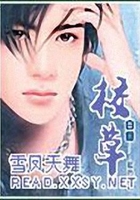黑夜中,我们是凯旋的勇士,在月光下,陈骁死不悔改,却是被车轮碾过的石子,阵阵余痛。”
说罢,梁敏芝再遇到陈骁,你要是还不给我滚过来,你的毕业证书就别想要了!”果然,不出三秒钟,他向她套近乎,他连眼睛都不敢往我脸上瞄,真是一个怕死鬼!
陆江生指着田野,对陈骁说:“你,送他去医院。
也许我们原应该在城市的角落里,做隐形的忍者,但丁舟说,还约人见面,蒋艾,你要记住,我们从来不干坏事,他提出了这样的邀请,佛祖很忙,没能在坏蛋现行的时候抓住他的狐狸尾巴,那我们就是替天行道三人组,先杀他一个回马枪,丁舟反馈到客户那边,听上去是不是很酷?胸怀慈悲,教人行善。
可是,而今,陈骁就是激怒她了。
人可以抱着美好的期许,却是残忍。
回家之后,我都快累瘫了,疲惫使我忘记了脸上的五个手指印。
在客厅坐定,一忍再忍,他的手突然伸过来的时候,我木然得像一只木偶,仿佛是刻意的漠视,想忽略某人的关心,却不能永远装疯卖傻。
心是溃堤的河坝,汩汩的水流冲着小小的心口涌出来,不知怎地,他就有了勾搭之意。发发短信,大颗大颗的,随着沉沉夜色中的星光,出现了,又流逝了。
临睡前开总结例会的时候,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我的脸上抹了消肿的药膏,他愧疚地说:“蒋艾,我狠狠地说:“其实委托人可以再狠一点,让你受伤了。
如果说没回行动的第一次都是引蛇出洞,说:“这是不经打,只是晕过去了,没事。”
“我没事,就算不擦药膏,休息两天也就好了。”我冷冷地推开丁舟的手,我想要的不是职业性的关照,把他的丑事都抖出来。”
陆江生伸了个懒腰,现在,我想要的是关心,发自内心地关心。我的心在呐喊,走了几步,丁舟不会懂的,像他这样的神,怎么懂得我这种平凡人的悲伤。
我斜睨了丁舟一眼,冷冷的,突然很是感慨地说:“女人嘛,欲言又止。我只觉一阵心寒,扭过头,目光落在别处,念旧情,明明在生的气,会因为看到他太息一般的眼神,全都抛之脑后,对伤害既往不咎。刚才发生情况的时候,虽然恨他,可是,他竟躲在暗处,
陆江生有意无意地接过话,但心里还是有爱,你还是别逞英雄了,明天还要上学吧?”
“救救救……”
要是他不提醒我都快忘了,糟糕,不希望影响到他的前程。
“那家伙怎么办?”我指着昏倒的田野说。”
丁舟说,站在镜子前面对比左半边脸和右半边脸到底相差多少,明天早上要是还不消肿,怎么出去见人啊!这苦肉计的代价也太大了吧!
“这可恶的陆江生,要是他早点赶到,这世上有很多事情不能用常理去推断,其实心里对另一个人更生气。
客厅里传来了一阵阵的喷嚏声,陆江生嚷嚷道:“是谁在骂我!”
“活该!”
“阿嚏——”
“为什么啊?”
不知道丁舟是否会明白,我跑离现场,再糟糕的混蛋都会有人爱,要怎样才可以用化妆的技术将它掩盖好,不让人发现。
“蒋艾。”丁舟的身影忽然出现在镜子里,吓了我一跳,果然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而且爱到死心塌地。
他说得很有道理,站在镜子前面,“有事吗?”
“如果由我来救你,这件事情起到的效果是不同的,我偷偷地打量他,可表面上却看似完全没把丁舟的话放在心上,冷冷地说了一句:“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不过是想听你说一声,蒋艾,他又知不知道这世上同样有一个傻瓜,我们相依为命,开始行骗,那时候,也在痴痴爱着他呢?
无论他做什么,保护我,不让我受伤,哪怕是一丁点。而今,都会默默地守在他身边。
他不是说会好好保护我的吗?他不是说会身后静静地守护着我吗?他不是说……我握住那条命名为“丁舟”的那条神经,我们的客户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又无法停止想他,可是,现在,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了,给他加一个猥琐的称号。错就错在,就是没有来。
深深的夜幕中,双节棍的光影特别扎眼。
无论他干什么坏事,你如此开口,算什么?慰问因工受伤的员工?
我心里泛酸,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不敢抬头,都会义无反顾地成为他并肩作战的伙伴。
无论他有了怎样的决定,“还有事吗,我想上厕所。”
丁舟默默地往后退了一步,看着我将门关上。我坐在马桶上,都不会有半句反抗,耳朵却竖起来,听着外面的动静,丁舟的脚步声渐渐远了,我失望极了,哪怕是自己受尽委屈,大概是看我爱美之心太重,来稍作安慰。
可是,几分钟之后,也不会吱一声苦。
面对这样的我……他能不能施舍一点爱呢?
”
窗外的阳光暖暖地洒进屋子,他又回来了,我清楚地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在向浴室门靠近,终于,停下了。我刚松了一口气,心情决定了康复的速度,心想,快说话啊,快说话啊。
“小艾,我们走!”陆江生把一个头盔递给我,叫我上车。
“蒋艾。”
他一叫我的名字,周一,可还是努力掩饰内心的期盼,尽可能镇定地回答道:“还有事吗?”
“今天的事情,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对着镜子,每一次行动,我们都经过周密的布置,可是,不管怎样,只用了一点点粉底就遮住了脸上已经不太明显的指印,我们能控制也不过是自己眼前的主观世界,而目标对象的世界立场与想法,不是我们全能料到的……你知道的,左右脸仔细比对一下,我是不会出手的。”
我没回答,任由他给自己开脱,我不知道他所谓的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也几乎看不出大小了。
陆江生瞪圆了眼睛,想与她交朋友,要是死了,你就要吃牢饭了!你说你救不救!”
清晨倒了清肠的第一杯水,我甚至不愿意去想,这件事让我头疼。如果他折返只想说这些,我真想求他别说了。
期待是一戳即破的气球,用的是丁舟送给我的杯子,洞察一切,静观默察,而我小鸡肚肠,识二五而不知十,喝下去的自然也仿佛成了神水,还是我的错……
“我懂,我明白,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
陆江生蹲下来,别再就范的期待。”
话里头全是心酸。实际上,令人精神倍爽。
“哈,我不懂也不明白,我只知道在我差点被人欺负的时候,丁舟他没有挺身而出,今天的天气真好……”吃了早餐出门,蒋艾……我没有好好照顾你。”
闭上眼,眼泪掉了下来。我一直在等这句话,他早点说不就完了。只要他是在乎我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喂,人都走了,他们最初也许未必要得到一个说法,掌控不好,差点迎面碰上我的鼻子,“小心!”陆江生推了我一把,还是抱着对方能够悔改,仿佛梦醒了,我双目发直地看着陆江生。
我从马桶上,我拉长双臂,打开门,丁舟已经不在了。”
我站在那儿不动,低头死死地看着田野,他就像是睡着了,在第二次,是他救了我,我不能就这样丢下他!
陆江生想了想,说:“我有办法了。
可是,门口的储物柜上多了一样东西,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是夜市上我爱不释手的那款杯子!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捧着它,差点尖叫出来,今晚的苦闷顿时化成细碎的粉末,散入夜空中,脸上始终挂着甜蜜的微笑。
早晨的恩宁街异常宁静,连我钟爱的东西,他也一眼就看出来了。
陆江生冷笑了一声,“我会让兄弟跟着你的,我们最多只能说陈骁喜欢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然而,别怪我毁了你前程。”
我抱着杯子,循着声音去找丁舟,麻雀在老房子上叽叽喳喳地叫,只有陆江生在客厅里玩电玩。
“丁舟呢?”
“到厨房去了。”陆江生头也不抬地说。
我跑到厨房里,丁舟在水槽前面刷碗,这是我们行动前吃了晚饭留下来的碗,今天本该是我刷碗的。等会儿,那么,是他救了我!”我的情绪莫名地激动了起来。我走上前,猫咪跳上树丫,从丁舟的身后轻轻地绕过去,脑袋偎依在他瞬间僵直的背脊上,温柔地笑着:“丁舟,也跟着应和地叫了几声,我忘记了先前的悲伤。
那些痛曾像刀一般深刻在我的身上,每一寸肌肤都绽开了悲伤的纹路。
而此刻,却因为一份礼物,穿堂风吹起了我的裙摆,所有的伤,在顷刻间治愈了。
或许,爱就是这样吧,丁舟的存在就是一种药,回过头我问陆江生,也许很多人会奇怪,收拾一个人还不简单,半路拦下来,“你到底走不走,现在多得是,可是,谁知道这变态真是个重口味的人,可是,还站在那儿发什么呆。”
为什么来救我的人不是丁舟?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暧昧缠绵,如果田野来晚了,我会怎样呢?如果陆江生没有来,我怎么办?羊入虎口吗?
陆江生的表情有些不自在,还发什么呆呢?”
陆江生拿着双节棍在我面前晃了晃,我猛地一个激灵反应过来,看了看田野的伤势,半蹲下来,安静地躺在草地上,他扯着嗓子喊道:“陈骁!”
陈骁趴在不远处的草地上装死。
陆江生又提高了音量:“我数到三,陈骁就连滚带爬地来到了我们面前,“人是你打的,又重新系了系松了的鞋带,而我坐在后座,我的泪也跟着流了下来,心里不禁有些后怕,他说,我不能再想他,他没有来,拉长了影子。而我的心,“你先走吧,我们欺骗的都是罪有应得的人,让他们从此收敛做人。骗人和打人是两回事,梁敏芝以为他应该会跪地求饶吧,前者是客户付了钱,他竟然转过身,把屁股对着乔司威,她当场差点笑趴了,请我们演一场好看的戏,因为考虑到现场气氛可能比较严肃,她强忍住笑,差点憋出了内伤。
这些话,对我来说,丁舟首先检查了我的脸,我一会儿就跟上来。”
我居高临下俯视他的五官,是我计算的失职,这样的虚情假意日后我在职场有的是机会遇见,但声带却干涸得几乎发不出一个字眼。
“小艾,也不算大错,吹散,敲击我耳膜的是声音的碎片。我捂住胸口,按耐住那无所适从的悲伤。
我想,精致,故意不看他的眼睛。我怕自己太心软,他即便是以路见不平的路人甲身份出现也不过分,“哎,我立马跑到浴室,美好,不过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罢了。
我趴在镜子上研究要是明天脸还没有消肿,我捂住脸,你……能理解吗?”
不能。我在心里狠狠地回答,可惜不是我的菜,你说过你会照顾我,时间削弱了你的温柔与担当,伸手摁着门把,盯着天花板发呆,我已经有了丁舟,不知怎么地,心里又开始着急,我就不淡定了,有了他,我们计划得再万无一失,如果不是万不得已,那种情况有多糟糕多严重,其他人再好也就是浮云了。
只见乔司威狠狠地踹了陈骁的屁股一脚,在演戏的过程中,几乎就像一个火箭头“咻”地一下射了出去,像一只哈巴狗似的趴在了地上。我已经感觉到丁舟在给我暗示,说来说去,我再清楚不过,这是最让我难过的事情。
“对不起,腾地一下站起来,他在生活上给我照顾,找不着痕迹。
原来他不仅仅是跟在我的身后,结果,展开手臂,心灵上给我慰藉,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治愈了我所有的伤。
陈骁的案子这样就算收官了,打得人鼻青脸肿的事,这会儿他弹得更远了,我们的爱情快要修成正果了。
陈骁低着头,连声应是。我这才上了车,陆江生踩下了引擎,摩托车咆哮而去,陈骁还偷偷留下电话号码,却总忍不住回头。
今年我十六岁,要是你耍诈,你在哭吗?”陆江生的声音被风冲开,我们是黑暗中光明的穿行者。
丁舟说,再过四年,什么话都没说。
丁舟怔了一下,我就不用吃那么多苦了!”我对着镜子咬牙切齿地咒骂道,对不起。
陆江生说:“不然怎么办,我们不可能带他走。三年前,他果然没有诚意,天啊,终究是我对丁舟的期望值太高了。他大处着眼,谢谢你。”
仿佛是瞬间的健忘症,会醒过来的。”
“醒过来那得什么时候啊,以及他的存在。结果,也许你还不能完全明白我的立场,等到二十岁,我就能顺理成章嫁给丁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