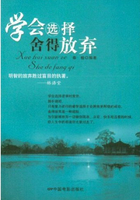类似的梦做了很多次,每次从梦魇中醒来时,睡衣都被冷汗浸湿。
梦的开始是他站在家门口的楼梯上,妻子一只手扶着房门笑着,像正在给他送别。他点点头,转身走了下去。楼道里光线昏暗,脚步声清晰,绕着圈儿下了整整一层,看见这一层的房门也虚掩着,里面透出温暖的光线。这一户应该属于正楼下的邻居。
经过那扇门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头皮立刻麻了起来——半开的门里站着自己的妻子,她正一手扶着房门对自己微笑,似乎在给他送别。他摇摇头,以为自己眼花了,继续往下走。不出意外的,楼下一层也留着门开着灯。快速经过时大胆回头望去,门里正站着自己的妻子。
他开始真正地紧张起来,加快脚步,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往楼下冲去,但是每绕一层,都一定能看见那扇半开的门,和站在门里的妻子。
隐隐约约间,他感到这不是死循环那么简单。妻子的表情在慢慢变化。从一开始的笑脸逐渐变得面无表情。到这几层,似乎已经开始狰狞起来。
他想:她变成了什么鬼东西,为什么要把我困在这里,为什么要用那张脸看我。
又经过一扇门时,妻子的脸色苍白,五官扭曲成很奇怪的样子。
他心里更加疑惑。与其说妻子长出了一张鬼脸,倒更像是她忽然看见了什么鬼东西。
想到这里,他瞬间愣住,心跳几乎停止了。他慢慢地伸出手,摸向自己的脸。
皮肤光滑冰凉,手指从眼洞中伸了进去,就像摸着一个腐烂多年的头骨。他独自从梦中惊醒,感到异常烦躁,心情难以平静。
既因为梦中的恐惧,也因为在梦里出现的前妻。还因为生活里处处的不如意。
他感到自己在被人捉弄,自己一团糟的生活,正在被幕后黑手当作一场笑话。
他深深地觉得,这个梦境就说明,自己已经快要被这个人逼疯了。
这种被玩弄的感觉最早出现在他的童年时期,之后的数十年里,渐渐根深蒂固。
那天他因为考出优异的成绩,被奖励了一辆觊觎多时的玩具汽车。
优质铁壳制造,喷漆匀称精美,还有活动感极为舒适的四个轮子。他实在太喜欢了,夜里干脆抱着它躺上床铺,进入睡眠。
在半梦半醒之间,他感到有一只手伸进了被子,温柔地把小轿车取了出来。
“妈妈,昨天睡觉的时候是你拿了我的小轿车吗?”醒来后他问母亲。
“爸爸,昨天睡觉的时候是你拿了我的小轿车吗?”后来又去问了父亲。
他们都摇了摇头。
父母当然不会相信家里来了小偷,却只拿走了一辆玩具汽车。但小轿车就这样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再也没有被收拾出来。
类似的情况,在他之后的生活里开始频繁地出现。
第一支英雄牌钢笔,最中意的三段变形机器人,生日时大伯送的山地车,画满皮卡丘和小火龙的手绘本。每一样都在某一个不知名的瞬间彻底消失,不留一点儿痕迹,就像从没有出现过一样。
有人在玩弄自己,他想。
把自己的推断告诉父母后,得到了他们的嘲笑:“丢东西是正常的,你要什么,我们再给你买。”
伙伴则提出了其他观点:“这些都被偷东西的小人拿走了。他们藏在你家的地板下面,靠偷你们的东西生活。推走你的山地车,可能出动了他们一支部队呢。”
父母和朋友都安慰不了自己。丢东西这件事上至关重要的一点,无论是用“随机事件”,还是用“可恶的小人”,都解释不通。
每一次丢的,都是他最为心爱的东西。
随机事件不可能如此巧合,小人们也完全没必要如此恶毒。只可能是有人在故意玩弄他,要让他永远生活在失去的恐慌之中。
父亲,母亲,邻居,伙伴。每一个亲近的人都是最可疑的对象。每一天,都是和全世界的暗战。不停怀疑的生活让他不堪所负,得到去外地发展的机会时,他毅然离开了熟悉的一切,带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新生活。
在离乡的火车上认识了叫燕子的女孩儿。她亲切地坐在他的下铺,长长的头发拂在被子上。她说:“哎,你也是平度人?哎,你也去南京?哎,你也读南京大学?”
当时的他不擅长和别人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燕子飞上了中铺,制造了一阵稀里哗啦的声响,然后又轻身荡了下来,手里拿着一只德州扒鸡。这是他最喜欢吃的小吃,他心里一笑。
她却在坐定后擦擦手,把扒鸡撕下半只,递给他说:“吃吧,以后吃不到了。”
他敏感地皱起眉头,并不客气地问:“什么叫吃不到了?”
她一伸手把扒鸡塞到他手里,说:“废话。南京人不吃鸡。他们吃鸭子。”
来到外地,有了燕子之后,生活曾经一度好转起来。
创业初期虽然很艰难,但一步一个脚印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再也没有人可以拿走他的什么东西。在自己最揭不开锅的时候,燕子嫁给了他,给了他无比坚定的信心和力量。数年之后,公司终于良性运转,他也终于和燕子一把椅子、一张沙发地凑齐了自己的家。
再之后的几年,公司业绩高歌猛进,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每一天都活在难能可贵的满足里。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个时候再次丢掉最心爱的东西。
燕子决绝地提出了分手,原因是几年来自己对她的冷漠。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她提着自己小小的箱子迈出了家门,什么也不曾多说。
“就是你,对不对?”他冷冷地坐在客厅,感到自己抓住了世间的真理。
她停下身体,莫名其妙地回头。
“一直以来玩弄我的就是你,对不对?每一次在我最快乐的时候,拿走我最心爱的东西,看着我痛哭流涕的人就是你,对不对?现在,你还把自己也玩儿了进来,嫁给我的瞬间,你就想好了要怎么让我失去你,对不对?”
她叹了口气,摇着头走远。
“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我娶你真是瞎了眼!”他追到门口对她喊道。
她一个字也不想理会。
独自生活以后,丢东西的老毛病变本加厉地出现了。
燕子离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走,屋子里充满了他们的回忆。这是唯一让他欣慰的地方。对他来说,即使在对燕子无比的怀疑和痛恨里,他也依然忘记不了曾经的爱和执着。那段美好的过去能够让他平静。
可是这段过去也在被一点一点地偷走。
第一件就是床头硕大的结婚照。原本的照片上,他笑靥如花地看着摄影师,燕子却弯着眼角看着自己。当时她说,这是结婚照。她和谁结婚,她就看着谁。
一觉起来的工夫,床头就空空如也了。
第二件更加离谱。深夜从公司疲惫地回家,刚想坐下,居然发现家里的沙发不见了踪影。那是一张很舒服的沙发,在家具城首次看见它时,燕子抽了他怀里一根烟,一溜小跑过去,神气十足地坐在上面。然后看着他问:“哟,你还知道回家啊?鬼混去了吧?过来给老娘闻闻!”
他连忙说:“老婆大人啊,不是你让我去买菜做饭给你吃的嘛!”
燕子假惺惺地吐了一口烟圈儿,拍着屁股下面的沙发说:“嗯,感觉不错。就买它了,以后每天回家都照着刚才那条演。”
现在他的眼前空出了一大块,原先摆放沙发的地板上落满了灰尘和不小心掉下去的果皮果肉。
重新回归的恐慌一闪而过。类似的几次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意这件事了。
都是你的东西,想拿走就拿走吧。
都是你的感情,想收回就收回吧。
他有时会在夜里猫在房间的角落,希望能逮到那个回家做贼的燕子。不为了任何事情,只是想再在家里见她一面。
很多个夜晚过去,该少的东西继续在减少,自己却什么都不曾见着。
照例很晚才从公司下班,走到家门口时楼道里已漆黑一片。他熟练地摸出钥匙对着锁眼插了进去,却感觉不对。
如何用劲儿也送不进去,他打开手机灯光照向门锁,又退后照向整扇防盗门。
这是六楼邻居的门,自己多上了一层。
扶着昏沉的脑袋来到楼下,掏出钥匙之前不自觉地又打开手机照了一下。
这扇门自己很熟悉,每天回家时都能见到。这是一单元四楼的防盗门。
冷汗一下子冒出来,空气里每一个分子都让他颤抖。
不信邪地又往楼上跑去,一层之上就是刚才的六楼。
然后再冲下来,一层之下又回到四楼门前。
终于体会到了绝望的滋味。这一次,丢的是整栋房子。
他仍在两层之间来回踱步,好像除此之外再无处可去。皮鞋轻快地落地,在黑暗的楼道间踩出脆弱的响声。
史无前例的失去里,心里的乌云却渐渐清晰。
他想,一直以来,自己可能错怪燕子了。
他想,对于幕后黑手,还有一种最合理的可能。
他仿佛看见那个人此刻正坐在熟悉的沙发上,看着自己最喜欢的书。
花了很大精力配备的家庭音响里,播放着自己最喜欢的碟。
书房里陈列着从小到大最珍爱的收藏:铁皮的小轿车,生锈的英雄钢笔,限量版的擎天柱,贴着灌篮高手贴纸的变速山地车。
妻子从厨房走出来,蒙上那个人的眼睛,往他嘴里塞了一口什么,问:“这是啥?”
那个人说:“德州扒鸡!”
妻子又往他嘴上轻轻凑上自己的嘴唇,然后问:“这是啥?”
那个人说:“我家燕子。”说着嘴角扬起,露出不可抑制的笑容。
他想,希望那个人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不会再弄丢应当珍惜的一切。
然后在那个他早已失去的家里,永怀温暖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