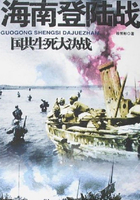1.自找苦吃自得其乐
朱增泉
诗集《享受和平》后记
我从出版上一本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并获得鲁迅文学奖以来,已有七年多没有出诗集了。对于一位尚在写作年龄的诗人,尤其同我诗歌创作高峰期平均每年出版一本诗集相比,这是一个不短的停顿和间隔。这几年,我的主要兴趣转向了散文随笔写作,但没有完全离开诗,每年还断断续续写一点。
这本诗集的整理出版,首先要感谢喜欢读我诗的读者们。这几年,他们在阅读我的历史散文和军事随笔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我首先是一位诗人,并没有忘记我的诗。有些读者在网上贴帖子说,我的历史散文和军事随笔比诗写得更好;但有些读者的跟帖则坚持说,他们还是更喜欢读我的诗。其次要感谢诗歌界的朋友们,几家主要刊物每年都要向我约一些诗稿。说心里话,写约稿就像学生在课堂上写命题作文似的,往往写不好。但我每次还是很认真地写,按时寄给编辑部。一般地说,自己有感而发写的诗,通常会比费尽心力写的约稿诗好一些。当然也有少数作品的情况刚好相反,这属于例外。第三要感谢评论界、学术界这几年开始注意研究我的诗。在当前新诗写作不太景气的情况下,这对我无疑是个不小的鼓励。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的一个观点:少争论,多把功夫放在创作上。任何一位诗人,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诗歌本身来证明自己。
我这本新诗集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所长蒋登科先生带的一位研究生,要写关于我的诗歌创作的毕业论文,来信来电话索要有关资料,其中包括最近几年尚未结集的诗歌作品。我和这位研究生至今尚未见面,但觉得对年轻人的热情应该积极支持,何况人家是不要任何报酬地“吹捧”我呢。于是开始翻杂志,翻报纸,尽可能把这几年所发表的诗歌都收集起来,将剪贴本复印一份,寄给了他。事后翻阅自己留下的这本剪贴本,又东涂西抹地改了一遍,忽生一念,何不借机出它一本?但这几年出版社都对出版我的散文随笔更感兴趣,出版诗集的热情大不如前,因为当前诗集出一本赔一本,出版社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我曾在河北省驻军工作多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我这本诗集。这些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书籍品位高,名声好,交给他们出版,我很乐意。
诗评家、研究者认为,我这几年的诗风有了一些变化。张同吾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过去曾为我的诗歌写过不少热情洋溢的评论,对我诗歌创作的来龙去脉十分熟悉。他为我这本诗集写的序言,除了一如既往对我的诗歌创作给予热情鼓励之外,对我这几年诗歌风格的某些变化也有中肯的评论。就我自己这几年的创作心态和创作感受而言:第一,长诗我是肯定不再写了。要想真正写好一部长诗很不容易,很累,写不动了。第二,诗随人老,随着我老之将至,我的诗风也由激情澎湃开始转向平实祥和,这是我的诗歌跟随我的年龄一起走向“老龄化”的心理反映。第三,虽是这么说,但我对诗歌依然痴情未改,仍在研究和探索之中。当今诗歌之河泛滥,水面上漂浮物较多,泡沫较多,我想到中国诗歌之河的上游和源头去寻找一点清水、活水。于是,我今年静下心来读了一遍《诗经》,又选读了几位唐、宋大家的诗词。唐诗我喜欢李白和白居易,李白豪放,白居易通俗。宋词喜欢辛弃疾和李清照,辛弃疾雄武豪放中含悲愤,李清照清丽婉约中多忧伤,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点,个人情怀的点点滴滴,全都浸泡在南宋羸弱王朝令人忧国忧民的大悲伤中。我回过头去读古诗,但不主张“复古”。我从一开始写诗就表达一个观点,一个时代必然会有一个时代的诗风,如果诗歌世世代代总是同一副老面孔,没人看。新诗要继承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是肯定无疑的,但新诗走到今天“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要想从“复古”中找到根本出路那是不可能的,尽管时下旧体诗词的写作队伍正在日益庞大起来。因为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的老知识分子、老干部队伍日益庞大,他们大多从小受过一些古典诗词的熏陶,退休后将诗词书画作为精神生活的重要寄托,但这并不代表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写得超拔豪迈,当今中国无人能比,但他也不主张年轻人写旧体诗词,毕竟时代不同了。我自己也不写旧体诗词,喜欢读,不会写。我喜欢读的是古人写的诗词,却不喜欢读今人写的旧体诗词,新酒毕竟不是陈酿,总觉得不是那种“味道”。我只想从古典诗词中吸取一些写新诗的养料。所以,我在阅读古典诗词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自我探索和尝试。比如追求平白如话、质朴无华;又比如把情节引入诗,把对话引入诗。这些,我是从唐诗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例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有时也从宋词中借鉴一点句子结构方法。但由于我这几年把主要兴趣和精力转向了散文随笔写作,对于诗歌的这些探索和尝试,未能深入下去。另外,我把平白如话、质朴无华当作自己的诗歌审美追求,有些诗歌作品写得过于口语化了。这种探索的得失成败,我需要回过头来重新思索一下。
最近,有一位记者在采访中问我:“你自己最满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是哪些?”我说:“我自己最满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只有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我自己比较满意的诗歌,是在老山前线写的“猫耳洞奇想系列”,诗情激越澎湃,意象新鲜奇特,没有任何模式,不带任何框框。我自己认为,我那个时期的诗是本真的诗情燃烧,写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诗。后来的几首长诗,例如长诗《前夜》创作于新世纪到来前夕,主要是思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和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挑战。长诗《想念毛泽东》主要是评说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反思“左”的教训,讴歌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大胆创举。这些长诗理性思考多了一点,但我可以无愧地说,我在这些诗中对祖国、对民族、对人类前途命运和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思考,是严肃的、认真的,甚至是痛苦的。我的短诗中也有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去年,应屠岸先生约稿,由他担任主编、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人文丛书中,有我一本《朱增泉世纪诗选》,书名起得有点吓人,是出版社起的,其实它只是一本只有六十几个页码的小册子,选了四十首短诗,旧世纪选了二十首,新世纪选了二十首。由于出版社对丛书有统一的页码限制,最后印出来的是三十九首。这些算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短诗。
前天接到西南大学吕进先生电话,他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又在撰写关于我的诗歌创作的毕业论文,我等待着研究者的批评。
对于我这本“集纳”式的诗集,读者不要寄予太高的期望,切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散文集《天下兴亡》自序
这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本散文集。
阅毕二校清样,我立即给责任编辑姜念光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的这一感觉告诉了他。这本集子我自己比较满意,要感谢姜念光的编辑眼光。我动念出版此书之初,曾对他说:“我想出版一本比较纯粹一点的军旅散文。”他读了我的绝大部分散文作品后认为,仅从某一个侧面,或从某一个角度去选编我的散文,有些可惜了。他说:“必须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整体性的阅读可能,才能让读者更加充分地感受到你散文风格的大气和厚重。”他还说:“你的散文中具有一些其他散文作家不具备的东西。比如历史感,比如观察问题的宏观视野与战略眼光,比如洞察力与预见性,比如文风的质朴与浑厚……”总之,他对我讲了许多“顺耳之言”。
我写散文有点“笨”,用的是“搬石头垒墙”式的写作方法,非把它垒得结结实实不可,恨不得把每一条缝隙都填得满满的,干活不偷懒,却不够灵巧。有一个词叫“笨重”,人们觉得我的散文比较大气、厚重,大概与我写文章的方法比较“笨”有点关系。
我有时也曾想过,我的文章为何也能打动一些读者?我自己找到的答案是,别人用旺火爆炒三鲜,我用老铁锅慢火炖肉,各有各的味道,各有食客喜爱。
我的散文随笔是属于“大散文”这一派的。大,就有一些“大”的标志。例如,我喜欢写一些引人思考的重大问题,习惯于从大处着眼看世界,从大处切入写文章,评说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也喜欢讨论他们的大得与大失,如此等等。
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历史,岁月沧桑,聚散分合,光辉屈辱,成败得失,全在其中,悠久,丰富,深厚。在祖国大地上到处走吧,无论走到哪里,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被某个重大历史题材触动,非写不可,欲罢不能。
我喜欢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析事论人。写了这一面,再写另一面;剥开这一层,再剥下一层;写一个人,既写他的功,也写他的过、他的哀、他的悲。如此等等。
我写秦始皇,以《秦皇驰道》为线索,写秦始皇的大得与大失,写秦朝的速亡教训。但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为何由秦国统一了中国?秦国何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于是我往前追溯一步,又写了《长平之战》《振长策而御宇内》二文,说明秦国强大得足以统一中国,其奥秘在于早在秦嬴政当政之前,他的列祖列宗,自商鞅变法之后的历代秦王,已经走过了百余年强国奋斗之路。我这样来写秦国的巨大成功与秦朝的速亡,前后观照,着眼点全在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长策与大计”上。我觉得探讨一下这类重大历史问题,是有某种现实意义的。
我写长城,发现长城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根装订线。正是依靠长城这根装订线,才把长城南北两边缝合到了一起,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假如把长城这根装订线从中国历史中抽掉,这部古老的线装书将立刻散落一地,难以收拾,理不出头绪。因此,用今天的目光去审视我们一贯以长城为界思考历史问题的思维方法,某些传统观念是值得商榷的,是应作些转变的。泱泱大国,对待本国的历史,应该具有一种历史大度。
我在写作历史题材时发现,古往今来,是南来北往的历史大潮在一波接一波地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古代的历史大潮主要来自北方,一浪又一浪地拍击着长城这道“长堤”,冲击着中原大地。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从秦皇汉武一直到明皇清帝,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在围绕着长城防线的安危,日夜思考着他们的帝业兴衰、生死存亡。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风向为之一转,挟带着海风潮汛的历史大潮主要来自南方,一浪接一浪地拍醒中国。鸦片战争发生于南方,太平天国起自南方,辛亥革命起自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起义也起自南方。中国的千年封闭,是被来自南方的海风打破的。历史要离远了看,才能看到一些大尺度的历史规律。
苏联搞了七十年社会主义,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对于发生在20世纪之末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怎能不令我痛苦地深深思索?为此,访俄期间,我带着强烈的疑问,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苦苦寻找答案,生发种种感慨,写下了一组文章。选入这本集子的《彼得堡,沧桑三百年》《朱可夫雕像》是其中的两篇,有些篇目被一些出版社选入了另外一些选本。
伊拉克战争令我投去格外关注的目光,不仅因为它是一场发生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型战争,调动了我作为一名中国将军的职业敏感;同时,着眼于新世纪伊始的国际政治动向,剖析一下伊拉克这个国家、萨达姆这位人物,也都具有某种典型意义。所幸,我跟踪观察伊拉克战争所写的《观战笔记》一书,虽是政论性、时间性很强的随笔性作品,但我在书中所作的一系列分析和某些预见性判断,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且正在被事态的发展继续印证。
几句题外的话
我一再声明,我是军人,写作只是我的一项业余爱好。文学这东西,一旦“爱”上了它,欲罢不能,难以割舍,把我自己“害”苦了。长期熬夜不说,闲言碎语也在所难免。好在有句老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么将军肚里开辆坦克也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能坚持业余写作到今天。我自己感觉“武”与“文”在我身上统一得不错,几近“完美”;但在有些人眼里,“文”与“武”永远是矛盾的、对立的。这边有人说:“当了领导还去写什么诗,不务正业。”另一边又在说:“他当了那么大的‘官’了,还到文人堆里来挤什么?”忽然宣布我得了一项什么文学奖,记者采访评委时也问:“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位领导,你们才给了他这么高的奖?”那位接受采访的评委火了:“你也太小看我们了!”我借此机会向这位评委表示歉意,我连累了他,让他受了委屈。有些人是讨厌“官”的,一听说是当“官”的写的东西,文章还没有看,就先入为主,认为那是“官样文章”,甚至还猜想有人为我“代笔”或“润色”。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诗歌和散文,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我自己的。
所以我始终认定一条:一位诗人,一位作家,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作品来证明自己。
所以我在写作上始终告诫自己:不以小名喜,不因败笔哀,不为流言弃。
所以我写得比较苦。我这是自找苦吃,乐在其中。
所以我目前想休整一段时间,待精神和精力均好时,看看还能不能再写出点什么来。
2.见证朱增泉
刘立云
做一个文学编辑的最大幸福和快乐,不仅在于能最先读到来自生活中的作品,最先闻到从新鲜的书页中散发出来的那种浓浓的油墨香味;而且还能亲眼目睹一个作家的破土诞生和逐渐成长,亲身分享他们相继获得成功的荣耀。但我要说,在我二十二年从文学杂志到文学图书的编辑生涯中遇到的诗人和作家,朱增泉算得上是个特例,因为他除去给我带来持续不断的幸福和快乐之外,还给我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惊异、震撼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