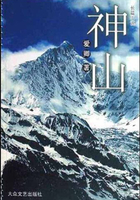孙锦泉
区域文化是在特定的种族、民族、自然生态环境、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等诸多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从自然形态来看,沿海与内陆、山地与平原、边缘与中心,区域之间的差异甚大;从经济形态来看,农耕与畜牧、生产与交换、需求与消费,亦很不一致;从社会形态来看,民族与宗教、历史与文化、民俗与语境,区域之间往往也大相径庭。因之,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不同区域的三大文化范畴内涵与外延、特质与属性亦很不一样。由于这些原因,区域之间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态势,形成诸多的区域文化类型和形态。此外,文化的内敛和张力体现出文化的活性,特别是文化自身的辐射、渗透以及两种文化的交流、互动,甚至多区域文化的联动,促进了相关区域社会的文明和文化的进步。
这就不仅需要我们对区域文化传播的方式、途径、文化交流的内涵以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吸收过程作全方位的解读和认知,而且更需要我们对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不同区域文化在文化撞击的表象后原生态文化的演绎和嬗变过程作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以期全面把握新文化因子融入后的区域文化更新或转型之样态以及对社会发展多方面的影响。
世界文化是成体系的,一般学者认为,自上古以来世界形成了四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就东西方的地域概念而言,其中三大文化体系是在东方,这些文化体系以一个中心向外辐射,形成固有的文化圈,中国文化旁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周邻国家,使之具有文化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印度文化辐射南亚次大陆、南洋及东南亚地区,与中国文化圈有较多的交叉;阿拉伯文化则涵盖西亚、中亚、北非乃至西南欧(中断型)若干国家和地区。东方的三大文化圈其文化的覆盖面积又是西方文化圈(希腊罗马文化圈)的数倍,这些特征,构成了东方文化的多元结构和文化内涵的异彩纷呈。文化本身是活性的、主动的,且彼此间又是互动的,有其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属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圈发展的程度、级次和特质差异,往往制衡着文化的走向。在中世纪先进的东方和落后的西方的格局下,东方文化明显地呈西向流动的趋势。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扩张后的阿拉伯帝国长期与西方毗邻,平分地中海秋色,在新航路开通之前的内海和陆运商业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民族冲突与协调、宗教攻讦与异化、文化碰撞与融汇,总是由阿拉伯和西方两大地域板块和文化圈集中体现出来。东来的中国、印度文化潮流,经由阿拉伯人汇总,甚至消化、吸收和发挥后传至西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拉伯文化既是东方大文化的总汇,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方人更多地通过阿拉伯人接受东方文化,认识东方,同时,保留着神奇东方的想象和传谬。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西方与远东的直接通航,一个“立体的东方”呈现于欧洲,西方遂对东方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开始系统地认识和研究,直接吸收长期以来令欧人心驰神往的远东文化精华,乃至近代在欧洲形成崇尚中国文化的高潮。中世纪西方文化是希腊罗马传统文化的延续,而通过中世纪东方异域文化的不断浇灌、渗透和整型,又形成不完全是传统文化的崭新的西方近代文化。
一、西方语言和语言学的东方源流
东方的语言文字在不同时期,经由不同渠道对欧洲产生影响,西方文字中大量借自东方的外来词汇或由东方词汇演绎和派生而来的西方词汇就是明证。语言文字方面的融汇和影响不是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是地区和国家之间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的折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外来词汇是追溯历史上不同时期文化流向的原始资料和信物。一个地区或国家引入的外来词汇有其内在规律,往往随外来文化潮汐的涨落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各个时期外来词汇的统计和分类,对文化的影响作恰当的评估和必要的定性分析。
在中世纪,东方语言文字对欧洲的影响有四次高潮。第一次是8世纪初,阿拉伯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在几百年的阿拉伯人的统治中,阿拉伯文化直接移植到西南欧。哈克木二世(961—976年)继位是穆斯林在西方统治的极盛时代,阿拉伯语言文化的影响达到了高潮。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将西亚实施的耕作方法传入西班牙的同时,也将大量的农作物引种此地。西班牙语中,遂出现有关西亚的灌溉农业以及农作物的许多专用名词。同时,由于不同民族的混居杂处,阿拉伯人的许多生活用语也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借用,以后的西方国家又从西班牙语中借用和转译成本国母语。
第二次高潮是阿拉伯人于10世纪占领西西里以后。902年,阿拉伯人的艾格莱卜王朝攻占西西里,此后,近两个世纪,西西里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省区,阿拉伯文化经由意大利门户传入西欧。一种文化往往不会因为携带和传播这种文化的统治者统治的结束而中断,新的统治者不得不直面既成的文化格局,推行相应的文化兼容政策,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1091年,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建起诺曼王国以后,阿拉伯文化不同程度地同化了征服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不仅能讲阿拉伯语,还能用阿拉伯文通信,在诺曼人统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不曾稍减,不少的阿拉伯文词汇,特别是手工艺、商业和航海方面的词汇被拉丁文或意大利文借用,以后又转译成法文、英文等。
第三次高潮是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侵期间。西方的十字军在与近东人的作战中学到了东方人的很多军事知识,甚至改变了十字军的一些装备。于是乎,武器、军乐、纹章、徽标、战争等有关的军事术语被引入拉丁文或西方各地区文字。与此同时,当十字军侵入农业经济发达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之后,又认识了不少西方国家并不熟悉的种植作物和瓜果,并引种于西欧,一些先进的生产工具也被西方人使用,这样,又有一些除西班牙文借用之外的有关农业方面词汇被西文借用。
第四次高潮是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殖民国家又从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母语中借用了若干词汇,包括农作物、果木及其他动植物名称、器物和生活用语、地名以及其他专用术语,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人们思想感情的交流更生动、细腻、准确,从而使西方的语言更具活力,推动了近代西方语言文字和语言学研究的迅速发展。
二、欧洲对东方文学成就的吸收
阿拉伯帝国形成以后,横跨欧、亚、非三洲,从地域上看,包容了波斯文化、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埃及文化等若干民族和区域文化,同时,也直接受到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的辐射和影响,阿拉伯帝国的学者,利用掌握的造纸术,通过翻译、考证、勘误、誊录、诠释、补遗等文化活动,特别是阿拉伯历史上的“百年翻译运动”(9—10世纪)将叙利亚文、波斯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梵文和科普特文等多种文字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类著作译成阿拉伯文,经过阿拉伯人的认同和再创造,最终形成包罗万象的阿拉伯文化,因此,阿拉伯文学的包容性使之能够从体裁、内容、结构、写作风格等很多方面在波斯、印度、埃及等国文学中寻根索源。
阿拉伯文学中的“格宰勒”(ghazal),即介于五行与十五行之间一种简短的恋歌,就是仿效波斯诗歌体裁创作的。散文方面由于受波斯文学的影响,一改早期散文简洁、质朴的情味,追求精词丽句的富华风格,留下更多矫饰的痕迹。从10世纪的海麦达尼到12世纪的哈利利,这种风格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于内容和结构方面更是不胜枚举,《天方夜谭》最为典型。素材有东方的各种民间故事,包括古波斯的、印度的、叙利亚的、埃及的等等,而故事的串联结构又主要受印度文学的影响,因为波斯串联式结构的文学作品如《巴赫堤亚尔故事》、《九重霄》等都可以追溯到印度文学的原型。阿拉伯文学中,有大量东方文学译著,有的文学作品经过几种语言的辗转翻译,最后归宗为阿拉伯文学,如初为梵文的《五卷书》,从巴列维语译为阿拉伯语时已更名为《克里莱与笛木乃》了,阿拉伯文学对东方文学的包容性由此可窥一斑。
各种文字的东方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成拉丁文和其他西方文字而为欧洲人所熟识。
西方对东方文学西传的最初反映是阿拉伯诗歌,特别是优雅、温柔的抒情诗歌,能够给基督教徒们以洁雅、空灵、超俗、恬静的天堂意境的丰富想象,故借用阿拉伯诗歌体裁和韵律,改造和发挥后,广泛地应用于基督教的赞美诗,包括圣诞颂歌。而诗歌中的恋爱主题和温柔、浪漫的思想情调,可以在西方中世纪骑士文学中和行吟诗人那里找到。散文方面,13世纪在西欧时兴的寓言、轶事、训诫故事等,同源于印度和波斯的早期阿拉伯作品非常相似。阿拉伯文学中的英雄冒险经历为主题的“麦嘎麦”散文体裁,有助于西南欧英雄与歹徒类故事的兴起。但丁的《神曲》显然受到穆罕默德的登霄故事和麦阿里的《饶恕集》以及阿拉伯天堂、地狱之旅描述的启示,至于来自于东方的文学素材,在西方小说或故事中更比比皆是。塞万提斯所著的《堂吉诃德》得助于阿拉伯手稿《堂吉诃德·台·拉·曼都》的材料,薄伽丘《十日谈》里的东方故事,是他从收集的资料中整理出来的,乔叟《情郎的故事》源出于《天方夜谭》的一个故事。法国诗人拉封丹自己承认,他写作《寓言诗》选用的资料中,有著名的东方寓言故事集《克里莱与笛木乃》。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历史、小说、抒情诗、史诗、颂歌、哀歌、悲歌、悲剧、喜剧等都在《旧约全书》中以各种形式充分展现出来,《旧约全书》为西方人所接受,实际上是西方人对希伯来人的历史、文学以及全部文化的认同和吸收。从《圣经》故事衍生出中世纪最初的宗教文学作品,到《圣经》故事的戏剧化,进而产生出12世纪因宗教瞻礼式的教会戏剧,从人文主义先驱但丁《神曲》中原罪说的观念,到文艺复兴盛期莎士比亚文学中对《圣经》的引录,《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的例证可谓多不胜举。无怪乎一批近代学者如是说:《圣经》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作家的想象力,它的影响不亚于文坛圣匠莎士比亚甚至近代的歌德。
总之,东方文学对西欧的影响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涉及形式、内容、风格、结构、观念和思想。但更多的时候则表现出一种潜移默化的浸润型渗透,这又妨碍我们从文学方面对东、西方文化整合的程度作恰如其分的评估,因为任何计量和统计学的分析方式都无能为力。
三、西方艺术中的东方色彩
伊斯兰教是严格禁止崇拜偶像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义学家们认为,只有真主才有表现人类和动物的特权,无论谁僭越权力将受到无情的惩罚。在一章圣训中先知宣称:“画家(造形者)在裁判日将受到最严厉的处分。”于是,伊斯兰教徒大都不赞成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人体和动物。在这方面,阿拉伯人不仅自身缺乏积极的艺术探索精神,而且还阻滞了周邻国家文化的移入。使得伊斯兰教地区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落后和片面发展的畸形状态。阿拉伯通常的桥梁作用反倒成为东方国家具象艺术文化西传的一道屏障。这是为什么既然有便捷的陆上“丝绸之路”,而欧人却对新航路开辟之前上千年异彩纷呈的中国艺术文化知之甚少的症结。阿拉伯人只是在几何图案和花卉的设计与装饰方面,能够吸收东方民族艺术之长,从而创造一种特有的装饰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传入欧洲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称作arabesque(阿拉伯式),特别在丝绸、纺织、工业图饰的印染设计上被欧人广泛借鉴和沿用,现藏于里昂纺织历史博物馆产于14世纪意大利织锦缎的构图,就是假阿拉伯文字作边饰、典型的阿拉伯花卉装饰风格。
亚洲具象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往往通过欧、亚人的互动游访完成的。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以后,亚洲人物画的特色和画面风格对当时托斯卡纳地区乃至意大利的绘画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恒定的、特别明显的,但仍然若隐若现地持续于文艺复兴的早、中期。从西埃那画家西蒙尼·马尔蒂尼的作品上能感受到中国工笔画和横轴长卷画的某些技法,他作于1328年西埃那市政厅的一幅壁画《基多里西奥·达·福格利安诺》的构图明显受到中国横幅画卷的影响,并且景物布置也颇具中国画风。另一位西埃那画家安布罗其奥·洛伦采提(Ambrogio Lorenzetti)表现城乡风光的宏幅壁画《良政佳绩》无论布局还是画意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清明上河图》,虽然作者不一定看过原画,但完全可能在其他中国艺术品中获得布局构图、写真传神的灵感。
文艺复兴盛期以后,随着欧洲和远东交往的日趋频繁,特别是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一些画家的作品更富有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手法,有的甚至是举世杰作。一些欧洲艺术家认为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的山水底衬,酷似中国山水画中朦胧而有层次的泉石意境。古纽德·马佩(Gunenad Mappe)的山石运笔是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手法的成功效法,他的立幅《圣安东尼之诱惑》更多地透露出中国画的风格。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在仰慕东方的大背景下,更有条件模仿中国画,荷兰使团的格莱尔(P. de Glyer)和凯泽(J. de Kayser)用中国画的透视法绘成了反映中国生活的150张插画,作为报告书的附录,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市场上还出售过以这种透视法则创作的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