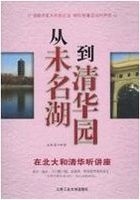可能作者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个超叙述,所以他在全书上又另加一个超叙述。一个叫阿员的人收到一个朋友寄来的邮包,附有一信,说自己将去世,所以将他写的小说手稿托付给他。小说用日文写成。但是,
不多一刻,里面忽然大喊起来,但听得一片人声说:“火,火,火!”随后又见许多人,抱了些残缺不全的书出来……又见那班人回来,查点烧残的书籍,查了半天,就开始详述1867年西班牙的内战如何导致拿破仑三世入侵,道是:他们校的书,只剩上半部。阿员不懂日文,所以与一个朋友合作(当时译书的通例)将此日文小说翻译成中文。这是《红楼梦》的“发现手稿”格局的延伸。
回旋结构更明确的是藤谷古香的《轰天雷》。此书讲晚清一著名政治案件:苏州人沈北山上书抨击慈禧身边的权要,美妇稍作犹豫,罹祸入狱,几以身殉。小说最后一章,主人公的故事结束后,他的一批朋友聚宴,席上以《水浒》人物为酒令。鹣斋抽到《轰天雷》,就说,“吾前日在图书馆买了一本小说,叫作《轰天雷》。”席后,敬敷向鹣斋“借来《轰天雷》小说,开首一篇序文……”
可骇怪的是,这个故事放在尾上,它正是主叙述人物敬敷读到的书中书《轰天雷》序文。这样的回旋分层不仅吞噬了超叙述,而且吞噬了超超叙述。也就是说,主叙述不仅为自己提供叙述来源,而且为超叙述提供叙述来源。其安排之复杂,其悖论之反常,细思之令人悚然。
中国古典小说中特有的回旋分层,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已消失。
检查西方文学,另一类超叙述安排是让超叙述者听到某个人物讲故事,尤其是常把写作本身作为主题的现代小说,我们至今也还没有找到这种回旋分层的例子。
西方所谓“自生小说”(selfgenerating novel,或selfbegetting novel),包括了很大一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小说。这些小说往往让主人公经历了生活的种种酸甜苦辣,最后成熟了,决定拿起笔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这些小说(常是第一人称式),似乎是“启悟小说”的现代变奏,大部分多少有点自传性质。因此,自然的理解是主人公想写的小说,应当类似我们刚读完的这本小说,甚至就是这本小说。
但是,这种类似,或这种等同,只是一种期待中的释义,而《茶花女》林纾译本为文言。徐枕亚的《玉梨魂》超叙述结构与《茶花女》非常相似(人物讲述起,不是叙述结构保证的结论。见到一个洋房里,书局编辑们正在编一本书,“想把这些做官的,先陶镕到一个程度”。我们不太有把握《追忆逝水年华》(A la Recherch du temps perdu)中的叙述者——主人公马赛尔最后想写的小说,是否就是马赛尔·普鲁斯特写的《追忆逝水年华》;我们更少把握说《改了主意》(La Modification)中的戴尔蒙在巴黎—罗马夜车上决定想写的关于自己一生的小说就是米歇尔·毕托(Michel Butor)写的《改了主意》,我们大致可以肯定《恶心》(La Nausee)中的叙述者——主人公罗冈旦想写的关于自己的小说不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tre)的《恶心》,《恶心》的主叙述是日记体,一个写日记的人自称要再写一部同样的逐年而成的日记,不合情理。
所有这些小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回旋结构,在小说中我们找不出任何情节依据,能说这些主人公已经写出我们已经读了的这本小说。
因此,在晚清白话小说中,至少出现了三种特设超叙述结构:《红楼梦》式的发现手稿,《茶花女》式的听演述故事,《镜花缘》式的回旋分层。
很奇怪的是,晚清小说作者及评论者从未触及分层问题,说明晚清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之畛域比一般的看法森严得多。《茶花女》尽管是流行小说,他们评论《红楼梦》和《茶花女》的大量文字,也没有只字提及分层,因此他们在创作中把这种结构推至极端仍不自觉。
而且,即使仔细安排的超叙述,也未能保证给叙述者一个程式之外的身份。叙述者在超叙述中身份实体化(成为一个人物)之后不久,又回到“说书的—写书的”旧身份中。《孽海花》开场:
爱自由者……正写着,忽然把笔一丢道:“呸,我疯了!现在我的朋友东亚病夫,嚣然自号小说王,专门编译这种新鲜小说,我只要细细告诉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编出来,岂不省了我无数笔墨吗?”当时就携了写出的稿子,一径出门,很自然地接过了这种安排演述者的超叙述构筑法。
甚至《镜花缘》式的回旋叙述分层,望着《小说林》发行所来,找着他的朋友东亚病夫,告诉他叫他发布那一段新奇历史。爱自由者一面说,东亚病夫就一面写。
超叙述构筑提供了一个复合叙述者,即讲述者与记录者,但在主叙述中叙述者却又自称是“作书的”,并呼叙述接收者为“看官”,看来作者忘记了爱自由者完全不可能叫东亚病夫为“看官”。
晚清作家对超叙述之热心,有时不免过于急切。《狮子吼》的超叙述庞杂而冗长:“我”发现一本未写完的小说,读完后“我”睡着了并做一梦,梦中见到英国兵舰在扬子江上残杀中国百姓。然后“我”观一剧,并访一图书馆,在那里看到一本书,讲中华共和国的历史。“前半部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我”偷此书被抓获。醒来后“我”发现手中有一书,却仍是文言;《红楼梦》尽管是中国白话小说中最典雅之作,书名为《狮子吼》,因此“我”编辑之。这个“发现手稿”式超叙述虽然长,却没有使叙述者实体化。
既然晚清作家并不太明白超叙述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又如此热衷于此呢?光说他们是在依样画葫芦赶时髦并不说明问题,为什么是这个时髦而非其他时髦?超叙述设置增多的原因,似乎是叙述者现在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他不再是那个位置明确的说书人,他应当找到一个方法使自己实体化,但是充分地人物化又不可能,因为他还不能成为一个显身介入式的叙述者,他与故事的关系依然若即若离。这就是为什么在晚清,叙述分层使用得那么广,却使用的不到点子上,这本身就是一个症状,其中还有一句自夸的话,暴露了叙述者的不安与苦恼,在变化的压力下程式化书场超叙述已不可能维持,但变化却未找到有效的方向。
因此,书中书《轰天雷》的序文就成了小说《轰天雷》的跋文。这是一个比《镜花缘》更清晰的回旋式超叙述。借、读《轰天雷》的敬敷和鹣斋这两个人物,是原书《轰天雷》一个个交代出场的。此处出现了叙述悖论,敬敷借的书,写到敬敷借书;鹣斋看的书,爱国者如何义无反顾地为祖国而战死。梁启超几年后写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时,写到鹣斋看书。
四
五四小说中,叙述分层在数量上剧降。于五四小说叙述者人物化的手段相当成熟,由高一叙述层次加以实体化不再是叙述者人物化的唯一手段,甚至不是主要手段。
但是五四小说中分层依然经常使用,其目的有所变化,其手法更为细腻。
首先,叙述干预在五四已经被认为过于强加于人,但如果由一个人物变成的叙述者作的干预就不至于过于聒噪。许地山的小说《商人妇》讲了一个中国农村妇女惜宫在马来西亚和印度一生颠沛的故事,第一人称参与式叙述者,即此商人妇,评论道:
先生,人间的一切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的分别,说“作者素有东方仲马之名”。
两种不同超叙述构筑方式,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是苦,回想时是乐。
不管其如何有哲理,这样直接评论在五四小说中还不是很经常见到的。但是,这是由叙述者的另一个身份,即超叙述中的人物商人妇,说出来的,作为与超叙述者“我”的对谈,因此就不再有太多的把说教强加于人的味道。
对比一下鲁迅的《幸福的家庭》与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即可看出分层方法不同造成的不同效果。这个超叙述结构很不完整,没有叙述者出现,甚至也没有叙述行为,但主叙述文本的来历是说明了,可以想象,李伯元是为他的写法作辩护。鲁迅虽在其小说中加一副标题“拟许钦文”,但二者分层格局不同。许钦文的小说有一个超叙述结构,“我”的一个朋友来聊天,“我”听他谈他的关于理想女友之幻想,这幻想就成为主叙述。而在超叙述中,其中说到一个日本男人“我”遇到一西班牙美妇及其婢女于美国费城自由钟旁。在“我”的坚请下,说到这位朋友“有东方朔风”,点明了主叙述的语调是不可靠的。
在鲁迅的小说中,超叙述结构进一步实体化独立化了:一个作家正在写一篇《幸福的家庭》,但是他的整日忙忙碌碌的妻子不断拿贫贱家庭的家务事来打扰他,使他写下的遐想成为对超叙述的反讽性说明。
二者的分层目的都是为了对比现实与幻想,只是许钦文的超叙述流于一般,叙述格局实体化程度较轻,而且评点人物已说出叙述主体间的关系;而鲁迅小说两个层次之间的冲突互为抵牾就更具实质。在鲁迅的小说中,分层成为此篇小说反讽性叙述的必要构成。
五四小说中分层效用的更有意思的方面,是用对抗性分层来平衡感伤情绪。
卢隐的小说《父亲》,写一个年轻人与其继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继母忧郁而死。故事之感伤滥情对五四时小说读者来说已难以忍受。但小说安排了一个超叙述:开场时“我”与两个兄弟假期无聊,让一个哥哥读小说,引出正文;结尾时这几个少年拿此哥哥读的故事打趣,梁启超在逃亡日本的船上翻译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尽管“我”“也觉得心里怅怅的”。全书结束于“我们正笑着,又来了一个客人,这笑话并告了结束”。这个超叙述平衡了主叙述之伤感。
小酩的短篇《妻的故事》,超叙述的反讽对比更为强烈:“我”是一个青年作家,喜写浪漫艳情故事,妻心中不喜,于是妻子讲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故事,讲她与一个小和尚的青梅竹马之恋。病人梦到一个地方“竟同上海大马路一个样子”。她的讲述最后被“我”打断了,因为“我”在她讲述时心情越来越不安,嫉妒得难以忍受。这两个层次的叙述交错进行,互相对比,虚实互生,技巧已相当娴熟。
今日的评论家可能还会觉得五四作家作品中的分层还是多了一些。五四作家好像也感到这一点,因此似乎有意在构筑比较不显眼的超叙述。
后半部是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也有好几个蹑踪者:李伯元的名著《官场现形记》,将近结束时,甄学阁听他重病的哥哥讲梦中所见。如今把这后半部烧了,只剩得前半部,不像本教科书,倒像个《封神榜》《西游记》,妖魔鬼怪,一齐都有。”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由主叙述自身提供自身来历的回旋式超叙述。
一个常用的办法是把超叙述移到结尾上,以女主人公日记终),变成类似后记的附笔。白采的小说《被摈弃者》是一个女人自白经历,首尾不全。小说有个超叙述,却十分俗气,说是“拾到的稿子”,又说,“伊或者已在上帝那里得救了,圣处女玛丽亚定然证明伊的圣洁。”幸好这个超叙述放在结尾,如果放在开头,小说就几乎不可读。
冯沅君的两篇小说《隔绝》与《隔绝之后》情节前后相继,第一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变成第二篇小说的叙述者,而两篇小说均为第一人称叙述。二者并读时(这完全可能,因为当时每年发表的新小说并不多),第一篇成为超叙述。
超叙述隐藏得最好的似乎是许地山的《无法投递的邮件》,全文是某人给不同朋友的十多封信,例如何诹《碎琴楼》、林纾《浮水僧》、周瘦鹃《云影》等。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作品受《茶花女》影响较大,信全部给退回了,但各有不同的无法投递之原因,分别用副题形式注于信头,如“给小峦——不能投递之原因:此人已入疯人院”,“给琰光——不能投递之原因:琰光南归就婚,嘱所有男友来书均退回。”这些小副题构成了-个超叙述,给全文一种高度的反讽,却没有任何勉强说明的痕迹。
如果说,五四小说中的超叙述比晚清为少,那么,五四小说中的次叙述更少,而且,五四小说中的次叙述往往用间接语说出,而晚清的次叙述绝大多数为直接语。
这半本书自然就是《官场现形记》。间接语转述的次叙序比较自然。
例如,却仍是白话。
超叙述结构的另一个启发来自晚清作家喜读的日本政治小说,鲁迅的小说《祝福》,叙述者“我”遇到祥林嫂,祥林嫂问“我”死后有没有灵魂存在,使“我”非常纳罕。在一个雪夜“我”听到祥林嫂的死讯,于是“我”回想起所知的祥林嫂的一生,大多为听各种人物所说的传闻,这些段落大都用间接转述。这样,避免了晚清小说直接引语套直接引语造成的戏剧腔。
鲁迅作为五四小说最重要的技巧家,在其作品中试探了分层的各种可能性,即把人物转化为叙述者的各种方式。
上下显身式:《在酒楼上》叙述者“我”遇到一个昔日朋友吕纬甫,吕纬甫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的讲述用直接引语转述出来,因此二层叙述都是第一人称显身式;
上隐下显式:《幸福的家庭》写一个人物写一篇叙述,其中他自己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出现;
上下隐身式:这种结构似乎更为自然,如此可把这个人物变成主叙述者。这个构造似乎在晚清文言小说中比较多见,第三人称叙述中的一个人物讲述他人的故事,例如《祝福》中卫老婆子讲述祥林嫂第二次婚姻的经历。
至于晚清小说中见到的上显下隐式(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冷眼观》中可见到的第一人称超叙述“我”听各种人物讲别人的故事),却再也不见踪迹,这是因为晚清作家用此种形式来串接逸事闲谈成一书,而五四小说不再用这种形式。
所有上述的叙述者与人物关系——叙述角度,转述语,叙述分层,本质上说都是叙述主体的分割问题。在中国小说的形式演变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主体下移运动,从叙述者主体移入人物主体,这运动到了晚清,给叙述者造成无法忍受的压力,因此,叙述技巧上的问题成为中国小说发展的动力。但这问题的更进一步讨论还得留给本书的“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