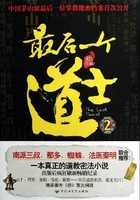一个叫夏冬的少年
和闯波儿的一战之后,我真的开始变了。
母亲痛哭流涕的担心与劝阻,父亲的欲语无言,砍在身上那些刀所带来的疼,侥幸活下来之后的后怕,一份正当而又符合理想的工作所能带来的快乐,这些都是让我改变的原因。我不想打流,也不想再和江湖上的事有任何联系,更不想继续做一坨九镇人口中的臭狗屎。
我想做一个好人。
我还在养伤的时候,家里就托关系为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九镇文化站的宣传员。因为会画画,在伤好之后,我被单位安排负责每星期一份的九镇区区政府大门前面的黑板报。
能够有一份发挥专长的工作的确是件很愉快的事情。你和别人一起看着同样的一块黑板,别人看到的只是黑,而你的心中却已经有了线条与文字的交错。
当一切在脑海中成形,你拿起粉笔,笔灰飞扬,钻入鼻孔,酥酥麻麻,酣畅的喷嚏之后粉笔灰却又迷住了你的眼睛。直线、半圆、波浪,轻描、淡扫,慢慢地,一幅幅的图画、一行行的文字从你的心中浮出,变成了现实之美。黑板不再黑,而是五彩缤纷的梦想。
这一切是多么的美好与快乐。那段时间,我破天荒地对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没有半点的懒惰与不愿,每天早出晚归,用尽浑身解数在那几米见方的黑板上写着、画着,乐此不疲。
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在门前乘凉,对面的王家奶奶笑着对母亲说:“刘家姐,你屋里的三毛儿终于懂事哒啊,天天上班做事,下班也不和街上那些鬼脑壳一路玩哒。我每回走过区政府门口都看到他一本正经地做事,搞得一身粉笔灰,打招呼都没得时间答应。呵呵,这个伢儿啊,懂事就好,懂事就好。你今后,八字就好哒,哈哈哈。”
母亲脸上露出客气的笑容。我看着她,慢慢地就看出了这种笑容里面的满足与幸福,这让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正走在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上。
邻居们的称赞与工作带来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前前后后大概也就两三个月而已。这一切的结束是因为,当时区政府的老办公楼并不在九镇,而在一桥之隔的彤阳。同时,在这段快乐的时间当中,我不在江湖,江湖却在那里,闯波儿的伤势痊愈了起来。
那一年的九镇,有这样一个年轻人:典型南方山区男人矮小精干的个子,小小的脑袋,有着如西方人般高耸的额头与鼻梁,高挺到一眼望过去,仿佛看不见他的两只眼睛,只能看到两片淡淡的黑影。不过,那一年,他深陷的眼眸中除了对于生活的不平和天生的纯真之外,还并没有出现日后那种如同深潭般莫测,让人心生惧意的阴沉寒芒。
那一年,如同我还叫姚义杰一般,他的名字也还叫做夏冬。
那时他早就辍学,自幼父母双亡的他被镇政府安排在县城某单位旗下的一家小鞋厂工作,聊以生存。后来,领导中饱私囊,单位经营不善,鼓励人们停薪留职、自主谋生,并且给每个部门下达了名额。虽然一直努力工作以求能够留下来,但是领导找他谈话之后,自知毫无背景,亦无资历,被辞退已成定局,自强也自卑的少年夏冬不待单位宣布,主动递交辞呈,回到了九镇。
当时,我们省有一个地方的烟花举世闻名,畅销世界。头脑活跃的九镇人看准了这个商机,也开始有样学样,造起了烟花。
除了父母留下的老房子之外,夏冬什么都没有。唯一可以让他讨口饭吃的,只有那一双天生的巧手。所幸,当时的政府还算仁义,将回到九镇的他安排进了一家山寨烟花制造厂。他辛勤地工作着,为了生活。
直到那一夜。
当夜,我躺在温暖的被窝中,正在看着一本小说,突然一声犹如天被砸破般的巨大爆炸声响起,床头上的窗户玻璃随着那一声响“哐啷”碎成千片,滚落在我的身旁、头上。
过了两三秒钟,我才回过神,疯了一般狂喊着去敲父母兄长的门,我以为地震了。随后,我听到了无数人的喊声、闹声、哭声,以及越来越多的警笛声、消防车声、急救车声。
母亲合十作揖,看着窗外爆炸声传来的神人山方向,眼里满是担忧与悲伤,她喃喃自语:“造孽哦,不晓得菩萨这回又请了几个人。”
爆炸那天,烟花厂正在连夜赶制一批烟花,夏冬也是当班的工人之一。除了他和工厂看门人以及一条狗之外,其余的七个制造工人无一幸免,全部身赴黄泉。他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听到工厂那只一向安静的大黄狗一整夜都莫名其妙地狂吠不停,听得夏冬越来越心烦。于是,他站起身来,想要出门打狗。当他走到门口,那位素来话很多,人却很热心的四十多岁的大姐给他说:“冬伢儿,你快点回来,耽误不得时间啦,厂长交代了今天要搞完。刘师傅,莫在这里面吃烟啦,万一点燃哒,就真不得了哒。”
“要得,要得,就吃完哒。天天吃的,怕什么……”
然后,已经走到了院子里的他,就突然觉得耳膜一疼,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夏冬说,从那天开始,他就已经是个死了的人。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他还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别个吃的,他也要吃,别个有的,他也要有。至于其他的事情,再也不是一个死人可以去考虑的了。
多年之后,江湖上出现了一位大哥,一位从来就没有靠过别人、求过别人,向来就独来独往却凭着聪明绝顶的头脑、歹毒凶狠的手段与深不可测的城府自立一方天地,如同传奇般出现在我市黑道的大哥。因为个子矮小与行事作风阴险,人们称呼他为:老鼠!
我之所以要提到他,是因为无论关于九镇江湖还是关于这个故事的发展而言,这个人都不能不提。
他曾是我的兄弟。我被伏击的当天,他也是当事人。
公元一九八九年农历十月一十七,我应该记住的一天。
我能够永远都记住这个日子,除了这一天是我的好兄弟鸭子的生日之外;还因为,在那天我认识了夏冬和北条。
烟花厂爆炸之后,老板连夜就逃之夭夭。大腹便便的镇长赶到处理大会上,对着夏冬以及那些痛苦欲绝的死难者家属们说:“经过调查,这次事件是由于违规操作引起的。主要负责人现在已经逃跑,公安机关正在抓紧追查。请大家相信政府,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这句话过去了三个多月,当夏冬与死难者的家属们一次次来到镇长办公室,见到的却是一副越来越铁青的面孔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过来:跑掉的老板不找到,他们是得不到补偿的;但是人海茫茫,这么大的中国,能找到他吗?
找不到。
所以,他不再参加那些职工家属们讨要说法的行动了,他也不再上班。每天,他就浑浑噩噩,如同野鬼般游荡在九镇的大小街道。这段时间,他喜欢上了打台球。于是,他也就通过他唯一的好朋友——一条街上穿开裆裤长大的北条,认识了同样喜欢打台球的鸭子。
头一天,我就接到了喝酒的通知,上完班赶到鸭子家里为他过生日时,鸭子专门找一林借过来的录像机已经开始播放起了李小龙的《唐山大兄》。
何勇、皮铁明、一林、鸭子正与两个看着有些眼熟却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同龄人,以及几个女孩子在一起已经喝得热火朝天、欢笑连连。
我笑着和所有人招呼。耳边传来了鸭子的喊叫:“姚义杰,老子的生日你才来啊?畜生,来来来,坐坐坐,一林,你往这里挪一下唦。”
刚进门,还没有落座,我就被已经明显喝多了的鸭子迎头骂了一通。我懒得理他,与大家打个招呼,自己找位置坐了下来。
“哎,给你介绍两个新朋友,这个是北条,这个是夏冬。都是兄弟
啊,铁聚(方言,很铁的朋友)!”
北条很豪爽,鸭子一说完,他就端起酒杯,先一口饮尽,然后才倒转杯口对着我说:“没得什么讲的。鸭子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看得起我,一起搞一杯。我敬你。”
根本没得办法,空着肚子,一口菜没吃,连屁股都没有坐热的我,也只能跟着他们端起才满上的酒杯,一口喝干。
我还在喝,就听到鸭子又嚷了起来:“喂,北条,夏冬,我给你们说啊,晓不晓得?老子的兄弟和闯波儿摆场的时候,姚义杰就是当事人。闯波儿,桥那边的大哥,晓得唦?你们就莫看这人而今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啊。一条猛汉!老子告诉你们,莫把他看瓤(方言,小看,小瞧)哒。姚义杰,呵呵,你们问一下在场的人,他打军军,在桥上头摆场,是不是条硬腿(方言,好汉,铁杆)。搞!搞!搞!夏冬你也和他搞一杯。今后都是兄弟,不得丢你们的脸。”
在鸭子放肆的吹牛声中,所有人都看向了我。何勇、皮铁明的脸上是一副“不晓得你是个什么货色啊”的表情,几个女孩的眼中却隐隐露出好奇的异彩,这让我有些不好意思。借机看向了鸭子口中所说的夏冬,我看到了一个矮小瘦弱的年轻人,有些怯意、有些羞涩地端着酒杯,也在望着我这边,安心地等待着鸭子说完。我感觉,这不是一个浑身流子气,喜欢装成熟老到的人,而是一个单纯的少年。他远远要比在场的其他各位,包括我在内都要来得单纯。
我对他点头一笑,马上伸手拿过一个酒瓶,给自己的杯里满上了酒。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夏冬对我说:“义哥,早就听鸭子哥、勇哥他们说起过你,说你而今还是政府的干部。我敬你啊。”
抬眼望过去,那个叫做夏冬的小个子少年坐在北条和何勇之间,比两人都要矮半个头,双手举着酒杯,几乎伸到了我的面前。
他的眼中满是敬畏与礼貌。我心底突然涌起了对于这个人的莫大好感,就如同小时候刚认识皮铁明、何勇、鸭子他们一样。双手捧起了杯子,轻轻迎向面前的那个玻璃杯,我尽量客气地微笑着说:“莫这么喊,莫这么喊!都是兄弟,喊这些我受不起,也没得意思哒。呵呵,来,我先干为敬,先干为敬。鸭子,你也满起,我喝了这杯就陪你这个长尾巴(习俗,九镇习惯把把过生日的人叫做长尾巴)搞好!”
那天,兴致高昂、真诚相对的我与夏冬,一口饮尽了我们之间的第一杯,也迎来了日后的千千万万杯。只是,年少的我们在意气佐酒、酣畅淋漓之时,从来就不曾想到生命的酒,却是苦如黄连。
夜色下的刀光
不久,九镇政府为了响应上级号召,也为了在年底宣扬政绩斐然、领导班子能力突出,决定办一期以“五讲四美树新风,现代九镇迎朝阳”为主题的大型活动。这个活动的其中一项就是要办一期比平时更加隆重,同样突出这个主题的黑板报。
这项任务就由鸭子口中当了“政府干部”,实际上只是一个临时工的我来负责。我想要又快又好地完成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于是我把早就已经融入到了我的朋友圈子里面,而且有着一双巧手的夏冬叫了过来,给我帮忙,负责为黑板报四周挂上各种颜色的小彩灯与绸纸剪成的鲜花。
夏冬的手确实很巧,不但剪出来的花比一般女孩剪得还好,而且还把彩灯的电线用绸纸包裹起来,与鲜花、彩灯浑然一体,非常好看。由于第二天领导上班就要验收成绩,星期四那天晚上下班之后,我并没有回家,依然带着义务帮忙的夏冬一起继续辛勤工作。
我们一直弄到了深更半夜,四周无人。
其实,在与闯波儿摆场之后,我并不是没有提防,我也担心自己天天在彤阳这边上班会出事。毕竟,闯波儿的名号不是骗来的。只是,有几次,我无意间在街上遇到了闯波儿以及那次摆场的其他几个人,却发现那些人除了颇有深意地看了我几眼,都无一例外地再无反应。时间一久,我就有了一些侥幸的心理,认为舅舅的能力可以威慑住他们。虽然闯波儿那天伤得最重,但是我的兄弟也受了那么重的伤,何况砍闯波儿的是何勇,而不是我,就算闯波儿要报仇,也应该不会首先就找到我的头上来。
再说了,我也在堂堂的区政府上班,闯波儿可能嚣张到来区政府砍我吗?所以最终我也就放下了心来。
其实,现在来说,当初我想得都对,起码在分析事情方面,我的思路并没有错得太多。
只是,我忘了分析人,分析闯波儿这个人。一个过了十多年之后,也不忘为父报仇,嚣张到光天化日之下,敢当街手刃仇人,然后扬长而去的人。在他的眼中,当深更半夜,大家都下了班,四周没有人,位置又偏僻的区政府大门口并不见得会比白天的街道上更加危险,更加不方便。在他的眼中,一个动手捅了自己的流子,与一个惹起了这场事端也参与了殴斗的对头也许并没有先后报仇之分。
何勇同样是个流子,比当时的我更加狡猾、更有经验、更不好办。而我每天都出现在他的地盘上,游走在他的面前,如同一只毫不设防的羔羊。
当然是哪个更加方便就先动哪个。
热火朝天地工作了很久,板报也终于快要办完,静静看着自己的作品,满心欢喜,手都写酸了的我决定稍微休息下。从裤兜里掏出了一盒烟,叼在嘴里一根,然后招呼依然爬在短梯上专心致志地为黑板报贴花纸的夏冬:“喂,兄弟,差不多哒。先休息哈,来,先吃根烟咯。”
“好,就来,先贴完这朵花。”
“快点,万宝路啦。十块钱一包,站长昨天给我的。”
“哈哈,要得要得。”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声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呼喊:“姚义杰!”喊声悠悠飘来,里面仿佛带着嘲笑、得意与某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味道。我觉得这声音好像有些熟悉,一时之间,却又偏偏想不起来。
借着头顶那盏为了办板报专门从单位里牵出来的三十瓦小电灯泡所发出的微弱光芒,我停下点烟的动作,看向了前方不远处声音传来的那条街道。除了几片被深夜寒风徐徐吹动的纸片之外,安静的街道上空无一人。
心剧烈跳动起来,莫名的直觉让我下意识地感受到了某种危险,求助地看了一眼夏冬,再回过头对着长街,尽量自如地问道:“哪个?”
“我!”
随着声音的传来,我看到二三十米之外街道两边黑暗的墙角中,缓缓走出了四个黑乎乎如同幽灵般寂静无声的人。
由于常年习惯躺在床上看书,我有些近视,但是那个年头,戴眼镜的不是愚蠢的书呆子,就是油头粉面的家伙。我从来都不愿意戴眼镜,所以当时的我除了看见那四个人正在缓步朝这边走过来之外,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也没有认出人。
“你是哪个?”我又大声地问了一句。
话才出口,就听到身边依然爬在梯子上的夏冬小声说出了一句话来:“喂,姚义杰,他们手上好像拿着刀!”
声音惶恐、紧张。
脑子里面一下炸开,我立刻猜到了来的是什么人,长这么大,我并没有惹过其他值得别人拿刀的事情。只不过,那一刻我的心底还有着一丝侥幸,我希望不是,我想要求证一下。而且,我需要做点什么来将那种让我手脚冰凉的胆怯赶出体外,好让自己别在夏冬面前太丢脸。所以,我非常大声地再喊了一声:“你是什么人?”
这次,再也没有一个人开口回答,四个人依然不紧不慢、近乎无声地向着我们走了过来。
二十米、十五米、十米……
然后,我隐约看见走在人群最后面的那个人,他一直低着头,身上披着一件大衣,走路好像还有些一瘸一拐。他突然停住了脚步,缓缓地把头抬了起来,似笑非笑地看着这边说:“前段时间,还碰到过几回,你就不认得我哒。”那个人蔫头耷脑地站在那里,连说话声都有气无力、阴阴沉沉。
我终于清清楚楚地认了出来。
闯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