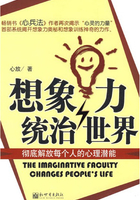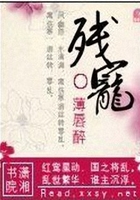永瑞四年冬,向来安逸的柳江城发生了一件大事——顾县令一家因逆谋被抓了,囚车向着城门缓缓前行,拉了长长的一队,沿途围观的百姓也了堵了长长的一街。按说顾县令中庸,十几年来并未出过什么大的纰漏,然而此番虎落平阳,那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竟都叫翻了出来,也不管孰对孰错,都先与他安了个不是。当然被诟病最多的还是他的女儿顾红翎,这个娇扬跋扈,傲气了半生的官家大小姐或许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一次任性不仅害自己失了身心,更害得全家人为她身陷囹圄。
叹世事唏嘘吧,瞧这数落嘲讽、鄙夷唾骂的比比皆是,菜叶萝卜鸡蛋毫不留情地往囚车上招呼;却也是人之常情,一个人纵有千般好,可一旦做错了什么,世人便往往只记得他的错了。
顾县令也为柳江城做过不少好事,只是此刻大概无人忆起,顾红翎大概也有了悔改之意,只是已经没有了机会。怨谁呢?既然种下了苦因,便自有须尝的苦果,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
秦瑶想,或许她近日所历的一切也是她须尝的苦果。
押送囚车的队伍行至城东大街,眼看快要经过柳江客栈,客栈门前早已围得水泄不通,栈中的客人也无心其他,一个个涌向栈门,踮起双足引颈以望,更甚者,还有人专门为了这事在客栈二楼开了一间厢房。
“啊,来了,来了,老天开眼啊,这狗官也有今天啊!”
“没错,没错,柳江城的苦日子总算到头了!”
“父老乡亲们,待会儿使足劲头啊,扔死那狗官!”
人群中沸沸腾腾,骂声一片,也不知顾家与他们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秦瑶摇摇头,将注意力重新放回眼前的账本之上。
却见李婶慌慌忙忙从二楼奔下来,上气不接下气道:“掌……掌柜的……你猜,我方才看到了谁?”
“顾家人是么?这城中只怕无人不知了吧。”秦瑶漫不经心道。
“哎哟,掌柜的,谁跟你提那些贼人了,上回那贼女在客栈捣乱,还打了你,你要是忘了疼,我李婶可还记着。”李婶义愤填膺,胖胖的脸上硬是让气给憋红了。
秦瑶笑开了,暗忖:到底是客栈好,李叔李婶与她虽无血缘,却胜似亲人,在她被抓去的几个日子里,他们一定急坏了吧。她还记得她刚回来那天,李婶大哭了一顿,把她拉近里里外外看了好几遍,又是嘘寒又是问暖,就连李叔也偷偷背身擦了擦眼。
“那你待会可记得挑最大的鸡蛋给我报仇。”忆着这两日感受到的温暖,她忍不住打趣道。
“哎,好咧!”李婶也来了精神,摩拳擦掌地走向厨房。
不一会儿,厨房那头便传来了李叔低沉的声音:“你好端端地拿鸡蛋做什么,浪费食物!”
秦瑶扑哧地笑了出来,掩唇之间,忽觉自己似乎许久没有这般笑过了,一时间竟有些替自己不值,也不解自己这一年来究竟在做些什么,都活了近半辈子了,竟还为那些旧事折腾自己,真真是白听了那么多天的暮鼓晨钟。
那年,在观云山上,她以为自己看透了的,结果,却是她高估了自己。
却说李婶满心欢喜地往厨房里走了一遭,出来时却一脸憋屈,窘迫地与秦瑶道:“哎哟,掌柜的,你看我都老糊涂了,我刚才要说的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是哪个?”秦瑶问。
“是那押送囚车的军爷,骑着骏马走在最前头那个。说出来你别不信,他啊,跟咱们家小二长得一模一样!”李婶凑近秦瑶,故意压低声音道。
秦瑶不由地一顿,良久才回过神来,轻笑道:“原来说的是这个,小二本来就是当朝的大将军,这并不出奇。”
“什么,小二本来就是将军?”李婶大吃一惊,敲着自己的脑袋在原地打起了圈圈,似乎怎么也想不通,嘴里碎碎念着,一会儿说大将军怎肯屈身做那等伺候人的事,一会儿有又怨秦瑶傻,放着好好的将军夫人不做,跑来这里活受罪。
秦瑶只默默地看着她,却半句也听不进去。
这几天,他一直还在柳江城,她是知道的,甚至乎,她还偷偷地想过,他这般大张旗鼓地离城,是为了叫她知道。只是,他一直没有来找她,而她,更没有勇气去找他……
那日在岳剑山庄地牢,受环境所迫,她说了许多心里话,尽管并没有后悔,但若换作此时此景,要她再说一遍,那么她是万万说不出来的。
“唉,我说掌柜的,小二将军都这般待你了,你怎的就不肯原谅他呢?”李婶一句轻飘飘的话语钻进了她的耳朵,“李婶李叔都是粗人,也吵过架,可夫妻之间哪有隔夜仇啊?不消半日便和好了。怎的换在你跟小二将军这等玲珑的人身上,就这么能折腾呢……”
秦瑶不语。
可心却像翻了个筋斗。
原谅他么?若是那日在地牢里一鼓作气地说了出来,又或者那时云明没有拉住她,或许便成了吧。
人其实很奇怪,不能一鼓作气,便只能气馁了。
她那颗心啊,恰似好不容易才露出了个头,却不可从一而终,堪堪维持了半日,又缩了回去。而日子拖得越长,只见胆子越小,徒生怯意!
他这次回京,只怕再也不来柳江城了吧。秦瑶瞥了一眼栈门处的人群,仿佛殿小二就站在那人群之外,再环视了一圈自己的客栈,突然想起那段殿小二在这里翻上爬下的日子,竟不由自主地轻叹了一句:“唉……这客栈倒是一日比一日冷清了……”
而此时,柳江客栈的门前,本来前行速度已极为缓慢的囚车队伍竟突然间停了下来,围观的人们都伸长了颈子观望,乍一看,似是走在最前头的大白马止足不前,耽误了整支队伍,然细看之下,却不难发现,并非这马不愿意走,而是马上之人紧勒住缰绳,叫这马前进不得,只得在原地低头喘粗气,愤愤不平地踏脚。
队伍一停便将近一刻,马上之人望着柳江客栈的匾额,既不下马,也不作声,却叫旁观之人纳闷至极。
这将军若是渴了,想到栈中喝杯茶歇歇脚,只管开口便是,用得着在那里犹豫这么久吗?周围的人窃窃私语,可马上之人却置若罔闻。
倒是杜潮守看不下去了,低声道:“头儿,你要是真舍不得掌柜的,就下去瞧瞧她呗。她打开门做生意的,总不至于将你赶了出去。”
殿小二斜睨了他一眼:“谁说我是怕她将我赶出去来着?”只是有些事尚未完全了结,觉得无脸见她罢了。其实也无怪杜潮守会这么看他,这几日,若不是身上有伤,又事务烦身,他应该老早就去找她了。
可是找了又如何?若无法解开他俩之间的心结,一切都于事无补。而解开他们心结的关键所在,便是这押送行程的终点。
“走吧!”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队伍,拉了拉缰绳道。再不走,只怕底下之人就要笑话了。
“咦?就这么走了?头儿,您真的不去瞧瞧秦掌柜?这一走,会有很长一段时日无法见面的。”杜潮守很是惊讶,脑袋应是拐不过弯来。这不像头儿的一贯作风啊。
“不瞧了!”殿小二一咬牙,将视线从客栈抽离,“瞧得越多,越不舍得!左右……日后的时间多的是!”
“啊?”杜潮守摸着自己的脑袋,只觉自己被他绕进了死胡同里。究竟是瞧还是不瞧?若是不瞧,您倒是往前走,别赖在这里啊。
却听“驾!”地一声,殿小二夹了一下马肚,在众人未回神之际率先策马而去,在此耽搁了许久的押囚队伍总算得以前行。
永瑞四年十二月,护国大将军沈青彦铲除叛党,凯旋而归,帝大喜,令普天同庆!
翌年春,传大将军身染恶疾,不治身亡,帝大悲,令举国同悼!
哀悼之日,天色灰霾,下起了朦胧细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