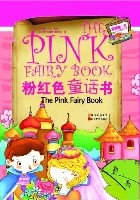“掌柜的,您在说什么呢?我如今姓殿,名小二,您忘了?”
“是么?原来你还记得!”
可是她却无法遗忘……
沈青彦,前任辅国大将军的独子,五岁便入宫于二皇子左右侍读,十八岁高中武状元,官拜正四品忠武将军,二十岁娶得相府次女为妻,二十一岁助瑞王也就是当今圣上取得皇位,擢从二品镇军大将军,而近两年,她虽不清楚,但想必也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
秦瑶笑自己愚昧,虽然在心中刻意地遗忘了“沈青彦”这三个字,可是那般刻骨铭心的三个字又岂是说忘便能忘的?“沈青彦”之上多了一个“殿小二”,他还是“沈青彦”,就像她秦瑶,即便多了一重柳江客栈女掌柜的身份,也不碍于她曾经是秦相府的二小姐。
一切还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二十一年前,新科状元秦礼正披红挂彩,骑马游街,因其容貌俊秀,是以吸引了沿路少女芳心无数,当中也包括了其时名满京师的两位才女——吏部尚书之女苏芷兰以及礼部尚书之女魏子澜。
两女才色相当,却素来不和,时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之事针锋相对,此番待状元郎也是如此,两不相让。成亲本是一桩美事,可苏魏二家同时到状元府提亲,却叫状元郎左右为难,几家人商量了一番,最后一拍板,一娶双妻,不分大小。
于是,苏魏两位才女便从未出阁斗到了嫁为人妇,斗到了秦家的后院,连生娃儿的先后也要斗一番。
一年后,魏氏早先一步生了一名女儿,取名为湘,而苏氏足足生了三日闷气,腹中的孩儿才呱呱坠地,那孩儿便是日后的相府次女——秦瑶。
上一代的争斗延续到下一代,秦瑶从记事开始便是在无止境的明争暗斗中度过的,不管做什么,娘亲都一定要她与姐姐分个高低,但她一直不明白,赢了如何?输了又如何?为了争一口气?为了在对方面前趾高气扬?
可苏芷兰到底是输了几分,倒不是输在姿色与气质之上,而是身子生来便比魏子澜弱了些,自幼便时常靠药物养着,这些年因生女晚了,女儿的姿色才气又比不上秦湘,心中便积了许多郁结,身子每况日下,没几年便撒手人寰。那时秦瑶才十岁,她站在苏氏的灵柩前,向来懵懂的她仿佛在忽然之间悟了一个道理。
苏氏离世后,秦瑶在相府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尤其是在魏氏为她添了一位幼弟之后,就连父亲对她的态度也冷淡了许多,但秦瑶却不以为意,默然地居住在自己的小屋里,却也轻松惬意。
少了苏氏的督促,秦瑶的课业也松懈了,琴棋书画只略通了一二,只女红做得颇为精巧,府里人都说,二小姐是个庸才。
相比起秦瑶的庸碌,秦湘却美名远播,年仅十四岁便挤下了工部尚书之女,成为京中“第一美女”,十五岁时又取代了张太傅之女,成为了京中“第一才女”。有如此盛名,自然获得了众多贵胄公子的青睐,那段日子里,魏氏时常笑得满面春风,秦相亦对这个女儿宠爱有加。秦瑶有一次甚至听到父亲私底下对魏氏道:湘儿将来必定是要嫁入皇家的。这话听起来并无不妥,但秦瑶总觉得他话中有话,比如说执掌凤英母仪天下之类的。
秦相的话不无道理,只因秦湘的爱慕者之中就包括了当时的东宫太子楚辰,当然,还包括了当时的武状元沈青彦。
熙景二十八年,正是秦湘与秦瑶的及笈之年,相府出入的人中多了许多少年,而这些少年大多数都是慕秦湘之名而来的。秦瑶不止一次登上阁楼眺望,但见清池竹亭间,翩翩公子执着纸扇品茗聆听,而佳人噙笑,玉指纤纤,温柔地弄着琴弦;或听得几声嬉笑,不知谁又得了几个妙句。
燕朝的民风颇为开放,少年少女结伴同游的画面并不罕见,但像这般令人赏心悦目的却也不多,秦瑶占尽的天时地利,欣赏风景之余偶尔也会秉笔描画几笔,末了又看着拙劣的画工摇头轻笑。
秦瑶的贴身婢女绿意却甚是不解,也替自家的小姐不甘。世人都只知道秦府的大小姐,却从来不过问秦府的二小姐。二小姐虽然比大小姐晚生了几天,比不得大小姐那般貌若天仙,才华满腹,可好歹也清秀可人,贤淑有德,又是正出的,身份与大小姐同样高贵,再如何也不该落得这般无人问津的境地。
“小姐,那些人当真有眼无光!”绿意时常望着院子中的人影忿忿而道,又叹自家的小姐不争气,愧对泉下的苏夫人。
秦瑶却一笑置之。勾心斗角,争宠夺权之类的,最麻烦了,一旦沾上便不知何时是个尽头。秦湘虽然风光,但她秦瑶不也逍遥自在么?
沈青彦也是当年时常出入相府的年轻公子之一,他虽是武状元,却也是当时京中有名的纨绔弟子,青楼赌坊酒肆之内,都不乏他的身影,只气得他那当大将军的爹七窍生烟。不过这也是沈青彦遇上秦湘之前的事了。世人都说,沈状元对秦家大小姐情根深种,从此浪子回头,不惜指天起誓,绝足烟花赌肆之地。
市井之言,真假难断,但沈青彦确实有那么一段日子经常拜访秦相府,唯恐被东宫太子抢了先。
然而,秦瑶初次遇上沈青彦却不是在秦府的后院,而是城郊树林的某个坟头附近。
天色青灰,细雨绵绵,正是清明时节。
秦瑶撑着伞,提着一个篮子走到苏氏的墓前,草色青翠,雨水涤着碑石,世界安静得只余下雨声。
尽管府里都有专人负责祭祖扫墓,但每年三月,秦瑶还是会抽一天亲自祭母,而今年,她索性连绿意也不带了,剪一捧白菊,带上一小碟苏氏生前最爱吃的糕点,穿过雨帘,踏着湿土独自来到郊外。
她将白菊与糕点置于墓前,笑道:“娘啊,孩儿虽没有照您的话与她们力争到底,可您看,孩儿如今不也活得好好的么?并不见得会吃亏啊。
“不过,孩儿去年便已及笈,婚姻之事孩儿作不得主,也不知他们将来会把孩儿许配给什么人。娘若是还惦记着孩儿,便佑孩儿得到一段好姻缘吧。”
墓中人自然不会作答,然雨声沥沥,听在某些有心人的耳中,就仿佛是低声诉语,那清风拂弯了青草,一点一点,不知是否被某人寄托了情思,正代替那人诺然应允。
秦瑶浅笑着离开了苏氏之墓,提着微湿的的裙摆欣然而回。未几,却见道旁歪歪斜斜地趴了一个人,看他的衣着服饰像是京中的贵公子,却不知为何晕倒在这泥泞之上。他的左臂上嵌了一支镖,黑血溢出,又被雨水晕开,形成了一滩血污,在细雨的敲打下弹跳着。
秦瑶怔忡了片刻,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来时这路上还干干净净的,她不过在墓前逗留了须臾,这路上怎么就多了这么一件麻烦物呢?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她小心翼翼地蹲下去,拨开了他脸上凌乱的发丝,之间一张英俊不凡的侧脸露了出来,眉如双剑,鼻直口方,然而双目紧闭,脸色发青,看样子是中了毒。她惋惜地摇了摇头,一瞬间,脑中涌起了种种猜想:陷害、灭口、家变、情杀、仇杀……
她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却发现那人竟然还有气。
“活的。”她低喃了一句,眉头皱得越发紧了。她左右四顾,然而林中寂寂,除了他们之外,别无他人,她又低头看看他健硕的身形,最终垂目站了起来。
“还是当作死的吧。”她承认自己与温柔善良搭不上边,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这救与不救还是得量力而行。想这荒林野外,湿漉漉的下雨天,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要把这么一个高大挺拔的男子搬回城中……难啊!
她抖了抖衣摆,举步欲离,忽觉有一道力扯住了自己,低头一看,竟是一只沾满泥污的手,它紧紧地抓着她的裙脚,叫她无法前行。
“姑娘,你要见死不救么……”一道低沉暗哑的男音传来,虚若无力,只一句便又没了下文。
秦瑶不由自主地长叹,早知方才就不该好奇,当作什么也没看见直接越过去该多好。自作孽不可活!
她忽地想起了这附近有一座供守林人居住的小木屋,若要把他拖到木屋去,倒还有几分可能。
她又复蹲了下去,道:“要救你也可以,可我力气小,你若是还能走,我便支着你走一段,如何?”
趴在地上的人没有回答,许久之后,才缓缓地睁开了眼,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又恹恹地闭上。
秦瑶无可奈何,只得将他的长臂搭在自己的肩膀上扶他起来,一手托着他的背,一手还得顾着伞,如是半拖半支,踉踉跄跄,好不容易才到了木屋。
守林人是秦府的下人,过去还受过苏氏的一点恩惠,是以对秦瑶还算恭敬。秦瑶甫进门便把肩上的重负扔给了他,又吩咐他不得泄露她的身份,而后便匆匆离去,片刻也不愿停留。
此刻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迫于无奈救的这个人,日后不仅进入了她的生命,还成了她的夫君。也难怪数年之后在得知自己在客栈门口捡的人是他之时她会暴怒,两次救人,救的都是同一个“麻烦”,真不知该说这是缘,还是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