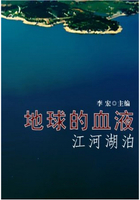其三,封建国家承认父权对社会基层组织的控制,从而体现皇权、父权、族权的联手统治。在广大农村,宗族家族长是编外官吏,代表宗族、家族向国家纳税、当差,其管理权既来源于封建国家的授权,更自然地来源于血缘亲属伦理关系的当然性。如果说父权、族权是皇权的延伸,皇权则依赖父权、族权代行其最高权力。较小自然村落的宗族组织是社会基层准政权组织,是封建国家政权的分支础石。强宗豪族掌控的较大村落宗族家族组织,左右地方或国家的政局,有的甚至可以同中央政府抗衡。中央政府一般只能对其安抚而不能无视其政治能量。因此,封建国家承认父权对社会基层组织的控制,既是客观需要,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朝廷对分散各处的社会基层组织力所难及。
2.三纲五常在封建国家立法司法中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立法司法活动并重视修法的国家,二十四史每部史都详述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形成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博大宏深的中华法系。中华法系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之处是它构建了一种以三纲五常论理指导的宗法伦理法,贯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五种宗法伦理、宗法道德精神,法律保护伦理关系、倡导宗法道德。对此,我们从立法目的、如何维护纲常、法制制裁破坏纲常犯罪、纲常对司法实践的影响简论其要。
其一,中国古代王朝立法的目的即为了维护三纲五常的社会政治秩序。夏商周三代立法即担承着双重使命:调节君主为首的宗法贵族集团的内部矛盾,压迫族内贫民和族外奴隶。尤其严惩“不孝不悌不友”《尚书·康诰》。的伦理关系混乱之罪。秦汉以后,封建王朝都把维护三纲五常作为立法的根本目的。秦朝虽然一任法家,但秦律仍规定体现儒家思想的维护三纲五常的内容,如“为人君则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云梦秦简·为吏之道》。
汉代立法更自觉地以儒家三纲五常论理为指导,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置入法律成为法律规范。其时盛行“引经决狱”,把儒家《公羊春秋传》之经看做有法律条文权威一样的执法量刑依据。儒学大师董仲舒参与法律制定,董居家应对朝议之问,“对皆明法”《汉书·董仲舒传》。唐代立法更明文规定法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入罪,在《唐律疏议》中清晰可见其充分体现。
中国古代近代之交的清末,为应对中国社会和世界的巨大变化,开始制定新法工作。但清帝明令修新法不准违背纲常名教,他在《修改新刑律不可变革义关伦常各条之谕》中说:“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异,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犯名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良以三纲五常,阐自唐虞,圣帝明王,兢兢保守,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今寰害大通,国际每多交涉,固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变宜民之意,但只可采彼之长,益我之短,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敝,该大臣务本此意,以为修改宗旨,是为至要。”故宫博物院藏《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清帝这个上谕虽然也声称“采彼之长,益我之短”,但坚持维护三纲五常的修法宗旨,不得“变革”。足见传统纲常论对订立法律影响之深重。
其二,中国古代法律充斥维护三纲五常的内容。其突出表现是法律规定的“八议”法制:议亲(皇帝亲属)、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朝廷认可的贤德之人)、议能(有大才能者)、议功(有大功勋者)、议官(职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议勤(有大勤苦者)、议宾(国宾)。八议之制初见《周礼·秋官·小司寇》,执法时考虑八种人的特殊身份给予照顾,是封建特权在法律上的反映,其要害是维护纲常中的君权和父权。这八种人享有特殊照顾的法律不平等特权,从《唐律疏议》中可见其具体的减、免、赎刑的规定。
中国古代法律维护三纲五常的内容很多,由于纲常论理重视父子伦理关系,将伦理关系视为政治关系的基础,特别侧重保护伦理关系。为此,法律具体规定依丧服表示伦理关系亲疏远近定罪,亲属相隐,相互包庇,如孔子所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存留养亲,死刑犯因父母年事已高需子女赡养而免死,迁就复仇,为报父仇而杀人免死,等等。
需要指出,中国古代法对三纲五常的维护除以国法规定外,还表现为在国法之外并在国法的支持下容忍家法、宗族法的存在和适用,主要以家法、宗族法保障父家长的特权:父家长直接主宰子女的财产、婚姻,可以任意教训、责打乃至杀死子女。家法、宗族法是父家长主宰妻子、子女的暴力工具,其对妻、子、女的迫害无人性可言,有的野蛮残酷至极。
其三,中国古代法律严厉惩处悖逆、破坏三纲五常的行为,其法条之多,量刑之重,实属无理、罕见。突出表现为法律规定的“十恶”重罪:谋反(颠覆皇朝统治)、谋大逆(破坏皇家宗庙、陵墓、宫阙)、谋叛(叛国投敌)、恶逆(谋杀、殴打尊亲属,丈夫尊、近亲属)、不道(杀死一家三口及肢解被害人)、大不敬(盗窃御用物品)、不孝(对直系亲属有忤逆言行)、不睦(谋杀或出卖近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或尊亲属)、不义(杀害本地及五品以上官长、夫死不举丧、守丧期作乐或改嫁)、内乱(近亲属间不正当性关系)。十恶重罪直接破坏三纲五常政治、伦理关系秩序,因此,严加惩处且不赦。《唐律疏议》申明:“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中国古代法为维护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严厉惩处不孝、压制妇女。中国古人视不孝为罪恶之根:“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刑章》。如此视不孝之罪,法律乃多定惩治不孝条款。如《唐律疏议》所列不孝罪名有:告言诅詈视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对父母、祖父母供养有缺,居父母丧时身自嫁娶,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丧,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等等。上述行为顶多是一般过错,之所以量为重罪,源自法律要维护纲常之故。为维护夫为妻纲这一名教教条,法律多规定压制、歧视甚至迫害妇女的条款。从《唐律》至《大清律》都沿用《大戴礼记·本命》中针对妇女的“七去”之说作为强制性法律规定: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去,为其绝世也;淫去,为其乱族也;妒去,为其乱家也;有恶疾去,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去,为其离亲也;窃盗去,为其反义也。七去是强化夫权、压制迫害妇女的无理法条,为维护三纲将妇女推向悲惨境地,对妇女无仁义礼智信可言。
其四,中国古代法制中受三纲五常论理影响还处处表现在为三纲五常张目的司法实践上。中国古代府州县级行政首长同时也是该审级最高司法官员,他在执法过程中一般偏向上者、尊者,至于在下者、卑者,即使有理也无法倾诉。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认为:“凡有狱讼,必下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一等。”《朱文公文集》卷十四《戊申延和奏劄一》。此种情形直至明代也无所改变。即便清官海瑞也以存纲常之体为由为朱熹所言之行状。海瑞坦言:“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宁屈小民,以存体(纲常)也。”《海瑞集·兴革条例》。
封建时代的一些府州县官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强词夺理,不顾是非曲直,不依法律而依道德规范定人罪名,从而增强了封建法制的不公正不平等性。如清代知县袁枚在审理一家兄弟三人在父死七日后为争夺遗产而诉讼时,一怒之下,断兄弟三人于父尸未寒时便挥戈涉讼,无颜以对父于地下,对宗族于人间,治以“不孝”之罪。如此以情代法、以德代法,既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既然身份上尊卑不平等,法律适用上必定不平等。纲常论理影响司法实践可谓极其彰烈。
3.三纲五常论理在文化教育举措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