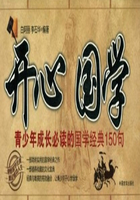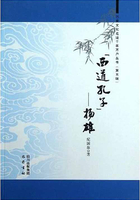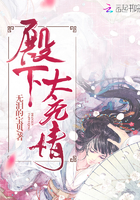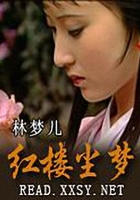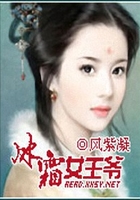例如,关于“如性”这一概念,当初译为“本无”。现在考究起来,这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如性”这个概念来自《奥义书》,并非佛学所独创,表示“就是那样”,只能用直观来体认。印度人已习惯地使用了这一概念,可是从中国的词汇中根本找不到与引相应的词。因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比较看重实在,要求概念都含有具体的内容,所以没有这类抽象涵义的词。所谓“如性”即“如实在那样”,而现实的事物常是以“不如实在那样”地被理解,因而这一概念就有否定的意思:否定不如实在的那一部分。印度人的思想方法要求,并不必否定了不实在的那部分以表示否定,只要概念具有否定的可能性时就表示出来了。所以佛家进一步把这一概念叫做“自性空”,“当体空”。从这个意义上说,译成“本无”原不算错。而且“无”字也是中国道家现成的用语。要是了解“本无”的来历,本来不会产生误解。但这种用意只有译者本人了解,译出以后,读者望文生义,就产生了很大的错误。最初把这一概念同老子说的“无”混为一谈,以后联系到宇宙发生论,把“本”字理解为“本末”的“本”,认为万物是从无而产生。这一误解并未因它的译名重新订正而有所改变。例如,以后“本无”改译成“如如”、“真如”等,反而错上加错,以至于认为真如生一切。……总之,我们不能把中国佛学看成是印度学的单纯“移植”,恰当地说,乃是“嫁接”。两者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就职是说,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注释: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吕澂佛学论著选集》,2438~2440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
二、讲习经义
为了广泛传播佛教,使之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中国佛教学者还采取讲习经义的方式。讲习经义和翻译佛经一样,是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独特的专业化活动,不仅构成中国佛教活动的特色,而且也成为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途径之一。
据史载,商北朝时,讲经活动已十分盛行,规模也很庞大。为了使佛教深入人心,扎根社会,讲经不仅有明确的分工,还有一整套程式。如擅长歌赞(梵呗)和咏经(转读)、善于阐释佛教义理的僧侣,称为“经师”。讲解佛教经典的僧侣,称为“讲师”。协助讲师讲经,在讲师讲经时和讲师对话,使听者更加易于明白经义的人,称为“都讲”。随着讲经的进一步发展,还出现了“宣唱法理,开导人心”的僧人,他们用美妙动听的声音向信徒传教,这些人称为“唱导师”。这种专业性的分工,表明佛教宣传的正规化,它有助于提高佛教传播的效果,使之根植中土。
讲经人对经文的理解直接受个人的文化水平、传承关系及其原有的思想倾向的影响,他们都是根据自己所学所知讲解的。而听经人也多半受过中国固有文化的熏陶,是借助于自己原有的中国文化思想素养去理解和接受经义的。可以说,讲经和听经,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思想与印度佛教教义的比较对照、融合会通的过程。中国僧侣讲习经义,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
东晋初期,讲习经义主要采用固定格义和自由发挥两种不同的方式。[注释:僧叡在《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中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泳以来,虽曰讲肆,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大正藏》第55卷,59页上)格义和六家是讲肄的两种不同方式。]康法朗、竺法雅等人,为了解释佛典中的“事数”,创造了“格义”的方法。事数,又作名数、法数,即名相,是带有数字的佛教名词,如四谛、五蕴、六度等。所谓“格义”,是“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注释:《梁高僧传》卷3《竺法雅传》,《大正藏》第50卷,347页上。]。也就是把佛典中事数和中国《老》、《庄》、《易》等典籍的相关概念进行比配,把相近的固定下来,作为理解、讲习佛教事数的规范。这样,就把佛教的名词、概念、范畴判定为中国固有的与之近似的名词、概念、范畴,形成了统一的格式。格义方法运用,常常导致人们对经义的理解与印度佛教典义理相违:“然凡谕之者,考文以征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验其义者,迷其旨者也。何则?考文则异同每为辞,寻句则触类每为旨。为辞则增其卒成之致,为旨则忽其始拟之义矣。”[注释:《道行经序》,《大正藏》第55卷,47页中。]意思是说,佛经文句不同,不具体把握其旨趣,一味执著格义的方法,拘泥于文字,以章句是务,就会造成迷误混乱。格义必然歪曲佛典原义。而我们认为,这种歪曲实际上恰恰也就是佛教义理包括佛教哲学中国化的朴素表现和初级形式。
采用自由发挥方法的是东晋时期的般若学派。由于此派是自由讲论,又分裂为六七个支派。这些派别的思想分歧,此处不论。这里只举例介绍他们自由发挥的程度和引起佛教哲学转型的后果。据载,般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支敏度,在往江东之前,曾与一伧道人商量到南方以后怎样讲般若的问题,伧道人说:“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注释:《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诸子集成》(八),226~2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于是决定“共立心无义”。支敏度单独到了江东,大讲心无义。尔后,道人又写信提醒他说:“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注释:《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诸子集成》(八),226~227页。]支敏度为了博得江南名士的欢心,以解决吃饭问题,自由发挥经义,不惜随意附和清谈玄学,于印度般若学外另立新论。再如,当时般若学派又一重要代表人物道安,长年讲《放光般若经》,并注意和《光赞般若经》作对比研究,他在《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说:
其为经也,以如为始,以法身为宗也。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净也,有无均净,未始有名。[注释:《出三藏记集》卷7,2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道安在这里是以魏晋玄学的本末思维方式来理解《般若经》,他把“如”、“法身”视为根本、本体,是不符合印度佛教本义的。《般若经》提倡空观,是破除现象和本体的实有,是否定本体存在的,或者说主张本体是空的。而道安则提倡“以无为本”的学说,把破除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印度佛教哲学的方向,改造了印度佛教哲学的内容,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本体论。
三、编撰佛典
随着佛教的长期流传,中国佛教学者由单纯的翻译转向进行独立研究,融会贯通,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据统计,中国僧人的汉文佛典撰述共约600部,近4200卷。这些著述不仅具有汉民族的思想形式,而且也程度不同地具有汉民族的思想内容,涉及宗教、哲学、伦理、文学、历史等诸多方面,表现了与印度思想不同的风格、色彩、特征。中国佛教学者的撰述是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标志,历代中国佛教撰述记载着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成为我们探寻、开掘、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主要资源。
中国佛教撰述,有以下多种类型:
(1)章疏。中国佛教学者尊奉印度佛教经典,持诵研习,坚持不懈,同时在讲经时加以解释,阐扬和发挥佛典的思想。也有的佛教学者模仿中国传统的注经形式,热心于撰写章疏。这类著作在中国僧人全部撰述中数量最多,居第一位。章疏往往引用中国古典著作的语句和固有思想来注解原文,作出中国化的诠释,借以阐发独立的哲学思想。例如,唐代华严宗四祖澄观撰写多卷本《华严经疏钞》,阐发《华严经》的圆融观念,发展了中国华严宗人的“四法界”说(后详),“四法界”说是中国古代佛教哲学中极为重要的宇宙结构论、现象论和本体论的学说。
(2)论著。中国佛教学者重视创作,勤于写作,撰写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论著。这些论著或为阐发总结佛经要义而作,或为发表独特见解而作,也有不少是在与儒、道两家争论中为“护法”而写的,包含着最丰富的中国佛教哲学思想,有的就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著作。如东晋时南方的佛教领袖慧远,与时人争论沙门应否礼敬王者的问题,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其中有专章结合中国古代灵魂不灭的观念,论述形尽神不灭思想,强调人的形体虽然有生有死,而人的灵魂是不朽不灭的。慧远这种形神不灭的观点,可以说,恰恰相当于释迦牟尼所抨击、拒斥的婆罗门教的观点——认为不灭的灵魂可以寄寓不同的躯体之中。早期佛教认为人的精神是不断变化的意识状态之流,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性的灵魂存在,而慧远则是中国固有的灵魂观念和实体性思想的支配下,去理解人的形神关系问题,从而导致了与印度早期佛教思想的背离,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神不灭论。
(3)经典。中国僧人还撰写了不少佛经。禅宗创始人慧能的《坛经》是中国僧人唯一公开称“经”的著作。这部著作是吸取佛教某些信仰因素,在中国儒、道固有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它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之大是众所公认的。此外,还有另一类伪疑经,是指断定或怀疑由中国汉族僧人编撰、选抄的佛经,不是译自古胡语、梵文的汉文佛经。伪疑经的内容往往与儒、道、佛三教斗争有关,有的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吸取儒、道思想编成的。伪疑经实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其中包含了鲜明的中国化的哲学思想。比如《提谓波利经》是中国僧人为在家信徒撰写的,着重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和持戒修行。此经把中国固有的阴阳五行学说、伦理纲常等与佛教教义结合起来,虽然这种结合不免生硬勉强,但却表现了中国佛教宇宙论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某种特色。
(4)灯录。又称传灯录,系禅宗人创造的一种独特文体,记载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著作,内容以记录言论的“语录”为主,也记载传承关系。重要的灯录有二三十种,其中包含禅师语录不下三百余则。语录大都为禅师口语,由亲随左右的禅门弟子笔录编集而成。语录中记述的是师徒传法心要、参悟验证、方便施行、参学所得等,集中表地现了禅宗的人生理想境界、心性思想、直觉思维,构成了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内容。
(5)善书。指宣传伦理道德、劝人为善的书。佛教善书往往糅进儒家道德观念,宣场儒佛两家的伦理目标和生活规范。如明代名僧云栖袾宏的《自知录》,把人生的行为分为善、过两门,劝人去过从善,积累功德,以获得好报。这种通俗易懂的说教,比正规经典更易为民众所接受,所以影响很大。佛教善书,反映了中国僧人在重建适应国情的佛教伦理道德学说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普及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哲学的成就。
(6)史书。佛教史书记载了佛教历史的发展演变,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史书,尤其是为中国佛教僧侣列传的纪传体史书,有总传、类传和别传等不同类型,记述了佛教代表人物的活动和思想,反映了历代佛教哲学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对于我们了解佛教哲学家的思想内涵和特色,以及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变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判教创宗
隋唐时代,由于佛典的大量翻译,佛教研究成果的长期积累,佛教人才的普遍成长,中国佛教的创造力空前高涨。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大,为中国佛教学者的思想创造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随着这种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佛教各宗派相继成立。在隋唐佛教宗派中,有的适应国情,结合中国固有文化,形成了不同的传承关系和教理主张,也就是偏离乃至背离印度佛教教义而创立的。这些宗派领袖在创宗过程中,各自阐发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精神的哲学思想。
中国佛教各宗派创宗所依据的经典,基本上来自印度。印度佛教不同派别的不同教义、不同经典的不同教理,一方面为理解、阐释佛教义理带来了某些困惑,另一方面,也为创立宗派带来了方便。为了解决困惑,创立宗派,中国佛教学者对印度佛教各类经典进行了统一安排,确定次序的先后和教理的深浅,并且把本宗所尊奉的经典置于最高的位置。这就是判教。中国佛教不同宗派的创始人,依据中国深厚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采取不同的标准、尺度,引导门徒去学习、研究自己所推崇的经典,推动本宗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判教反映了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思考的过程与选择的结果,体现了中国固有的历史哲学和价值观念。
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根源
上面我们论述了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途径、方式,现在要分析的是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根源。所谓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根源,就是中国佛教哲学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根本原因缘自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哲学生态环境”——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环境。只有深入地考察中国佛教哲学形成的“哲学生态环境”,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佛教哲学产生的根由、源头和必然性,进而也有助于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内容和特色。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作为一种在主题、主导思想方面与中国固有文化根本不同的异质文化,必然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碰撞、冲突,这就要求佛教传播者必须根据中国的客观环境,作出必要的反应。中国是一个土地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一个历中悠久、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国。当佛教由西向东,经过千山万水、流沙荒漠,传入中原一带时,面对的是和印度同样伟大、先进的文明古国。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以关怀现实生活、重视道德实践的儒家学说为主导思想的。当时中国官方和文人中还广泛存在着华夏中心主义、中国中心观的思想,更增强了接受佛教的心理障碍。但是,中印两国文化的发展态势和达到的水平是相当的,两国文化的主题差异又为文化互补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两国的不同价值观念对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人群都具有相应的主导意义。这就是说,印度佛教文化和哲学与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既有不相容性,又有相容性,也即存在着把印度佛教文化与哲学加以改铸以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可能性。
中国佛教学者从事的佛教学术活动,就是在中印两种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冲突融合中进行调适。他们一方面受印度文化的规范,另一方面又选择印度佛教文化。所谓选择,包含着排拒和吸纳两个方面,既排拒那些不适应中国国情的思想文化,吸纳那些适应中国国情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说,选择是有条件的,是受中国的种种复杂的因素制约的。选择的后果,就常常出现“郢书燕说”、“种瓜得豆”的现象,以致背离了佛教思想的原义。中国佛教学者在对印度佛教哲学的选择过程中还进行整合工作,竭力把经过选择和自己创造的佛教哲学思想,组织成为一个结构严密的、相对完整的哲学体系。因此,这种整合构筑,最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佛教学者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也是受中国的固有文化和社会需要制约,并受中国佛教学者的主观条件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