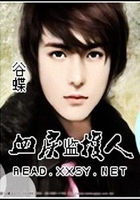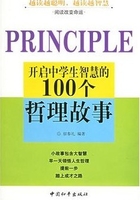跟着怀安走了一圈,柳伊才知桃园有多大。她原本以为这只是府内的一个小院子,想不到竟比整个春花幼儿园还要大上不少,分明是一个江南园林式的大公园嘛!
好不容易来到闲逸居,柳伊感觉自己腿累不说,刚刚的七分饱,又只剩下三分了。她记起怀里还揣了个热鸡蛋,伸手一摸,想了想,又放下了手。
先前怀宁便让人带了话,因此二人一到,候在院外的怀宁便迎了出来,一边见礼,一边笑着说道:“公子这会儿正在听琴,少夫人倒是赶了个巧。”
“还是清音阁的头牌么?”怀安问。
怀宁点头应道:“除了云先生,还能有谁呢?”
“倒也是……”怀安赞同道,说完朝一脸好奇的柳伊解释道:“清音阁的头牌云先生乃民间琴仙,琴技出众,曾誓言效仿古人伯牙,只为知音弹奏。他与叶师父交好,忠人之托来教公子习琴,后因公子染疾,便改为听琴。”
“原来如此。那倒要好好听听。”柳伊闻言顿生向往,便加快了脚步。
闲逸居,与闲云居格局相似,都是坐北朝南的一进大院子,只不过前者位于桃园左侧,后者位于桃园右侧,呈对衬状。院子正中一样以花园假山相隔,东厢依次是琴室、棋室、画室、茶室,西厢则是叶彬的寝居、偏厅、药房与诊室。北边是小灶房,仆人房及储物间。
柳伊随怀安怀宁来到琴室外,往里一望,众人都在。坐着正中闭目弹琴的是一位乌衣男子,约莫二、三十岁,长相极普通,但那种气定神闲、从容自若的气质,倒是能看出几分。
柳伊暗道可惜,长相不够衣来凑,这所谓的琴仙穿着一身黑衣,怎么能显出飘逸似仙的出尘气质来?
瞧见柳伊等人,怀珍伸指到唇边,作了个噤声的动作,然后蹑手蹑脚地出门,将柳伊静悄悄地请了进去,怀安二人则候在门外。
李君临斜倚在软榻上,也没睁眼,看不出来他是在陶醉,还是在瞌睡。李铁与叶彬盘腿坐在他左右两侧,前者淡漠垂眸,后者悠然凝视。
柳伊见没处加塞,便随意寻了一处,坐下听琴。
古琴的音色婉转,意境悠远,艺术欣赏水平要求很高,不只是阳春白雪,更有几分禅的韵味。听琴,很讲究静。一是环境安静,二是心情平静。二者合一,才能更好地领略此中韵味。
大约是柳伊缺了那么点儿慧根,又或者是她听惯了活泼轻快的儿歌,只听了一会儿,便感觉昏昏欲睡。原本还闭着眼有心欣赏,不多时竟迷糊起来。
眼看又要睡过去,她连忙掐了自己的大腿一把。在琴仙面前丢人现眼事小,艺术家们通常心气儿都高,万一她惹恼了人家,小正太不是又少了一点人生乐趣么?
掐完自己,她还贼兮兮地四处瞟着,就怕让人知道了自己欣赏水平低,冠她一个‘对牛弹琴’之类的评语。她的动静并不大,倒霉的是这一瞟,却又撞上了李铁淡淡睨来的目光。
柳伊朝他尴尬一笑,对方却面无表情地垂下眸子,反倒是站在他身旁的怀玉眼尖,虽不敢出声,却朝她瞪了过来。
还好没多久琴声便停了。
云先生睁眼瞧见柳伊,竟是毫不理会,低下头,自顾自地抚着琴身。
艺术家果然心高气傲啊!
叶彬笑眯眯地和他解释了一句柳伊的身份,对方瞟了柳伊一眼,朝李君临很直白地说道:“糟蹋了。”
柳伊暗暗翻了个白眼,什么意思嘛?说清楚,谁糟蹋谁了?!
李君临勾了勾唇,自嘲道:“确是误了娘子。”
“云某是说瑾瑜公子。”看吧,看吧,有才华的人通常情商都低!
李君临眯开眼,认真道:“先生差矣,是瑾瑜之福。”
柳伊闻言感动不已,这小正太就是懂事,招人疼!
她略为一想,便起身朝琴仙施了一礼,输人不输阵地说道:“听闻先生乃雅中仙,怎似那俗人见解?姻缘姻缘,若无几分天定的缘份,不是一家人又怎进一家门?既是天定姻缘,何来糟蹋之说?”
可惜琴仙似乎是个沙猪,别开眼,根本不与柳伊对话。
柳伊也不着恼,又侃侃道:“若论年纪差异,寥寥数载,韶光易逝,携老时也不过是一双垂暮,谁又比谁年轻?若论皮相,红颜白骨,纵然倾国倾城,谁能抵挡时光之刃?若论身份家世,父辈荫泽,岂能算作自身能耐?况且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后事难测,莫欺少年穷。若论才华……”
被一个妇人如此辩驳,琴仙只觉颜面无光,摆着手打断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古人诚不欺我!”
柳伊扑哧一笑,指了指李君临,狡黠道:“他是小人,我乃女子,可不正是天作之合么?谁又糟蹋了谁?”
“女娃娃切莫张狂,你方才所言,都是大不逆之道,若然传出去,定然惹祸端。念在你是妇人之身,云某不与你计较,但奉劝你谨言慎行,莫连累了李氏一族……”琴仙愤愤道。
柳伊本就是赌气,被他这一说,虽然不服,但回想方才所言,却也暗自担心起来。她撇了撇嘴,没再回话,只希望这琴仙节操有下限,莫做了喜爱搬弄是非的八公。
琴仙见她不语,便冷笑了一声,起身抱琴,朝李君临与叶彬揖礼道:“今日无端被妇人相扰,失了琴意,云某先行告退了。”
叶彬本是兴致勃勃地看着好戏,见此便起身回礼相送,歉意道:“妇人之言,就如同童言无忌,长天兄听过则罢,切莫耿怀于心。”
“哼!”云长天悻悻地甩袖而出。
叶彬饶有兴致地瞟了柳伊一眼,施施然随后跟了上去,将云长天送出了桃园。
李君临目送二人离开,示意李铁扶自己坐起。待坐好后,他朝柳伊望去,还未说话,对方已不声不响地低头回座继续绞着手装小媳妇。他顿时失笑,这个‘伊伊姐姐’,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有趣,他倒是真没见过这么单纯的人。就连怀玉,都晓得暗中使坏,她的心思却是毫不遮掩。
不过,能遇到这样的‘娘子’,很庆幸……
“云先生并非恶人。”李君临道。
“嗯,我知道。”柳伊状似乖巧地应了声,随即抬头望了望李君临,奇道:“咦,临儿又有力气说话了?”
“每日由叶师父诊治之后,公子的情况总会好一些。只是一旦过了午时,又恢复原样了。”怀珍淡淡地替李君临解释道。
怀玉瞅了瞅李君临,补道:“倒也奇,今儿个公子的气色确实较以往有所好转,说话时中气也足了些。”
闻言怀珍与李铁仔细打量了李君临一会儿,略带欣喜地点头赞同道:“看来公子不日定将大好了。”
“既然诊治确有疗效,为何不再继续施针泡澡?”柳伊有些不明白了。
怀珍与怀玉闻言很是泄气,沉默了会,才听得怀玉低声嘟囔道:“若是使得,怎会不用?姐姐是不知个中痛楚,非常人能忍……”
李君临倒是无所谓地淡淡一笑,答道:“太费事。”到底不是根治之法,何苦为了那一点点微薄之力,费时费力费财地自找苦吃?
“……”柳伊无语,想了想,讷讷劝道:“病痛病痛,病了哪有不痛的?临儿暂且忍耐,或许多诊治几次,便能好转呢?但凡有一丝希望,咱们都不该放弃。”
“公子才不是畏痛怕麻烦,只是不想耽误学习罢了。”怀玉大声替他辩解道。
“身体才是最大的财富,都病成这样了,还学什么?”柳伊瞪着李君临,恼道:“你就是修成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才子,又如何?还不是照样连说话都力不从心?倒不如好好养病,踏踏实实地过好小日子,待他日能活蹦乱跳时,再求学事。”
“只为乐趣罢了。”李君临淡然道:“生死由命,强求无益。”
“就你超脱……”柳伊白了他一眼,低头喃喃自语道:“看来这古琴什么的,就不该让小屁孩听。瞧把人都祸害成啥样了哟,小小年纪都看破生死了……”
叶彬回来后,众人移步至棋室,师徒俩切磋起棋艺来。怀玉帮李君临下子,怀珍候在一旁,不时吩咐怀安与怀宁端茶递水,李铁则按着李君临之意,替他不断调整身姿。
柳伊一看,根本没自己的事,围棋她又不懂,也不好与众人探讨五子棋与围棋的渊源,或是研究飞行棋的奥妙,便干脆告退打道回府了。
跟着怀安回到闲云居,张罗着用过午膳,柳伊想到钱银问题,便问明了情况,带着怜儿一起到专属于她的库房查验嫁妆。钥匙早在昨夜闹完洞房时,便由温氏转交到她手中,因此二人毫不费力地进了屋。
可惜这么一看,柳伊是彻底无语了。
大箱小箱倒也装了十来箱,可除了十多身四季成衣,一小盒原主娘亲留下的首饰和二十两封银,便多是些莫晚其妙的琐碎玩意。比如:剪刀、痰盂、尺子、荷包、腰带、花瓶、铜盆及鞋……诸如此类。
反正柳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解释为柳府抠门抠到家,拿家里不要的东西充嫁妆。
算来算去,整个库房里头,最值钱的,反而是她入门时穿的那身凤冠霞披,以及李君临挑盖头时用的华丽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