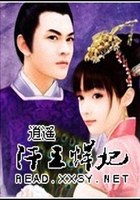过了半个月,善常忽然把清婉叫了出去,清婉到了正殿,见是四福晋来了,却不明白为什么特特把自己叫来。
平时给四福晋奉茶,四福晋当然不会正眼看一个下人,这一次清婉上去请安,四福晋却拉住她打量,见她执礼甚恭,又大方不畏葸,甚是喜欢:“额娘,这就是凌柱家的姑娘?果然体面。”
德妃道:“你喜欢便好,上次你来说弘昀病了的事,我就寻思着要给你找个帮手,我贴身的人,老四未必待见,我又离不得,这孩子来了一年多,原是侍候茶水的,稳重妥当,很难得的,性子又温和,进了府,断不会给你添乱子的。”
清婉听到这儿,明白自己是被赏下去了。
德妃觉得这也是为了她好,又道:“我打听了下,敢情凌柱夫妻只有这一个女儿,这一进宫,二十五岁才得出去,出去了也嫁不到好人家了,倒不如跟了老四,要是她有造化,得个一儿半女的,将来也不用愁了。”
清婉简直不知作何感想,只听四福晋道:“额娘放心,我一定不会亏待她。”
于是这事便定了下来,其中没有她置喙的份儿,她惟一需要做的就是跪下谢恩。
四福晋姓乌拉那拉,早年有个儿子叫弘晖,是四阿哥的嫡长子,可惜乌拉那拉氏生了弘晖后便不能再生养了,弘晖长到八岁又夭折了,如今四阿哥的两个儿子都是侧福晋李氏所生,李氏是个沉不住气的,恃子而骄,乌拉那拉氏性子虽好,心里也未免不快活,所以她爽快地答应要清婉,也是有自己的一番打算在内。
胤禛差事在身,尚未回府,乌拉那拉氏将东跨院东厢房拨给清婉,又按例派给她下人。
胤禛妻妾儿女都少,东跨院在清婉来之前是没人住的,院内几套房都长年锁着,刚刚搬进去的时候,清婉总觉得屋里有股很浓的霉旧味儿。
等到安顿下来,日子倒也不难过,除了每日例行的请安和偶尔的往来外,其余时间把门一关,就可以自成春秋了。
不过,尽管饮食起居比以前精细许多,她却并没觉得处境有什么改变。
这不过是一个缩小的皇宫,在皇宫好歹还有十年的期限,在这儿却要待一辈子。
东厢房左间窗前有株桂树,清婉却是喜欢,虽然入了秋桂花才开,春天一树绿叶碧油油的,却也生机盎然。
平日清婉坐在窗前做做针线,抬头望望窗外树影,心里便觉喜悦安稳。
如此过了一个月,她晚上开始乱梦不断。
梦里风过树梢,发出簌簌声响……
清澈见底的溪流沿着峰底蜿蜒而过……
这是……哪里?
有小兽窸窸窣窣穿过树下的长草,树上却“啪”的一声,飞出一枚桃核,小兽吓了一跳,毛茸茸的大尾巴一甩,匆匆钻进草丛。
小女孩清脆的笑声水珠一样从树顶洒下来,枝叶被分开了,露出一个小小的身影,却被日光模糊了轮廓,看不清楚面目……
“灵儿,快下来!又乱跑了!叫师父担心!”
洪亮的声音撞进心里,擂鼓一般将她惊醒。
冷汗浸透衣衫,她睁着眼睛,在黑暗里怔了半晌。
此后的每夜,她都从相似的梦境中惊醒,她心里知道,这不仅仅是幻梦,梦里的一幕幕,必定与她失去的记忆有关。
她有时在院子里,扶着桂树的树干出神,一站就是半天,期望能忆起些什么来,无果后,她又时不时往后花园去,那儿树木葱茏,与她的梦境最为相似。
四月里的一天,她又准备出门,丫鬟冰梅拦住她道:“格格,贝勒爷这两天就要回来了,万一过来了格格不在……”
清婉一心想记起前事,闻言并没放在心上,笑道:“没事。”
“那奴婢陪格格去。”
“不用了,园子里还能出什么事不成?”
丫鬟彩鸾正倚着院门嗑瓜子,见她出来,福了一福让开,等她走出很远,方对冰梅道:“我瞧咱们主子也不是个有造化的,出身又低,又不知道讨好人,虽是娘娘赏下来的,可谁不知道贝勒爷跟娘娘不和?咱们跟着这位主子,是没机会出头了。”
冰梅沉默一下:“格格性子很好,从不打骂下人。”
彩鸾嗤笑:“性子好有什么用,你也是个没出息的。”扬扬回头,却见远远地,清婉回过身来往这边看了一眼,虽然隔得那么远,清婉不可能听到她说的话,彩鸾还是吓了一跳,陡然感到一阵心虚,忙匆匆回屋。
时值暮春,繁花开得烂漫如锦,园中一道水渠,因为引了活水,清碧异常,能镜子似的将人照得纤毫毕现。
清婉立在渠边,对着水中清清楚楚的倒影。
那一身天蓝旗装的少女就是她么?为什么会有种挥之不去的陌生感?
“你是谁?”她不知不觉轻声问。
自然没有回答,头顶飘下几瓣素白的梨花,落在深绿的水面上,轻轻漂浮着,好像青天上的几粒疏星。
梨树上有雀鸟鸣啾,清婉伸出手,一只乌背雪腹的小雀“嗖”的飞下来,停在她纤细的手指上。
清婉微笑,颊上酒窝若隐若现,对小雀道:“嗯,你从哪儿来?”
对岸响起脚步声,雀儿受惊,振翅飞起,转眼不见。
清婉一笑,看向来人,认得是侧福晋李氏房里的两个丫鬟。
贝勒府里的丫鬟,都是一个打扮,一色青绸背心,红绫裙子,发式也是一样,新来者往往辨不出谁是谁,只有清婉从未认错过。
两个丫鬟走近,看见清婉,只得过来,马马虎虎行了礼,其中一个笑道:“婉格格一个人到后花园赏花哪?怎么也不叫人跟着?”
十余名长随簇拥着一顶八抬凉轿穿过街市,停在贝勒府门前。
从人中一个身着青色宫服的小太监撩起轿帘,笑道:“爷,到家了。”
轿中人“嗯”了一声,伸手扶住轿门。
轿门被漆成红色,阳光下更显鲜明,衬得他修长手指,根根剔透如玉。
他俯身出轿,直起腰时抬头望了一眼,日光很盛,他红绒结顶冠上的东珠都仿佛要在这日光里融化了,似乎很不喜欢这样的强光,他随即低下头,转身跨过轿杠,走进大门。
先到大书房换了便服,再到福晋房里看视,乌拉那拉氏交代了后院诸般事务后,笑吟吟说了一句:“给爷道喜。”
“何喜?”胤禛坐在榻边吃茶,听完福晋的答话,微微扬起眉毛,“哦?”
乌拉那拉氏道:“我叫她来给爷请安。”
胤禛摇了摇头,问道:“谁家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娘娘说了什么?”
乌拉那拉氏一一答了,胤禛又道:“你瞧着可还规矩安分?”
乌拉那拉氏笑道:“这爷就不用担心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再叫她来吧,这会儿就不必了。”胤禛站起身,“你歇着吧。”
乌拉那拉氏见他并没什么欢喜,心里倒不自在起来,一时别的话也不便说了,只好起身相送。
胤禛喜欢独居,除了晚饭跟福晋一起吃之外,一天的起居都在大书房里。
打理大书房的,是他最宠信的贴身小太监玉坠子,此刻正候在门外,见胤禛出来,躬身笑道:“两位小主子念着爷呢,爷可要去看看?”
胤禛点了点头。
李氏住得较远,中间隔着后花园,走过假山旁的鹅卵石小径时,隐约听见水渠边传来说话声。
只听一个女子声音道:“贝勒爷就快回来了,格格就算不在房里守着,也不该随便乱跑吧?我们这些当下人的是没办法,格格可是主子。我们主子的两个小阿哥,昀哥儿和时哥儿,格格还没见过吧?当主子的都是前世修来的,前世积德,这辈子就有富贵可享,前世造孽,这辈子就要吃苦,我们主子不是前生积德,哪来这样的福气?格格既有空闲,也该像我们主子那样,潜心礼佛才是。”
胤禛皱眉,看了一眼玉坠子,玉坠子脸上陪笑:“这说话的,好像是李福晋的丫鬟……”心中甚是恼火:李福晋怎么管教丫鬟的,说起话来上下尊卑都不分了!
另一个女子笑了起来:“你看这一树梨花,本无什么区别,然而风一吹,落英纷纷,有的飞入罗帏,落于锦罽之上,有的飞到路旁,落于泥淖之中,境遇便立刻不同,所谓富贵贫贱之分,只看这一阵风,把你吹到哪儿,跟报应因果,又有什么关系?”
少女的语声低柔而清晰,音色至美,一番话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任人胸中有千思万虑,也被荡涤一清,只余澄静空明。
胤禛心里一动,微笑着想:此乃西方迦陵鸟,却是从何而来?
两个丫鬟涨红了脸,想要反驳,清婉到底是娘娘赐下来的人,好歹也算半个主子,说得过火惹恼了她,自己也讨不了好,只得勉强忍了气,告退离去。
清婉被这么一搅,也有些索然,正想回东跨院,忽觉水渠对面有动静,一惊抬头,却见假山后缓步走出一个男子。日光强烈,他逆光而来,看不清楚面目,只觉举止沉着,步履稳重,身材修长挺拔,着一件银灰长袍。
清婉怔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他是谁,如梦方醒,跪下道:“贝勒爷吉安。”
胤禛走到渠边停下:“起吧。”
清婉缓缓站起,两人隔水而望,清婉这才看清他的眉目,犀利如刀剑,清峭如冰峰,即使在炫目的阳光下,都似乎带着淡淡的寒意。
胤禛却觉她坦然得出奇,自己久久不说话,她也不紧张,清澈的眼波里偶尔流出好奇的神色,而嘴唇微微翘着,却仿佛时时欲笑,不由微微仰头,无声地微笑起来。
这微笑一瞬即逝,快如庭院里晴丝的隐隐一闪。
此刻她身后的梨花素白如雪,他脚边石缝里的海棠却开得鲜艳,仿佛绣了一地的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