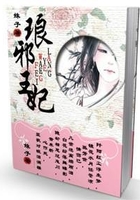承德自被辟为皇帝避暑之地,几十年间,渐渐热闹繁华起来,关外地方,马市尤其兴盛。
马市角落里,一个马贩子正坐在石墩上抽着旱烟,忽听有人问:“这马怎么卖?”马贩子一扭头,惊讶地发现问话的是个女人。
女人裹了一件灰色江绸披风,披风宽大,兜帽将大半个脸都遮住了。
女人来买马不常遇见,但也不是没有,想到这必是个江湖人,马贩子先存了个小心,笑道:“您真好眼力……”
女人道:“不必多话,报个数吧。”
马贩子咽了口唾沫:“五十两。”
女人从怀中摸出一张银票递了过来。
肌肤莹润的手,指甲都修剪得整整齐齐,花瓣儿似的贴在雪白的指尖上,马贩子心里纳闷,不过只要银票毋庸置疑,其他的他也不想多问,二话不说,爽快地把缰绳给了女人。
买了马,又购了些金创药,趁手的兵器一时半会儿却找不到,清婉只得将就买了一柄短剑。
这十年她武功未有进益,摄魂之术又极费精神,使钱氏安睡后,她自己也深感疲惫,只是这紧要关头,容不得半点耽搁。
一出承德,清婉立刻快马加鞭,直奔木兰围场。
等她赶到,围场却已戒严了。
清婉听到军士议论,只知皇帝无事,刺客逃逸,如今正在四处搜捕。
清婉心中焦虑万分,好在她随胤禛来过一次,多少知道周围地形,当即绕到偏僻处,敲晕一个落单的旗兵,剥了他的衣服换上,弓箭也一并搜走。
骑马进入莽莽山林,一种久违的熟悉感扑面而来。
天色已暗,正适宜潜藏,清婉行至一丛灌木旁时,猛听风声呼啸,一把雪亮钢刀带着胳膊粗的沉沉铁链,从灌木后飞了出来,清婉见这来势,哪敢硬接,足尖连点,向后连跃四五丈,方才避开刀锋,那钢刀在空中划了个诡异的弧,所到之处无坚不摧,清婉猛地认出这招式:“大师兄,是我!”
钢刀嗖嗖收回,了因破开灌木丛跳出来,紧跟着是广慈和路民瞻,其他几个师兄也陆续现身。
清婉见七人均在,心中顿时一阵狂喜。
路民瞻臂上中箭,草草包扎了一下,见了清婉,一愣之后欢喜叫道:“师姐!”
白泰官扶着甘凤池,咧嘴笑道:“我就说么,灵儿一定会回来的!”
甘凤池却捂着腰间,脸色灰白,清婉见他指缝间的血都已成了黑色,嘴唇也隐隐泛紫,惊道:“三哥,你……”
“老三中毒了,”曹仁甫道,“又伤在要害地方,亏得他功力深厚,否则当时就没命了。”
为免元气溃散,甘凤池不能说话,只向清婉点了点头。
清婉把来时准备的金创药都给了广慈,又将坐骑缰绳递了过去:“师父,你们快些带三哥下山,我来断后。”
路民瞻吃了一惊,一把拉住她:“师姐,你不跟我们一道走?”
清婉回头微微笑道:“小七,师姐还有事没交代,不能离开。”
广慈道:“灵儿,你……”
清婉摇头:“师父,我从不对你说谎。”言罢一笑,“身入清水,心怀日月。生死原是小事,何况我不会让自己轻入险地,待此间事了,将来必有再会之日。”
广慈见她说得通透,叹道:“你自己千万小心。”
周浔见她没有趁手兵器,将自己的长剑递给清婉:“说话算话。”
清婉接过,重重点头。
夜幕覆盖了山林。
草木的气味清新而浓烈,夜露**了头发和衣鞋,要不是心头那根弦紧紧绷着,清婉几乎要以为,自己已经回到了天台山。
远远地,有火光一闪,清婉凝神,隐约听到马蹄声疾,正往这边而来,清婉跃上一株合抱粗的白桦,藏身树冠。
“刺客是往这边跑了?”
“是!奴才们瞧得清楚!”
清婉屏住呼吸,只见唰唰几道刀光,灌木长草被砍倒分开,一个青年带兵纵马而出,火光明灭之间,清婉依稀瞧见他的眉目,只觉甚是眼熟,旋即想起,这是胤禛的同胞弟弟胤禵。
胤禵武功不凡,清婉也有所耳闻,心想是他去追的话,怕是有些麻烦,又见胤禵身边只有十余人,并不算很难对付,便悄悄取出弓箭,搭箭在弦,瞄准胤禵,手指扣住弓弦,慢慢拉开……
“老十四?”
树丛分而复合,又有一队人马来到,清婉听得这个声音,心中一惊,蓄势待发的箭顿时停住了。
“四哥?”胤禵道,“这是怎么了?四哥遇到刺客了?”
“刚刚碰见一个和尚,十分厉害,我身边的人当场死了六七个,这几个奴才的伤算是轻的了。”胤禛的声音淡淡响起,“我瞧见他往这边来了,就一路追了过来。”
清婉听他语调平稳,知道弘历应当无事,心中一块大石落地。
却听胤禛又道:“有个刺客被弘历扎了一匕首,龙须匕淬有剧毒,那刺客虽未死,想来也行动不便,老十四,你挑几个身手好的,跟我骑马去追。”
清婉听得分明,眼前一黑,差点没摔下树去。
难道甘凤池那极重的伤势,竟是……
胤禛胤禵正要离开,忽然,胤禛像心有所感般,往清婉藏身之处望来,清婉虽知他不可能看到自己,心中仍是猛地一悸。
好在胤禛随即拨马而去,清婉想着他方才的话,死死咬住了下唇。
最终刺客仍是逃逸而去,至于皇帝的震怒就不是清婉所关心的了,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她连夜赶回了狮子园。
钱氏每日吃斋念佛,一无所察,到了第七日上,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清婉正站在门外,脸色苍白如雪。
钱氏唬了一跳:“格格?!”
清婉向她笑了一笑,慢慢软倒。
胤禛早已遣人往狮子园报了平安,福晋格格们也是每日念佛,冰梅心有余悸,虽见清婉元气大伤,却也不敢再说不该斋戒的话,私底下又与小柿子念叨:“原来上天示警的事是有的。”
清婉心力交瘁,只盼着弘历早日回来,问明匕首之事。
“额娘!额娘!”几日后,弘历回来了,一路跑着进门,一头扑进她怀里,死死抱住,随即哽咽起来,“额娘……儿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清婉心中五味杂陈,将弘历抱到膝上,擦净他白嫩面颊上的泪痕。
弘历自幼随性音习武,身体强健,手脚灵便,比一般孩子有力得多,但要说他能刺伤甘凤池,清婉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
跟随弘历回来的玉坠子在旁将皇帝遇刺的事说了一遍,清婉问道:“王爷现下怎样?”
“格格放心,王爷无恙。”玉坠子道,“皇上也没事儿,就是哈达亲王不幸罹难,如今木兰已被封锁,王爷还要收拾局面,小主子待那儿不妥,王爷便命奴才把小主子送回来。”
清婉点了点头:“有劳玉公公。”却听弘历道:“额娘,儿杀了人!”
清婉脱口道:“什么?”
玉坠子道:“是有个刺客被小主子扎了一匕首,只是那人当时没死,不过小主子的匕首上淬了毒,想来那人也撑不了多久了。”
清婉脸色顿变,极力压抑住情绪,勉强道:“是么?弘历的匕首……听说是皇上赐的?”
“嗯!额娘要看么?”弘历跳下地,取出那把匕首,出鞘时,刃上蓝光一闪,果然有毒。
弘历道:“这是‘龙须匕’,淬了龙须草之毒。”
清婉只略懂一点医药,龙须草之名却是没有听说过,但想起甘凤池那极重的伤势,若不是剧毒,以甘凤池功力,断不至于伤到那个地步,一念及此,她连忙握住弘历的手,将匕首插回鞘中:“皇上怎能……把淬了毒的匕首给你,若是不留心割破了皮,可如何是好?”
弘历认真道:“额娘不必担心,皇爷爷说,当年皇爷爷自己得赐这把匕首时,跟儿差不多大呢,儿自会小心。”说着弘历又骄傲地一昂头,“儿若是那么不知轻重,可就配不上皇爷爷的赏赐了。”
清婉问道:“此毒可有解药?”
弘历点点头:“儿这儿没有,皇爷爷那里收着。”
清婉沉吟一会儿,道:“你一个孩子,怎么就能伤了刺客……”
“也是儿的运气。”弘历仰头道,“其实那刺客不坏,儿险些从观猎台上掉下去,还是他拉儿一把,可他要行刺皇爷爷,就是罪该万死的逆党,所以他拉住儿的时候,儿便趁势刺了过去,正刺在他腰上。”
“罪该万死的逆党……”清婉苦笑,抬手捂住脸。
“阿玛说,皇爷爷没空照管弘历了,这段时候,弘历都会在家了。”弘历不知母亲心里所想,扑闪着眼睛道。
玉坠子笑道:“这是王爷特意叫小主子带的话。”
“他有心了……”清婉默然。
弘历笑道:“皇爷爷待儿好,可儿还是喜欢跟额娘在一起!”
因为皇帝遇刺,这年的秋狝不得不匆匆忙忙中止。
虽然圣躬无恙,却搭上哈达亲王一条命,其余侍卫军士的死伤,更是不可计数,这让康熙恼怒非常,但御驾回京之后,他第一道旨,却是封胤禵为大将军王。
“皇上必然要追查那批刺客的下落,如今胤禵去了西北,江南这一趟差,九成要归我了。”胤禛从清婉手中接过茶盏,漫不经心道。
“王爷怎么知道刺客从江南来?”
胤禛淡淡一笑:“南方??暴客,杀夺为耕耘。靴刀裹红帕,行劫无晨昏。事主诉县官,县官不敢问。这是沈德潜的折子上所附之诗,刺客从何而来,想都不用想。”
清婉垂下长睫:“是这样么?”
胤禛携住她手,笑道:“江南虽烟柳繁华,凶险处却不下于西北的铁马黄沙,这差事没有一年半载,恐怕是办不下来的。”
清婉道:“府里有福晋在,王爷不必担心。”
胤禛摇头道:“我不放心弘历。”
清婉微微笑道:“王爷在他面前,可不能说什么放不放心的,否则他一定吵着要王爷带他去。”
胤禛忍不住笑了起来:“可不是。”
清婉道:“我有时抱着弘历,回想他襁褓之中的模样,仿佛就在昨天一般,七年弹指一挥便过去了,他很快就会长大的,王爷。”
胤禛见她笑容有些恍惚,微觉疑惑,正要开口,清婉又道:“王爷要出远门,有件事,我得告诉王爷。”
“什么?”
“那天马把我甩进河里,凉水一灌,倒让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
“哦?”胤禛奇道,“说来听听。”
“别的也没有什么,”清婉微笑道,“只是有件事,我爹娘大概忘记了,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哭过。”
胤禛一怔,只觉她清凉的手指冰雪消融般从自己掌中挣脱,清婉慢慢跪下,口齿清晰地说道:“王爷,奴婢告退。”
“柿子,你跟我多久了?”
小柿子正忙着摆盆景,闻言也未在意:“奴才十一岁跟了格格,也快十年了。”
清婉点了点头:“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小柿子一怔:“奴才能有什么打算?自然是一辈子伺候格格了。”
清婉道:“那要是我不在了呢?”
小柿子大骇,转身跪下道:“格格这是什么话?格格一定长命百岁!”
清婉道:“你起来。我知道年长些的公公都会在宫外府外置办产业,你年纪轻轻,自然没有什么积蓄,我也帮不了你太多,王爷待我虽然不错,逾分的赏赐却是没有。”
小柿子道:“王爷对格格的好,原也不在这些上。”
清婉唇边浮起浅淡笑意:“我知道,他给我的,远比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贵重得多,是不是,柿子?”
对着那清亮的目光,小柿子不由得后退一步:“格格,您为什么这么看我?”
清婉冷不丁道:“你在粘竿处待了几年了?”
“……”
“你不必害怕,”清婉笑了一笑,“其实早些年,我就隐约猜到,只是最近,看得更清楚了。粘竿处,粘竿处,其实夏天的蝉噪响一些,又有什么呢?真正搅扰王爷清静的,在府外啊。”
“格格!”
清婉道:“你十一岁就跟了我,手上还是干净的,趁没有陷得太深,向王爷讨个清闲的差使,远离了这京师吧。”
小柿子又跪了下去,重重磕个头道:“格格,跟您之前,王爷就对奴才说了,这辈子奴才的眼里只有格格,奴才只听格格的话,格格不要奴才,奴才只有死路一条。”
清婉道:“没有谁离了谁就活不下去的,你既然只听我的话,那我要你以后永远不许提这个‘死’字。”
她慢慢走出门,屋外晴空万里,天蓝得无比纯粹,没有一丝杂色。
廊下红嘴绿毛的鹦哥叫道:“格格出来了!”清婉伸手,轻轻逗它,鹦哥侧过头,颈子擦着她纤长的手指,十分惬意的模样,嫩黄的脚爪动了一动,拴在腿上的细细金链碰出清碎的轻响。
“被人养在金笼子里,吹不着风,淋不着雨,其实也不坏,是不是?”她用几近耳语的声音低喃着。
可惜,她不是鹦哥,天下之大,她终究要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