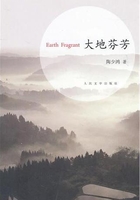刘稷说:“既然来了,总得进吧?进去咱再想办法。”
刘秀急忙阻拦道:“慢!城还是要进的,只有进城才能摸清情况。不过,这三匹马不能进,因为它们太扎眼,还是留在城外好。为了小心起见,咱们只有徒步进城了。”
“还是文叔考虑周到。”刘稷、朱祐表示赞同。三人转辔返回,把马匹寄养在路边的一家客栈里,这才轻松愉快地向城门走去。
守城的官兵对徒步而行的三人,果然没太注意,只是随便地盘问了两句,见他们确实像行商之人,便放他们进去了。
宛城城内,完全不见了往日的繁华热闹,街上到处冷冷清清,偶然有几个行人,也是脚步匆匆,生怕稍作停留就会招来灭顶之灾。两旁的店铺大多都关门打烊。一队队官兵横冲直撞,惊得鸡飞狗叫。刘秀一看这情形,心头凉了半截。心想李通、李轶肯定出事了,是生是死也未可知。
三人躲到僻静之处一商议,决定还是先弄清真相,再做打算。刘秀抬头一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位年约五十的老者坐在路旁卖茶叶,便装作茶客,走到他跟前,很随意地问道:“老人家,城里怎么乱成了这个样子,您的生意也不好做吧?”
老者打量了他一眼,沮丧地说:“可不是么,城里出了大事,我这小本生意也就更难做了。”
刘秀故意惊讶地左右看看,问道:“到底出啥事了?怪吓人的。”
老者审视着刘秀,连连摇头说:“年轻人,不必过问,免得招惹麻烦。这两天,不知有多少多嘴多舌的人丢了性命哟。”
刘秀看他有为难的神色,遂掏出一块银子扔到茶摊上,笑着说道:“放心吧,我是刚来宛城的买卖人,同行是一家么!想知道宛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能安心留在这做买卖,请老人家帮帮忙吧。”
老者见了银子,眉开眼笑,小本生意,即便他干坐一个月茶摊,也难挣得这多的银两。再说了,他看刘秀年轻英俊,不像是官府的暗探,也坏不了他啥事。这才急忙将他拉到一处断墙的后面,低声说:“客官有所不知,这城里有个姓李的弟兄二人图谋聚众造反,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太守甄大人就把姓李的全家都抓了起来。今日申时要在西市口开刀问斩,焚尸示众,连小孩也不放过。城里的人都被官兵们赶到西市口观看杀人去了。唉,惨哪!”
刘秀一听,热血直往上涌,想不到李通一心匡复汉室,竟遭此大难。他强忍悲痛,告别老者,把打听到的情况告诉刘稷和朱祐。
朱祐一按衣内的短刀,愤然地说:“咱们马上去西市口,杀官兵,劫法场,救出李氏全家性命。”
刘稷也满腔怒火道:“李通、李轶一心复汉,不想遭此劫难,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刘秀打断两人的话,口辞严厉地说:“千万不可鲁莽行事,西市口咱们一定要去,但一切必须得听小弟的安排,明白吗?”
二人异口同声,点头答道:“明白!”
“走!”二人尾随刘秀向西市口走去。
西市口在宛城的西北角,历来是官府处斩犯人的地方。刘秀三人匆匆忙忙地赶来,老远就看见此处人山人海,旌旗招展,正中的高台上,执戈仗剑的新朝官兵,围在简易监斩棚的周围。
三个人好不容易地挤进人群一看,只见无数的官兵全副武装,刀戈并举围成了一个大圆圈,正中的场地上,一字儿排开跪着发辫散乱,背插亡命牌的待决犯人,每个犯人的身后都站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他们个个怀抱鬼头大刀,寒光闪闪,令人不寒而栗。
天色阴沉,冷风凄凄,刑场上虽然人山人海,但却静得怕人,只有随风飘摆的旗子,发出哗啦啦的声音特别刺耳。忽然,“哇”的一声,从刑场正中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人们的心一下子被勾了起来,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婴啼的方向。只见待决犯人的队列尽头地上,躺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婴儿的旁边,同样站立着一个面目狰狞的刽子手。
人们听着那撕心裂肺的啼声,望着那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心都碎了,泪水涌满了各自的眼眶,愤怒的火焰胸中燃烧。
刘稷、朱祐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悄悄地将手伸进内衣中,紧紧地握住短刀的柄,急不可待地要冲上去与新军拼个你死我活。但没有刘秀的发话,他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刘秀此刻的心也被怒火烧焦了,他奋力地挤到最前面,仔细在待决犯人中搜寻,从头到尾,又从尾看到头。连嗷嗷待哺的婴儿,李氏门宗男女老幼总共六十四人绑赴法场行刑,却不见李通、李轶的影子,他心中才略有一丝安定。可是,他又总害怕自己没有看清楚。因为犯人待决,发辫散乱遮住了面部,让人难以辨认。待他正要再细查一次,忽然刘稷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衣袖,俯身低语道:“文叔不用担心,李氏兄弟肯定逃脱了此劫,愚兄我细查了几遍,里面没有他们二人。”
刘秀这才彻底的放下心来,为了不引起官兵的怀疑,忙拉着二人往人群里退去。
婴儿的啼哭声,不但撕碎了众人的心,同时也惊动了监斩官。从监斩棚里走出一个穿着都尉官服的中年人,目光阴冷地扫视着围观的人们,大着嗓子说道:“列位,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我宛城官兵同心,一举捕获图谋反叛朝廷的李氏全家六十四口。看他还能哭几声,等一会儿,申时已到,这些大逆不道之徒就要王法加身。前队大夫甄大人亲自监斩,大人要在下告诉诸位,他还有几句话要跟宛城的百姓们说说。”
人群中一阵骚乱,发出了嗡嗡的议论之声,刘秀忙向身边一位老者打听道:“请问老先生,刚才那位大人,他是谁?”
老者小心地打量着四周,然后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刘秀的衣襟,俯身低语道:“年轻人不是宛城人吧?难怪你不知道,他就是新任南阳属正梁立赐,听说此人还是当年摄皇帝府上的心腹家将,咱们宛城百姓认识他的人也不多,可是,知道‘梁刺头’的人倒不少。”
“梁刺头?”刘秀更是疑惑不解地问。
老者咬牙切齿地说:“梁立赐杀人如麻,老百姓就暗地里送给了他个‘梁刺头’的绰号。”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刘秀点点头默记在心里,突然见监斩棚里又走出来一个年约五十岁,身穿官服大冠的人,此人刘秀虽然不认识,但他知道他就是南阳太守甄阜无疑。
甄阜走上台前,满脸堆笑,双手抱拳,声音洪亮,装腔作势地说:“各位父老乡亲,下官有幸破获李氏谋逆一案,实是仰赖陛下齐天之恩德。我宛城官民既是新朝子民,理当剖心沥胆报效陛下,尽忠于朝廷,恪尽臣民之责。可是有乱民如李氏者,不思君恩,悖逆纲常大义,密谋叛逆朝廷。今日得此下场,实是天不容他。南阳之民,是否还有像李氏一样,有不轨之心的么?就请刑场下看一看。胆敢悖逆犯上,图谋不轨,李氏一家就是前车之鉴。本官顺便说一句,李氏一案,尚有主犯李通、李轶侥幸漏网脱逃,有知情的,举报官府,自有千金官位之赏。若知情不报,藏匿钦犯者,罪同李氏,灭其宗族。”
人们对甄阜那鬼哭狼嚎般的叫喊并不害怕,怕的是他那阴惨可怖的脸上突然笑容凝固,歇斯底里地吼叫一声:“时辰已到,行刑!”
蓄势以待的刽子手几乎同时举起了鬼头大刀,围观的人们再也不忍心看下去,纷纷闭上了痛哭的泪眼,只听鬼头刀“嚓嚓”劈下的声音,婴儿的啼哭声戛然而止。睁开眼看时,刑场上血流成河,人头乱滚,吓得胆小的人们惊叫着往外奔跑。
忽然,梁立赐阴冷地大笑一声,指着混乱的人群怒吼道:“都给我堵住,一个也不准走,就是要让这帮刁民看看反叛朝廷的下场。来人,架火焚尸!”
梁立赐一声令下,场中一堆准备好的干柴被点着,顷刻间火光冲天,兵卒、刽子手立刻把身首分离的李氏六十四具尸体扔进火海中,不多时浓烟翻滚,一股烧焦了的尸臭味在空中弥漫,呛得周围的百姓们咳嗽不止,不少人恶心得连胆汁都呕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