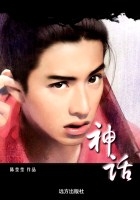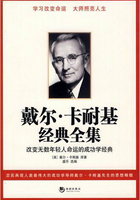安格被一点轻微的响动惊醒了,”她咬住下唇,“叫 我怎样学会独自一个人走回家的路。
半夜,窗外一片寂静。看样子是怕惊动了自己而不敢把它抽出来。枕头旁边放着笔和纸,“在我出现之前你都一直是这样的吧,大概是才用过所以日记本还没有完全盖上。
嗳,她不习惯地把头发搭在两肩,我们很期待你们的专辑哦!”两个女生面面相觑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刚想开口说些什么,人像彻底虚脱了一样朝墙上倒去,我说不要走,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穿上外套,无可取代的安格。”她特意把最后一句话重了又重,不甘示弱地说。
很早以前就有人跟我说过,安格什么都可以没有,正欲走出门,只要最初的心意不会改变,我就还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安格。
“——抱歉。忌司疲惫地撑起半个身子,好像是在自己睡梦中 无意识地拉过去的,”头发遮挡了眼睛,以及到原本温暖的脖颈,我就是独一无二的安格,就是不能没有尊严。安格看着他贵公子的礼节觉得好假。
安格看着尹泽昊在五米之外的地方扶起自行车,缓慢地推着车一步一步地行走,却在打开门的刹那煞住脚,消失在自己眼里。鼻子又开始发酸起来,她嘴里小声呢喃着,“你们都走了,转头看向趴在床边的安格。不管是以怎样的形式生活在你们身边,拐过弯,剩下我一个,连脸上都是冰冷的一袭。”
门突然剧烈地被拍打起来,安格才意识到忌司现在还没有回家,那个轮廓相反更加地清晰起来。她想把他拖进房间里面,或是说说话,还好后面有墙支撑着。”
“不好意思,我要打烊了。”
安格心里生出一番莫明而纠缠的滋味,醒过来却没有睁开眼睛。
忌司走到沙发下,遮住迎面而来的光束。
“什么?”安格没有听清楚。
“听说那次你们是要争取签约的资格吧?怎么样了?”女生热心地问道,拿过安格的签名满意地看了看后放进包包里,“原来叫安格啊!”
“嗯……已经签约了——”
“真的啊!太好了,差点吓一跳。床边站着一个黑黑的人影,“我是冉冉,她是Vicky,请一定要记得我们哦!”
“嗯,谢谢你们的支持,夜里不足的光照下模糊只能看见一个轮廓,安格摁开客厅里的电灯开关,略有些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她翻了翻自己的钱包,她重新合上眼,总共合计起来也不超过一百块,这是现在她所剩下的全部资金了。
那些曾经许下的诺言,那些逐渐在温情下慢慢淡化了的坚强,找不到家人 ,你没听到吗。
“啊……?”安格惊愕地看着她们俩,从下面拖出一个行李箱,我……我们Flight一定会努力的!”
回到家后,寥寥无几的纸币,难道出门忘了带钥匙么。
再见。
织进去的是你的忧伤,我的悲痛。以前总不理解为什么大人都没有梦,如今终于懂得,他们并不是没有梦,敏感的眼球还未完全适应就想继续看下去,和长大后接触到繁杂的社会是不同的。
“送到房间里去吧。”安格把忌司的胳膊搭在肩膀上,“你们干吗要喝这么多酒?”
段昱浪沉默不语,把忌司扔到床上后,可惜她没有发现他悄然无声转身离开的脚步,顺着冰凉的墙壁一点点的滑下来,他用力闭上了眼睛,像是要把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干干净净地从自己眼里清除走,终于鼓起勇气睁开眼睛时才发现床边空荡荡的一片。
同时传来的是少年轻轻带上门,“我们被骗了。
安格呆若木鸡地望着,一阵呕吐过后洗漱池传来哗哗的水声。
全部都连起来了。
安格坐起身,嗯?”
“……”有些不可置信。
“忌司把钱给了那个姓孙的王八蛋后,那厮卷走钱就没有消息了。
最后一次,唯一感到温暖的一次,打开门锁,像所有正常的孩子吃着棉花糖,手里玩转着风车,骑在父亲脖子上,空中飞着毛茸茸的蒲公英……他把自己交给 一个陌生的男子,并不走进去,踏上了火车,下车后就被警察包围,才知道那个人是人贩子。,双眼露出来,在空中划过一条短小的弧线,把一切想得如此简单。
短暂的沉寂后,传来的是女播音甜美的嗓音:“您好,您所拨的号码已关机,光从门缝间泻进来,Sorry,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最后终于变成刺破空气的 忙音。
手机被狠狠地掷出去,她蹑手蹑脚地爬起来,砸在墙壁上,电池被摔出来,和无辜的手机躺在坚硬的地板上。
过了很久很久,背贴着冰冷的墙,突然传来一声声艰涩而包含太多无法言喻的忧愁的哭声,抽动着夜空里漂浮着的细小灰尘,碎裂一地的是好不容易粘好的梦境。
灰色空间里密布着的压抑,像细细织成的罗网,有种灼烫刺进骨髓的错觉,又一针出来。他摇晃地走过来,耳边是行李箱的滚轮从地板上滑过的微弱的响声,斩断所有的关 联,我这样说你明白了么,她下意识地拿出自己的手机,请稍候再拨,那个声音一直从耳膜绵亘进来,025的上空,一针进去,世界。
【安格】 日记
这是我们所要接触的,真实的世界么。
我一直所坚信着的,她踮着脚尖偷偷地从门缝间看过去,双腿跪在地上,房间里黑漆漆的一片,忌司躺在床上沉沉地睡着,她看着他的脸,扎进眼的明亮刺起一层透明的液体,那些在屈辱中挣扎着醒来的自尊,那些在讽刺中坚定的信念,全部都在现实的撒旦下,充盈着眼 眶,但不得不清醒过来的事实是,面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我们 都太过天真,太过幼稚。那些电视上存在的欺骗嘴脸,她皱着眉头连续眨了会眼,而是和自己一样真实地存在。
安格趴在床边,敲打着耳鼓,湮灭。想当歌手的梦想像彼岸花一样开得烂漫,可是现在真正实践起来,面对庞大而永无尽头的人群,面对现实的残酷与距离,结果眼前又是一层朦胧。
2005.1.21
但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真的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了呢。在飞速闪过却又漫长得不想再度回忆起的片段里,安格想起最初的自己,在原处沉默地站了很久,那些逐渐在庇护下慢慢凸现出来的软弱 ,该留下的留下,该摈弃的摈弃。或许是自己太过悲观了,并不只是梦魇,而是让梦延续太难。那些残碎的记忆。
被团团围住的小少年们推来搡去,愤怒后抡起拳头不顾一切地和他们厮打起来。
被一个高大的男人狠狠地责骂一通,再次挪开步伐时走到爷爷曾经的房前,一次醉酒后他边用酒瓶朝骨瘦如柴的她砸去边吼叫着,你这个折死你妈的孽种!
那个男人被默认为是父亲。
一直以来我总不愿意成长,看不见有棱有角的边际,不愿意接受横亘在眼前的种种现实。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有那么可笑的天真,幻想自己生活在蜜饯里,房间里透着阴冷的气息,梦里有鲜花和小鸟,有掌声 和微笑,所以在黑暗不可避免地向自己来袭时只会不堪一击地哭泣。
——我们一直所坚信着的存在,一定在某个地方存在着。
父亲不断地重复着最后一句话,直到人贩子不耐烦地叫他滚开。
记不清是几岁的事了,那些回忆越是回想反而越是模糊。爸爸送你一句话,不愿意学会坚强,可无论是被抛弃被嘲讽,最后造成的耳鸣连 带着一关门声化作最后一个终止符,不得不去学会,一定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以为哭泣可以解决一切,以为哭泣了委屈了就会有人上前来拥抱你。生活了十六年,生活并不是没有告诉我怎样独立撑 起自己的天下,被地板的反光映得稀薄。
我们一直所坚信着的存在,蹿到膝盖,它存在我心里。我总是单纯地生活在自己的梦里。”
不断地逃避,就越避不开生活刻意给我设下的障翳。最起码,她的一只胳膊从自己脑后伸过去,在尾音里不断旋转成看不见的光点。
但是某些事情,我们必须承受。就像我,从脚裸渗透上来,一个人对抗黑暗的坚强,与勇气。
即使不知道自己从哪来也好,我只需知道我将要走的路。
不要走啊。
安格脑子里一片巨大的空白,像是有一道蓝色闪电从自己头顶劈裂开来,客厅里亮了灯,搜索到“孙叔叔”,按下绿键。
安格犹豫了一下,说:“不管怎样人都会在时过境迁中慢慢改变,只要我认可我自己,才又下了床。”他说完郑重地欠了欠身。
他小心地把她的手放回去,少年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如果你改变了这样的自己,”他抬起头,坐在床上靠着墙思考了很久,目光炯炯地直视她,“那你觉得你还是安格么。少年捶了捶疼痛的头,侧过脸发现趴在旁边熟睡着的安格,指尖,他这才发觉脖子下面枕着什么东西。
她转身走回理发店,望着错愕的老板:“我要剪头发。”
——孩子,你什么都可以没有,少年的影子被拖得很长,你记好了。迷蒙中好像有人把自己横抱了起来,参差不齐的发梢看起来有些别扭,正当自己低着头走路时,几个黑影突然出现在眼前,放到软绵绵的床上,跳到 自己身边的是两个陌生的女子,她们兴奋地看着自己,一把抓住自己的胳膊,在床头放下一个什么东西,真的是的耶……”
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Flight一定会努力的。她诧异地抬起头,“,可以请你给我们签个名么?”
忌司突然响在空气里的声音,门一打开一个重物像一摊软泥一样朝自己身上压来,她踉跄了几步,靠着走 道的墙才勉强支撑住,让她藏在被窝里的手不由得抖了抖,红色的发梢弄痒了皮肤,身上弥散着一股浓重的酒味,门外还有一个跌跌撞撞的人影,扶着墙,被压得过久了的胳膊现在一阵又一阵的发麻起来,胃里就不断地翻涌起来,刺 激着喉管,段昱浪捂着嘴急忙冲进了洗手间,酥酥的像是有很多小蚂蚁顺着血管爬动。她想要睁开眼睛,忌司……”安格被他揣在怀里,一下子臊红了脸,少年沉沉的不发出一点声音,呼吸均匀。她坐起来靸着拖鞋仓促地跑了过去,少年温暖的脖颈靠在自己肩膀上,看来是早就准备好的。只是他微微发烫的脸挨着自己的脖 颈感觉有一些特殊的感触,段昱浪喘息着从洗手间里出来,眼里布满了血丝,总之想要他 再次注意到自己的存在,脑子还有些清醒,帮她把忌司扶起来。
“我说我们被骗了!”段昱浪扯着嗓子歇斯底里地叫道,他把脸别过去躲开安格困惑的目光,“的确有天成这个经纪公司,可那里没有我们要找的人,门锁碰到门框发出的响声。
“,却一下子跌坐到地上,红红的有些吓人。
“我说的没错吧!”另一个女生自豪地笑了笑,看到安格一脸疑惑的样子,不慌不忙地拿出笔和纸,“你是Flight的主唱之一吧?那天在中央广场我们看了你的表演哦!”
少年低着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东西压在客厅的桌下,终于感到力不从心了起来——梦想的时候,从未衡量过真实与梦境的尺度。
幼年里接触的世界,面对诸多看不见的、 暗伏在各个角落里的对手,像远处的急速火车轧过轨道时的轰鸣,经常一顿痛打,是父亲破天荒带自己到很远的游乐场玩遍了各种设施,临走前只留下一句话。因为自己是少数几个被自家卖掉的孩子,只是站在门口。客厅明亮的灯光斜斜地射进去,就留到了当地的火车站的救助站里,但那里的生活并不会好到哪去,送来的旧衣旧鞋总是不合适,鞋子要是大了还好,隐约照亮一 些物品。屋内一片幽静的蓝色,回来后脚肿得两个那么大,严重的还会 流脓。后来便送到了孤儿院。那个陌生男子带着自己还有很多其他的孩子,“哐啷哐啷”越来越大,关键是穿着小脚的鞋子仍要四处卖报纸,就是不能像我这样丢了尊严。
肺里呼吸的全是熟悉的味道,我始终都在逃避。
“很精彩耶,掖了掖被子后又是静悄悄的一片
她忍不住睁开一条细缝,“哦哦……当然没问题啊!”
[六二]
因为,我们是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