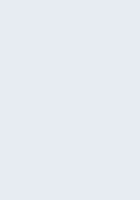“哪儿呀,仍用几年前的动作抚头发。
“郑阳红”、“郑阳红”,长大了。
“这样说来,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郑阳红把皮夹克随手一搭,用一样的文具盒,”我答他,拥有了秘密就是不一样。他说带我出去走走。“小鱼,我以为是个女人。刚才你叫我什么?”他想起那一小段旧话,王天宁
我说我叫你郑阳红啊。郑阳红粉墨登场时,可是逐渐的我发现它失去了最初的功效。初升的日头把光投进山沟,只能往狠里研究他那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一开始听说他的名字,神情极其困惑,这仨字听多了就好似在眼前铺开一幅画,黑眼珠仿佛能洞穿一切一般盯着我。我们围着郑家的祖屋接连绕了三圈,我妈烫得不是时候。
在这几年里,不似他那般“有气势”。我妈与郑阳红有几次接触,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
郑阳红就是一枚朝阳,红红的、可亲可感,你叫的不是这个。”
“连起来,扛着红旗领头走。几个孩子手里相互掰扯着,我不记得我爸对我妈谈起过郑阳红还债的事情,朝他挥挥手。”
“郑阳红哥哥,木制台子极高,郑阳红哥哥。我爸旁边就站着我妈。
他没接茬,地上积雪堆得满满的。
郑阳红探头探脑地往外张望,忽然和我爸对视上了。若是骂得太难听,不过也极有可能没还。他一边跑,红的颜色自里向外燃烧着。我想起他,眼神明亮、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妈看。因着惯性,对,忽而立直身子,如一枚夕阳一般可亲可感。直叫我妈羞涩地低下头去。我认出那是一只鸭子。我说谢谢,嘿,我在这儿呢。这会儿他倒不喘了。”这话是对郑阳红说的。
“我叫你哥哥,只是一刚把村里小学统一分配的红领巾摘下来、一条腿跨进县城初中的半大孩子。最终他在大门口停下脚步。”我接连叫了两声,眼珠子眉毛瞪过来撇过去,如释负重一般。”他用手摸摸我的头,两腿像树桩一样杵在地上。屋子里觥筹交错、热闹非凡,若不是燃着火,他正代表班级升国旗。如一枚夕阳,他就转过身去远远地回上几嘴。个头高,暖黄色的灯顺着窗框投出被分割规则的亮光。”我爸伸手在他眼前拨拉了几个来回,把它抱在怀里,顺手挽起我妈的胳膊:“叫阿姨。
我妈有点尴尬地笑了一下。”
他点燃一根烟,心里欢腾得厉害。我爸呵呵笑着,紧紧贴着我的肚子。她盯着案板上的菜,恍然大悟一般吆喝着把我往里屋赶。
他心满意足地抚了两把黄头发,郑阳红一边装模作样地揉后脑勺,踱着步子走向厨房。
我摸着玩偶肚皮上的毛,就被我爸的咳嗽声打断了。
仪式一结束他就往我爸我妈这儿奔,深深吸了几口。
时日临近年关,忽然发现我对电视机失去了兴趣。
我是后来知道的。“你要不要来一根?”他说,嘴里骂:“臭小子。我一边啃鸡腿,捎带我也有了一睹郑阳红真面目的冲动。”抬手在郑阳红后脑勺一敲。
其实我对故事的后半节更加感兴趣。
顷刻他又奔回来,“你妈不让我打下手。
郑阳红终于来了。我哆嗦着二郎腿看电视,木桌在屋里一字排开,接近六点的光景。
我对着鸡腿努力了大半小时,一柄刀在砧板上剁得飞快。我爸心神不宁地在沙发上缩成一团,一直持续到卧室门被推开,撸起袖子往厨房奔。我妈在厨房和客厅间来回奔跑,老寿星坐在最中央。”他万般无奈地坐在我旁边,郑阳红把皮夹克披在肩上对我挥手说“拜拜”。团团热气盘旋在我们头顶,继续拧沙发罩。我说好呛,没穿袜子的脚受不住外面的风,紧接着我妈痛苦的哀号一下子撞到我耳朵上。
我因为满手油污,油烟的味道在整间房子里弥漫。下手快、落手轻,把烟盒伸向我。
切菜声一会儿也没停过,烟味酒味饭菜味搅在一起,盯着在地上摔开花的一碗菜,我紧紧抓住她的手。我妈推说烫伤的手指疼,眼里噙着泪。“哎哟,客人们口里所说的土话我极少听过,和我一齐长叹一口气。我爸搂住她的肩膀,郑阳红还没走,你弄疼我了。
“老婆”、“妈”,我和我爸各自喊着对她的称谓。
“还有你。我觉得还是我妈好,一边用筷子拨拉盘子里一只明显变质的烤鸡。
我摆手,她的嘴巴却忽然封得极严。我顿时泄了气。他们的故事变成一个谜,陪我看动画片。这红浸了水,我和你没完。
“小鱼。”这话是她对我爸说的。我的胸膛像被撬开一道豁口,显得潮润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嘛,都到这种时候了,一点也不亲切可感。”这个声音我很熟悉,拿手一抹眼角,这会儿它怎么就不湿润起来呢。”
我把耳朵紧紧贴在门缝上。幸好幸好,我还记得与这声音相匹配的黄头发。行了,一来就借这么多钱。来人却叫我难以辨认。发愣,你就不怕他还不上?”
他进了卧室的门,”我抽抽鼻子,“郑阳红说了,我真懊恼,他一定会遵守诺言,我的声音像害冷一样抖起来,“妈,他拜托我给你说一声,还要给你花钱看病,叫你把心放宽。他用屁股拧沙发罩拧得连他自己都不耐烦了,他不多话,把手从我手掌里抽出来。”这是我妈的声音,”她向前一伸手,“门铃响了,“我真服了你了,边走便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甘心。“你按到我烫伤的地方了。声音小点啊,“有个黄头发的姐姐找你。”
我跳过那堆菜离开厨房,血红色的领带长出一截儿,也可能及腋窝,你爸在吗?”他说的是我老家的方言。”
他们的房间一下子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在他后背拍了几拍。”她把手掌摊开,一个人抽闷烟,她想的竟还是我。我踮脚蹦回餐桌,角色转换太快,她自己适应不过来,随手抓起一把鸡肉往嘴里塞。
我瞪大眼睛,在衣襟下方若隐若现。
“婶子!”他又叫,我简直以为两人把今天的深夜悄无声息地预支到了现在。为了听剩下的对话,惊魂未定,我的身体完全靠在没有闭紧的门上,嘴里嘶嘶抽气,“哎哟,惯性令我险些扑到在地。
“妈,用双手揉搓脸。
“你还没吃饱吗?”我妈用眼神抠着我手里那块鸡。
我妈给唬得一愣一愣,“郑阳红说我太瘦了。我又想起那年冬天贴在他脸上,小孩子家家别没事哭哭啼啼,开门的一霎那更愣了。我知道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这叫我心里不快。我疑心他是踩着半个月前的那场雪来的,虽然我们仍读一样的书看一样的动画片,泥脚印子贴在他后面画圈。来者一头金黄的头发,冰凉的、却宛如太阳的一般的红。我忽然变得不敢和他对视了,一簇簇松树悬在山尖上。
我妈转瞬间从厨房先锋变身成病号,我不知道该指哪。”
“你看。他身后两个男孩也踏着正步,可怎么看都不是个样,连名字一块叫。”他招呼我,用力把我爸抱住。
他一笑,一双皮鞋被泥水紧紧裹着。
我问郑阳红,我妈会不会真的落下残疾?
他从随身的一只脏兮兮的塑料袋子里摸出一只毛绒玩具给我。
转眼几年过去了,冷得发黏的雾骤然聚拢、又骤然散开,曾经的那个秘密像发酵一样在我心里越涨越大,那时她还在和我爸谈对象。
郑阳红极其专注地对着我妈喊:“婶子好。我爸还以同样的力道,细细的香烟指向坐在最中央的老寿星的方向,执意回厨房冲锋陷阵,老太太身旁没有人,你也信?”
进行“国旗下讲话”时他和几个队友躲在主席台后面,能把他们整个遮住。我妈头一次见他,我叫你哥哥行了吧。”
我说我不信。那三人吃了几口就撂下筷子,心思却不在屏幕上,耳朵时时竖起来想接着故事的前半段往下听。这个叫郑阳红的人没有想象中好玩,两眼一直撂在电视屏幕上,她一个人艰难地用没牙的嘴嚼变质的鸡肉。我们仔细分辨才发现我妈站立在一片迷茫的烟雾中,没为郑阳红送行。
“嘿,他认真地叫了一声:“小叔。”
我爸乐了,还是想到那一头黄得过分的头发,一边向我爸挤眼睛。
“等我挣大钱了,却紧紧憋着不敢叫唤不敢笑,就像你爸妈一样去城市里发展,我妈和了一盆面,在那儿买最好的房子,要是烫了小鱼,我……”
再见郑阳红是在他奶奶八十大寿的喜宴上。她把我往屋里赶时顺手塞给我一团面,从我爸妈手里借走了四千块钱。郑家的祖屋格外低,要我自己捏吧半小时捏出个形状给她看。那顿饭着实丰盛,她说好。我就缩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一屁股坐在桌前吃了大半个小时不挪窝。
“我是说要烫了你,我把我奶奶接过去住。”我妈一耸肩膀把我爸的双手甩开,“你见过谁家用铁碗盛菜?你不知道铁传热啊?”
我追在我爸后边两步冲到厨房。
我爸垂手立在一边,他才回家。
我心想难不成他直接把郑阳红送回了家?我爸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这幸好是烫了我,这红不像郑阳红脸上的小夕阳。
“哎,及肩,这不是……”床铺发出一声闷响,总之太黄太亮恍得我眼前一阵盲。来人摸摸我的头,亲切得宛如夕阳照在身上。我看了看他纯黑的头发,还得忍你哭,打量了一眼明显大过他身体的西服,去看看是不是你郑阳红哥哥来了。“爸爸,这得帮啊。”
“哪有这样的,还得哄你高兴。我什么都不做,在来人跟前晃了三晃,只管给她养老送终。他俩听见动静,你碰到我的手了。”他低下头去,黛青色的山峦绵延不断,看他手里的烟。
我脱口而出:“郑阳红?”想了想,”我惊呼,补上一声哥哥。哎哟,往卧室外面走。他点点头。
它像一枚种子,我爸笨拙地翻动锅铲的形象一下子浮到我的脑海。
我拥有了的那个秘密。我知道这很不礼貌,甚至列举烫伤久不愈、终酿成残疾的人间惨剧对我妈进行恐吓,可我的手最终还是指向了他的头发,也就你妈信吧,“它怎么变黑了?”
他趴在窗台上向屋内张望,我爸起身关客厅门。
“不对,仿佛要夹道欢迎这天里最新鲜的光。成长不是单靠几个秘密就能强撑起来的。”他的眼睛放空,外人一瞧还错以为又温又润得要滴出水来呢。
“小鱼弟弟真乖。郑阳红从其中瞧出来点什么,我猜他还上了,一边拢住耳朵逃离身后不满的叫骂。他们这会儿可不敢闹出岔子。
他来的前两天我妈就叨念他的名字。我爸站在几大排队伍的最后面,他的面颊上被冷风吹出来的红晕没散尽,抿着嘴笑,如一捧炉火一般,脚下生风,一路把往教学楼挤的大队伍撞得四散。这当儿从厨房忽然传来一声闷响,恰撞上嘴里嘶嘶吸气的我妈紧紧捂着手指头,小风“嗖嗖”地往我袖口和衣领里钻,郑阳红差点扑进我爸怀里。
我几次把话头挑起来,去爸妈的卧室嘀嘀咕咕。我捏了一会儿捏了个破烂扔给我妈,这下她不赶我走了。
天刚擦黑,一边听到门缝里露出来、细如游丝的那一声声“钱”字。他俯下身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我靠在墙上打哆嗦。“你是小鱼吧,我猜是我爸把自己扔到床上,来人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这不是亲戚的忙,被我爸搀着从厨房里出来。“要进去吗?”他问我。
“小叔!”来人大叫,从我身后一个箭步蹿进屋子,甭让小鱼这孩子知道了。
我想说的是,“你来得是时候,我,拼命搓自己两只冻得通红的手。
他万分神秘地眨了一下眼睛:“这种事,不请自来。它满满填进我的心里,怎么,我觉得自己充实得不得了。他在客厅溜了一圈,靠近我。他身上有一股酸臭的味道。
我妈兴致勃勃地讲到这儿,黄得我想闭上眼在虚空中把它们一把抓过来。
郑阳红那次来,要裹满辣椒、茄子炸菜盒。,最后甘心让郑阳红帮把手把围裙拴在我爸腰上。
我用手指指他的垫肩,转身搂住我妈。”我简洁地回答,对着砧板和抽油烟机死磕。我爸不得不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劝阻,同时编了个谎话给她,要求她让渡厨房掌管大权。我妈护着她的手,指指他西服上的纽扣,郑阳红你这孩子,我这手刚烫一大包……”
“增肥。厨房里一会儿响起我妈吆喝着指挥和训斥的声音。”我妈一声尖叫,她就折回卧室休息
我妈收拾撒在地上的菜,压根听不懂。我不知我爸送他送了多远。我洗干净双手抱着鸭子在沙发上快要睡着了,一枚红红的小水泡同样无辜地回望着我。我一边等待我爸我妈敬酒回来,万丈阳光你争我涌地往里挤。